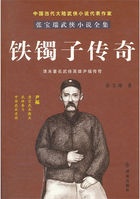地铁日渐日旧,沉默着,单调地来回穿行。
上海现在有两条地铁线路,一条南北方向运行,贯穿这个城市最热闹的市中心,另一条从河流的底下穿过去,把河流两边的土地串连在一起。从早上五点到晚上十一点,地面上城市从苏醒到沉睡,地底下的城市也同样地从苏醒到沉睡。
清晨和傍晚的时候总是最拥挤的。夹着公文包的小白领不停地发短消息,上学的小姑娘要踮着脚尖,把书包抱在胸前才能够安心,人们在地下穿行的时候都在揣测着头顶,是水管,是马路还是河道。其实地铁站是个很好的地方,沉默而便捷,四周的小铺子里卖着不正宗的关东煮、珍珠奶茶、时髦的恐怖小说和漫画插图本。内衣和手机的广告牌和人群一样地簇拥着,外地人站在自动售票机前用手指仔细琢磨着复杂的路线和站台名,这里很少有乞丐,只有卖报纸的人会在车厢稍微空一点的时候贩卖手中新出的晨报。拍粘纸照片的地方挤满了刚刚放学的女学生,穿着自己改短过的校服裙子,头发多是染过很不明显的褐色,双腿交叉地站立成一堆。早晨她们从各自的屋子里化着看不出来的妆,吮着豆奶走出来,走进地铁里面.膝盖并紧地坐在候车位上背书、等车,傍晚她们三五成群地再次走进地铁站台,把校服悄悄塞进书包里面,把扎拢的辫子散开来,唧唧喳喳地说着私密的话,在地铁车厢里聚成一小簇一小簇的,埋着头,眼光流转,只有她们才显得和这里如此贴切。
可可在自动售货机里买了两罐冰冻百事可乐,给小俏一罐,俩人坐在橘红色的候车座位里,把书包摆在膝盖上,一人抽出一本漫画书来消磨等待地铁的时间。
“昨天看见有卖那种用带子系在脖子里的,黑底和粉红色的刺绣。”可可凑近小俏的耳朵说,“很贵的啊,不过夏天穿肯定很好看,脖子后面有一个小蝴蝶结。”小俏在她身上轻轻拍打了一下,俩人嬉笑着看了一眼坐在她们旁边一个中年男人。他穿着中年人常穿的细条纹衬衫,坐得异常端正,心不在焉地在一本黑色的记事本上面涂画着什么东西。她们俩都多看了他一眼,因为他的眉眼长得竟然有几分熟悉。
地铁开过来,坐在座位上的人都站了起来,可可拉拉自己被改得过短的校服裙和小俏站在人群的后面,这时候身边那个一直在涂画着的中年男人也站了起来,穿越过人群往前走,手臂甩在小俏的胳膊上,他扭过头来低声说了声:“对不起。”又笔直往前走,走到站台边,不急不缓地站了一会儿,向右张望了一眼从黝黑的轨道尽头驶进来的地铁,车灯发出刺眼的光芒。他向前走了一步就好像平时走进车厢那样,匆促地迈进了地铁的轨道,地铁根本就没来得及刹车。
男人的身影倏地一下就消失了,保安的口哨声尖厉地响了起来。
男人消失在车厢的底下。
地铁停了四十五分钟以后,又再次打开了车厢门,人群没有过分的慌乱,在保安的El哨声中徐徐地走进了车厢,嘟嘟声后地铁就开走了。车厢里的人握着摇晃的把手,三五成群地小声议论着刚才那个自杀的男人。
“喂,你猜那人为什么自杀?”可可摇晃对着车窗玻璃抚摩着自己的眉毛。
“不知道。”小俏摇摇头,“他死了吗?”她们还是都抹不掉那个男人跳上地铁轨道的那一瞬间,竟然觉得他的样子至少还是优雅的,甚至没有那种在地铁站台常会见到的急忙的厌弃,他就是那样优雅地往轨道一跨就倏地消失了,好像过马路一样就去了那一边。
“那还用问,肯定死了。”可可把脸倚在车的把手上面。
两个人都不再说话,只是注视着地铁车厢门玻璃里面自己脸孔的影像。这两个女孩子,一般大的年纪,也是一般高的个头,站在左边的小俏是个美少女胚子,面孔像陶瓷一般,眼梢稍稍地向上翘着,额头上有一层柔软的毛发,不过这种少女的美还是藏着掖着的,没有舒展开来,或许也是有点自知,但是却弄不明白旁人的目光到底是投向哪里。身边孜孜不倦地抚弄着眉毛的是可可,她的头发很浓密,染了浅褐色以后就在头顶微微地松散着,宽额头,五官散得有些开,眉毛被修剪成彩虹的形状,细细弯弯,都不太好看,却有一种很淡然的妩媚。两个女孩子就这样互相倚靠着在地铁车厢里面说着私密的话。地铁里有很多这样的女孩子,有时候很难区分她们,她们都穿着短裙子和彩色及膝丝袜,书包上挂小东西怎么挂都不嫌多,听听她们讲话,多半都是在讲老师的笑话、暗恋的小爱人,或者是鄙夷的人。
这时候,2004年的春天已经只剩下一个尾巴,所有的傍晚都宛若一张少女抹过面霜的面孔,而夏天就将到来,在夏天到来之前的地铁里,死去了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本来这一切与小俏和可可的故事并没有关系,可是可可在这个中年男人迈上地铁轨道的时候,拣起了他掉落在地上的那本黑色记事本,小俏想阻止可可把记事本放进包里面,可是可可还是固执地把它放了进去。
她们只需要坐几站路就出了站,俩人的家住得很近,都在四季新村里,新村房子是这里最常见的,灰蒙蒙的,整洁的,排在一起,四周种一些香樟桂树或女贞这样叶子细小的树木。一层楼里住着几户人家,公用的走廊里摆着自行车和废旧的箱子,沿阳台的楼道里种养着葱、大蒜和一些细小的仙人掌,或是用蓝色布头遮着光的鸟笼,各种广告单子塞满信箱,每个新村里都有一些小胭脂店,卖冰冻啤酒和康师傅饼干等,老板娘的侄子如果碰巧在的话,还可以送货上门的,门口站着戴红袖章的老头子,终日双手捧一只装满茶叶渣滓的玻璃杯。
这些和地铁又是全然不同的风景,只是一转弯,顿时所有的喧嚣和流彩统统消失了。
萝卜排骨汤和咖喱鸡块的香味从一些颜色模糊的窗口里面散发出来,那么安静。小俏和可可在一条窄小马路的路口分手,一个向收了摊的菜市场方向走去;一个拐进了弄堂里面,身影很快就隐没在了低沉下来的夜色里面。
可可进了家门就换了拖鞋,趿拉趿拉地拐进卫生间里面,拧开水龙头开始往浴缸里放水,然后她合上马桶的盖头坐下来,从书包里拿出那本中年男人掉落下来的黑色笔记本翻开来看,大部分是备:忘录,把会议的时间和地点写在那些狭小的格子里面,可可翻了一会儿,就倦了,把本子放进马桶边上的旧杂志堆里,跨进了浴缸,把身体蜷缩到水面之下,耳朵听到的都是水在水管里面奔腾的声音,而那个男人匆匆拨开人群向前走的身影又再次出现在她的面前,她闭上眼睛,不愿意再去想。
星期天的下午可可从昏睡中醒过来,头晕得不行,昨天晚上她去看大维在U2酒吧的演出了,然后就喝酒了,最后是被人从厕所的一堆呕吐物里像根萝卜那样拔出来的。她不敢回家,妈妈看到她这副样子肯定是会疯掉的,可可觉得自己的母亲时刻会疯掉,她是个正值更年期的神经绷得很紧的女人,为了一点点儿的小事情都会歇斯底里起来,她脆弱得简直比个青春期的少女还要碰不得。
所以她去了小俏的家里,在小俏家的浴缸里面洗了个很舒服的泡泡澡,换了小俏的睡衣以后就没心没肺地一倒头睡到现在。此刻小俏不知道去了哪里,她就一个人静悄悄地躺在床上注视着房间里的一切:墙壁上的收音机头乐队的海报,趴趴熊的床单,地板上拼了一半的拼板,桌子上几瓶廉价的香水和指甲油,彩色条纹的内裤都叠得好好的摆在一只透明的箱子里头,一棵快要死掉的龟背竹摆在窗台上面。
可可昏沉地爬起来,把桌子上小俏替她倒的一杯凉水倒进了花盆里,又趴在桌子上,在笔筒里找了一支顺手的圆珠笔,打算给小俏留张条子就回家去,刚推开房门,就看到小俏的妈妈捧着一碗糖番茄走向厨房。
“哦,我们家小俏出去上补习班了,晚上才回来.呢,你不等她了吗?”小俏的妈妈绝对是个慈眉善目的女人,很善良的一心一意对女儿好的女人。
“不啦,我该回家去了。”可可说,“跟小俏说一声。”
“嗯,你去洗手间洗把热水脸吧,面色很不好,到厨房吃碗粥再走哦。”
可可在洗手问打开热水龙头,把小俏的芦荟洗面奶抹在脸上,抹了她用的尼维雅,水兜边放着一盒redearth的胭脂,是不久以前她们俩一块儿去买的,店里面的营业员小姐直夸她们俩的皮肤那么好,到底是才十八岁的女孩子。可可觉得小俏是好看的,小俏的好看是一种真正的唇红齿白,她就是不化妆,穿着规矩的校服也依然是好看的,她上体育课的时候穿着线裤和白汗衫在跑道上跑步的时候,可可注意到有很多打篮球的男孩子都会用目光的余梢追随她。她想象着小俏平时每天早晨起床,对着这面镜子洗脸,用食指挑一点面霜用手指在脸上抹开,那张脸是真的面若桃花。
而现在镜子里可可的脸却是苍白的带着点酒精带来的浮肿,她的眼睛和小俏比起来太小了,睫毛也不卷,关键是,镜子里的那个女孩,看起来是那么沮丧和病恹恹的,可可生气地拿刷子往脸上扫了一点儿胭脂,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稍微红润了一点儿,又觉得扫得太多了太红了,令她想起玩猢狲把戏时的那只猴子,她突然沮丧得想哭,开了水龙头把脸上的胭脂通通地洗去,拿毛巾狠狠地擦,回复到那张黑着眼眶的苍白的脸,这才闭起眼睛不看镜子了。
回家的路上恍恍惚惚的,下午的太阳太好了,新村里有人出来遛狗,有人把棉花胎晒在绿化带里面,几个穿着旱冰鞋的小孩从可可的身边擦过。手机响了,可可从包里很费劲地找出她那只缀满了挂件和铃铛的小家伙。
“喂,我是大维。你昨天后来还好吗?”
“嗯,后来去小俏家里了。”
“那就好,你昨天在男厕所里乱吐,还哭了。”
“以后再不喝那么多酒了。”可可挂断了手机。
可可与大维已经分手三个月了。事实上,三个月前,大维突然消失,他消失后的一个星期,可可在公交车上看到他搂着另一个金灿灿头发的女孩子,在马路的拐角处一下子闪过,可可狠狠地删除了手机里大维的电话号码,大维在这三个月中也不曾找她,从此俩人断绝了联系。可是现在大维突然又出现,她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在甩了她之后,又回来找她,突然又请她去看演出,他或许只是消磨时间吧,可时间是足够可可消磨的,而可可正好只担心冗长,也有可能在她的内心里,这三个月始终没有忘记过大维。
她把耳塞塞进耳朵里面,开始听收音机头乐队哀鸣的声音,她有一点忧伤,看到自己家的阳台上面她刚刚洗过的校服晒在太阳底下,滴着水,那裙子被改得太短了。昨天晚上她醉了,吐的时候,真的大哭了吗?真的当着大维的面大哭了吗?
回到家里,妈妈蜷在客厅的沙发里面,没有开灯,厨房里还堆着许多要洗的碗筷,水龙头没有拧紧一个劲儿地滴水,她只是蜷着不动,默然地看着电视里的电视剧,每个夜晚她都是这样度过,在电视机前面坐着,连瓜子也不吃,一动也不动,爸爸总是加夜班,她就这样坐着等他,有时候等到十点钟还没有回来,她就一个人抱着一条毯子婆娑着走进房间里去。这时候可可想起了刚才在小俏家里喝的那一碗冰糖番茄,嘴唇边还有甜甜酸酸的味道,心里觉得难过。电视里面正在播新闻,一个声音标准的男声说:“最近地铁里又发生了自杀事件。”可可看到电视屏幕里一张男人的照片,正是她和小俏眼睁睁地看着他跳进地铁去的那个男人。原来他是个会计师,名字叫做程建国,一个太普通的中年人名字,有着他那个时代的烙印。
“哎哟,我是看着他跳下去的。”可可惊呼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