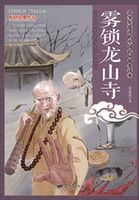乔茵身高一米六七,长长的头发,和万紫一样,皮肤白,眼睛大。她是个出众的小美女,这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了。十一岁的时候,她就开始在成都参加街舞比赛,在很多唱歌跳舞的孩子中间,颇有点小名气。
她并不想到北京来。但比她大不了几岁的继母,让她头疼不已。爷爷奶奶希望她回父亲家去住。他们有自己的生活,要旅游,要锻炼身体,他们不想这个年龄了,还要操心乔茵的一日三餐。突然有一天,奶奶说:“你去找你妈妈吧,她稳定下来了,有了工作,买了房子,想要你过去跟她一起住。”
乔茵长这么大,还从没有离开过成都呢。她的心里涌上了不安和恐惧。
妈妈这些年,每年都会回来看她,也常常给她带很多东西:好看的衣服,MP4,新手机。她十三岁生日时,妈妈还买了一套芭比娃娃给她。
那时她早就不玩这个东西了,可是她没有拒绝。
父亲和爷爷奶奶,真的开始准备让她去母亲那里时,乔茵心里充满了愤怒。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总是被亲人抛弃,先是妈妈,后是父亲,现在爷爷奶奶也不喜欢她了。
这让她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价值。但她从不对任何人说出来,只是非常心灰意冷的时候,才会深刻地觉察到这一点。这个时候,她会感到非常悲凉。
万紫在乔茵的心目中,有点像一尊塑像,而不是妈妈。摸不着,看不透,也不能靠近去摸。
有那么几次,万紫从北京回来过寒暑假。她带乔茵一起去玩,公园、电影院、游乐场、商店,她握着乔茵的手,乔茵的手就一动也不敢动。她体味着母亲这陌生的手的温度。万紫的皮肤偏凉,再热的天,也是凉凉的。乔茵不习惯,直往后躲。
等她再大一点,万紫回到成都,就再也叫不动她了。去吃饭,去买好看的衣服,去买游戏机,通通打动不了她。她表情淡淡地,跟万紫打声招呼,就钻到自己房间里去了。等到万紫和陈先旺离了婚,除了看女儿,万紫再也没有更好的理由到陈家来了。
她也没法去资中,想到母亲那个样子,不如待在北京好了。那些年,她才三十出头,相貌不坏,性格虽然有点内向,但因为从小吃过苦头,却也知道做人要随和。
有男人追求她,答应好好照顾她。两个春节,她都是在北京过的。
年三十,她会给乔茵打个电话。电话通了,她叫着乔茵的名字,用欢快的语气冲她喊:“乔茵啊,春节快乐!你在做什么啊。”
乔茵就说:“看电视。”
万紫不能再像前几年,问她想妈妈吗?那时她的问句脱口而出,乔茵的回答也很爽快:“想!”
但现在不行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她问她这句话,乔茵一声也不吭。这坚硬的沉默,让万紫心凉如铁。她开始小心翼翼地选择词汇,跟女儿说话了。
即便这样,乔茵还是不跟她好好说话,万紫问一句,她才回答一句。口气中,这个妈妈其实完全是多余的、没有必要存在的,甚至耽误了她看电视节目。
万紫发誓,只要一安顿下来,她就一定要让孩子尽快到自己身边来,否则就太迟了。
她给乔茵上的是一所很好的私立学校。这也是为什么她会选择去外资公司工作,而不是留在高校或是科研单位的缘故。
可是收入高,也就意味着将非常的忙碌。要买房,要买车,要给孩子上好学校。她没有什么好弥补她的,除了更多的物质享受。这世界从来如此残酷,赚钱和亲情不可兼得,她再一次联想到了母亲的那些岁月。
从这个角度讲,她在走着和母亲并无差异的一条路。可是,比不上母亲的是,她扔下了孩子。
乔茵平时住校,周末回家。
只要她回到家里,万紫会尽量放下手头的所有活计,陪着乔茵。可惜乔茵并不需要,也不在乎她的牺牲。她不是躲进房间里看书,就是告诉她,和同学有约。然后,她关上洗手间的门,在镜子前打扮一会儿,就跑了出去。
万紫对这个女儿,有点拿捏不住。她不能教训她,最糟糕的是,她也不能跟她太亲昵。她们俩在一起最愉快的时候,就是共同看到一部好看的电影,两人的心里,都因一个感人的好故事,而泛起温情。空气中,有着往日没有的平和气氛,万紫给女儿倒杯水,她也会很自然地伸出手接下来。
可惜这样的时候并不多,因为“佳片有约”开始的时间,往往很迟了。乔茵不瞌睡,万紫也困了。
在万紫的心里,她只希望,能和女儿好好相处,即便没有很多的亲情,能彼此温暖也可以啊。
自从乔茵来到北京后,她每天晚上都睡得很踏实,这么多年的恐慌、寂寞、想念,终于有了安妥了,就像潮涌不断的海面,突然丝绸一般地平静了。
平静的海面下面,注定有惊涛骇浪。
两个月前,万紫接到乔茵学校老师的电话,问她乔茵的病好了没有,能否可以来上学了。
万紫接到这个电话时,正在办公室。手里放着几个项目的论证材料,桌上还有她和女儿的照片。听到老师这么说,她突然双手发抖,口干舌燥。她不知道乔茵多久没有上学了,也不知道将事实告诉老师,对乔茵是否够好。
她颤抖着声音说:“好了,她很快就可以上学了。”
老师大概听出她声音有恙,在那头轻轻叫了一声:“你还好吗?”
万紫没有话说,她大脑一片空白。孩子这段时间,如果不在学校,她在哪里?她已经来例假好多年了,她会因此而怀孕吗?
她坐不住了。好长时间,才意识到自己还拿着话筒。她对着电话,说了一声谢谢,那边传来一阵忙音。
她拨乔茵的手机,对方却是关机。乔茵曾对她说过,自己在学校时,手机是关掉的。因为不能影响上课。现在她并不在学校,为什么还要关掉手机?
她发了一条短信给她,“尽快给我回个电话。”
怕她担心事情败露,做出什么别的蠢事来,她又加上一条:“我病了,很难受,能否跟老师请假,回趟家?”
这一天已经是周四了。万紫发完这条短信,便将手里的资料,整理装包,匆匆开车回了家。她怕万紫很快就会回来。
晚饭时间悄悄过去了,万紫坐在沙发上,房间里安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天边在酝酿着黑夜,万紫的心七上八下,仿佛时间的黑幕也在一点点拉上她的心头。乔茵在哪里?她这些日子,住在什么地方?她身边会有男孩子吗?她为什么要这样骗她?为什么不愿意去学校?她以后要做什么,她又会做什么,她到底在想些什么?
尽管脑子里全是愤怒的问号,像一颗颗子弹,射向她的胸口。但万紫的外表,却反而更沉寂了。她仿佛被这些密集的子弹,逼到了促狭的阴暗的黑洞里,动弹不得。几个小时过去了,她一动也没有动,天终于黑了。
她也不开灯,仿佛生怕光线的明亮,冲散乔茵上楼的脚步声。
八点多,门口终于有了动静。乔茵在拿钥匙摸索着开门,万紫吁出了一口长长的气,心口突然疼了起来。如果心脏也有肌肉的话,就好像憋得太久,绷得太紧,现在放了下来,当然会疼。
乔茵走了进来,顺手打开灯。
她并不主动开口问万紫话,而是站在门边上,观察着她。万紫脸色肃穆,看着乔茵,她也不知道第一句说点什么才好。乔茵手里什么也没有拿,没有包,没有书本,只有一串钥匙。钥匙圈套在食指上,那样子,似乎在说,我只是回来看看你,马上就要走的。
她甚至不肯坐下来。
万紫只好站了起来。她告诉自己无数遍,千万别不耐烦,别发脾气,别说难听话,好好跟孩子谈一谈。人心都是肉长的,乔茵这个年龄了,该懂的事,她应该懂得了。
万紫说:“乔茵,吃饭了吗,妈妈给你做点什么?”
乔茵冷冷地说:“吃过了。你不用管我。你怎么了,看起来不像是生病。”
万紫已经走进了厨房。见到了乔茵,她才觉得自己也饿了。她一边烧水,准备下点鸡蛋挂面,一边说:“不太舒服,想见见你。我下点面条,你陪我吃点好不好?”
乔茵犹豫着,踌躇片刻才说,好吧。
她开始换拖鞋,将钥匙放在茶几上,打开电视,调到音乐台,声音放得极大,房间里立刻充斥着黑眼豆豆的说唱音乐。她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屏幕,一副别打搅我的表情。
万紫用筷子,轻轻压着浮上水面的鸡蛋。她只想愤怒地大喊一声:“关掉电视!”她感觉乔茵将声音开大,是故意的,就是不想跟她说话。但再照顾孩子的情绪,该谈的问题,是不是也要谈呢?难道,她还指望乔茵对她主动交代不成?
不行,她不能这么坐以待毙。够了,她也受够了。她受够了这孩子的懒散、冷漠、自私、任性。她丝毫也不明白牺牲意味着什么,就开始跳在她的头上,指责她抛弃她在先。
万紫也有自己的生活,谁说她这一辈子,就要为她乔茵活着了?何况,她做出这么大的努力,忍受着这么多年的孤独、寂寞,远离亲人的痛苦,还不是为了给女儿一个更好的未来?
她凭什么,就认定,是她对不起她呢?
她一把将煤气灶拧灭了。强忍着怒气,告诫自己,数三下,数三下,再去客厅里。一定要有个好的开始,这场谈话,才能继续下去。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乔茵,把电视关掉,我有话跟你说。”
她终于站在了客厅的当间,而且声音不高不低,正好合适。听不出在生气,但也绝不是随便说说。
乔茵看了她一眼,不情愿地举起遥控器,将声音关小了一点。万紫说:“电视机关掉,我想跟你说个事。”
她在努力控制自己,可声音还是透出了不满的情绪。乔茵不高兴了,咔嚓,将电视关了,背靠在沙发上,双手抱在了胸前。
万紫拉一把椅子,坐在了乔茵的对面。她想看着她的眼睛,跟她说话。她离开乔茵来北京上学时,乔茵已经五岁了。她记得跟乔茵好好谈过一次,她告诉了乔茵很多,她的希望,她的未来,她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因为要跟孩子分别,她哭了好几天。可是走的时候,又担心孩子会缠住她,她就骗她是去给她买吃的。
五岁的孩子,应该有点记忆了,那时她甚至庆幸自己考了这么多年才考取,孩子大了,到底能明白一些事情。那个时候,无论她说什么,都是抱着乔茵,看着她的眼睛。乔茵的眼睛很漂亮,比万紫年轻时还要好看。可是这双仿佛是从自己面孔上转移过去的眼睛,现在却变得陌生,冷酷了起来。万紫发现,乔茵躲闪着她的视线,她并不愿意跟她对视。万紫就说:“乔茵,你知道妈妈要跟你说什么事了,对吧?”
乔茵当然知道,她怎么会不知道呢?接到万紫的短信时,她就知道自己逃学的事可能暴露了。因为她晓得,万紫真要生病了,她更不会告诉她,她会自己去看病,才不要耽误她上课,从学校将她叫回来呢。
她是想回来转一圈,赶紧找个借口,就溜。如果时间还早,她可以借口明天一早有考试,得回学校。如果晚了,她就说瞌睡,想睡觉,钻进自己房间好了。
她觉得万紫不会对她怎样的。她了解万紫的性格,她是那种一心要做好妈妈的女人。她有文化,有知识,和小市民妈妈不同。她不会跟她撕破脸的,不会骂她,更不会打她。
只是她们的交流,需要时间。总有一天,她会明白乔茵在想些什么。
真没有想到,这么一个她觉得无论如何也不会跟她较真的母亲,居然拉了把椅子,坐在了她的对面,眼睛盯着她问,知道她要说点什么吗。
乔茵不怕万紫疏忽她,但怕她会关心她。她盯着她的眼睛,则更是一件无法令人接受的事情。因为妈妈,也是一个既陌生又不能忽略的人。她对她内心的感情,有很多很多种,其中有一点留恋的原因,是因为在她心里存了那么多年的不满、给自己各种不良行为寻找的借口,都可以拿她来发泄。
她无赖地回答:“不知道,那么多事,我不知道你要说哪一桩。”
万紫看出了乔茵的抵触,耐心地:“这些天,你不在学校,都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人在一起?”
“朋友,同学。”乔茵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万紫突然发现,她好像烫了头发,蓬蓬松松的,尾梢有大卷。
“什么样的朋友和同学,他们也不上学吗?你住在哪里呢?”
“不是告诉你了吗,朋友和同学那里。”
“他们都不上学吗?家里有大人吗?他们的家长怎么说?”
“有些上有些不上。我们在一起作音乐,住的那家,大人都不在国内,大房子就她一个人住,所以,我们可以住得下。”
乔茵说得如此自然,万紫不由倒吸一口凉气。什么叫有些上有些不上,什么又叫一起作音乐,还有,父母都不在国内,留一所空房子让孩子住?
这样的孩子,能住出什么好事来?
这天底下,怎么有这么多奇怪的事情?
再追着问,终于大概弄清楚了。提供大房子的是个女生,叫遥遥,是乔茵那个所谓乐队里鼓手的女朋友,鼓手叫邵飞,比乔茵小几个月。同住在一起的,还有乐队里的吉他手春儿,电贝斯手溜达。
万紫皱着眉头说:“他们怎么叫这名,真名是什么?”
乔茵说:“他们的艺名比真名更出名,你记住这个就行了。”
乔茵这个乐队,成立了小半年了。万紫一直用一种不去了解的态度对待它,因为她想,只要她不闻不问,或者说,更多的大人都像她这么不闻不问,这几个小屁孩子,自然就会灰溜溜地解散的。但现在看起来,似乎不问不行了。乔茵是主唱兼主创。万紫说:“你们这里面,谁上学谁不上学?”
“溜达有学上,他在通县的一个影视学校学表演呢。春儿邵飞遥遥都和我一个学校,遥遥还去上课,但我们都不愿意去了。”
“为什么?”
“志不在此。”
乔茵说到这里,站起身来伸懒腰。她这是用肢体语言公然挑衅吗?告诉万紫,没有你这么大惊小怪的,我的人生志向早已选定,你不支持我,就别想挑我毛病!
乔茵刚成立乐队不久,就对万紫提出过,想去上艺术学校,学演唱或是表演。她喜欢这个。万紫学理工出身,简直无法想象家里会出这样的一个人。她认定这只是乔茵心血来潮的孩子气,过一阵,玩厌了,自然也就好了。
艺术那东西,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学的吗?
单不说奋斗之路的诡秘和运气,就说那些大把大把的潜规则,她也不能让女儿去啊。
她没有理她。现在,这也成了乔茵逃学的理由——谁让你不让我去学唱歌的?
万紫压着心头火,看着理直气壮的乔茵在她面前做起伸展运动。她说:“你笃定你能靠音乐吃饭?”
乔茵满不在乎的口气:“那我也不笃定我能靠上学吃饭。”
万紫苦口婆心:“音乐美术这些东西,当做爱好就很好了。年轻的时候,多试一些别的可能,做多一些选择才有意思。为什么只给自己一条路可走,而且是这么一条不靠谱的路?嗓子好,唱歌好的人,一抓一大把,就像抓沙子,能留下来的,有几粒?你到底有多坚强,有多少才华,年纪轻轻,给自己这样一条最艰难的路?听我说……”
乔茵打断:“妈妈,我瞌睡了。你别说了,我要洗澡睡觉。”
说着,就去卧室取衣服。
万紫跟在后面,一把抓住乔茵的胳膊。用的力气大了点,乔茵夸张地叫了起来。
“你弄疼我了!”她喊道,“我只是想睡觉,你干吗?”
万紫刚松手,就看见乔茵眼泪汪汪。乔茵这是委屈,说不出的委屈。并不是真的被万紫抓痛了。她不喜欢这么被母亲追问,仿佛她做了多大的坏事。是的,她逃学了,可是她又没有吸毒抢劫和杀人,她只是在做她喜欢的事情。她要写歌,要练歌,还要处理乐队里的其他事情。她答应了几个小兄弟,只要找到钱,他们就会灌制一张唱片,拿到唱片公司去推销。唱片公司里的人,他们谁都不认识,但她一点也不害怕。她认定只要肯去做这件事,就一定能做到的。
在音乐里,她是一个勇敢、自在、快乐、有抱负的女孩子,可是一回到课堂上,她立刻就六神无主,昏昏欲睡。面对老师鄙薄的眼光,她还很自卑。因为她知道老师们都在怎么想她。他们和妈妈一样,认为她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对自己的未来,没有规划。想都不用想,就会知道,她今后一定会有一个失败的人生。
果真,听吧,妈妈已经开始说了:“你总不想学你爸爸吧?他那样糊涂,那么对自己没有要求,看看现在……”
乔茵甩手:“少拿爸爸说事,至少他对我,比你对我要好。”
这话,如一把锤子,重重打击到了万紫。她松了手,一时间连站也站不稳了。她扶住了头,身体摇晃起来,乔茵见她这个样子,不像是装的,再不扶一把,可能人都会倒在地上。她抱住了万紫,嘴里喊着:“妈,你怎么了?你真的生病了吗?”
她扶着万紫向沙发上走去。万紫一头栽在上面,眼冒金星。一下午的呆坐,加上刚才的着急,她的脑袋里像是塞满了沉铅。她怎么也抬不起头来,同时感觉到思维混乱,不知道接着该说什么。
乔茵居然对她说,陈先旺对她比她对她好。
她是因为接受不了这句话,才轰然倒塌的吗?可是,这话只是乔茵在说她的感受,你万紫又有什么不能听的呢?她说她的,你听你的。自从你离开了女儿,你需要面对的解释,就实在是太多了。她难过,只是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而已,可是想想女儿,那么多年,那么多重要的岁月,都是跟陈先旺一家在一起的,她说出这样的话,又有什么不对呢?她不是比你万紫,对此更有发言权吗?
可是万紫不愿意啊。她简直恨不得像林黛玉一样,一口吐出鲜血来,让苍天明鉴。她多少次,都忍不住要说说陈先旺和他父母的坏话,说说她自己的委屈。可是她全都憋回肚子了。她就是在为乔茵着想啊。
她不愿意让乔茵的心里,留下对亲人的不满,那会是一些人生的阴影,一旦留下,变成性格中的缺陷,就很难销蚀。
她不能告诉乔茵,多少个假期,每当她想带孩子单独出门几天,给自己和女儿一些时间相处时,陈家总是会冷嘲热讽地拒绝她。
她也不能告诉乔茵,多少次,乔茵读书上学买衣服,陈先旺赌输了钱,就打电话叫万紫出钱。万紫为了安抚陈先旺,从不敢对他父母讲这钱是她怎么省吃俭用省出来的。
她更不敢对乔茵讲,陈先旺有多么喜欢乱搞男女关系,在娶她这个年纪轻轻的小继母之前,还和多少个女人拉拉扯扯过。
在那些日子,她明知道陈先旺有问题,却不能说出自己的愤怒来。她生怕他们会把气撒在乔茵的身上,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心只想快点出头,把孩子接到自己身边来。
多少个日日夜夜,她都是喊着乔茵的名字入睡的。在北京近十年的时间里,她反复想过自己的人生,每一步,她都觉得后悔懊恼,唯独乔茵,让她充满了对上天的感激。
乔茵是她手心里的宝,比她自己的生命都要重要。她的一切努力,只因为有了乔茵,才有了意义。
可是乔茵说,她待她没有父亲待她更好。
她默默吞咽着口水,想让头疼能减轻一些。她终于想到该怎么对乔茵说了,她说,既然你更愿意听你爸爸,还有爷爷奶奶的话,那我们打电话给他们,让他们来说说,你不上学对不对,好吗?
不,乔茵又不傻,她怎么会不知道自己将迎来怎样的暴风骤雨。
她说:“妈妈,你感觉好了吗,我去洗澡了。我实在是太困了。这事明天再说吧。”
她语气坚决,平和之中,又有些不屑。这让万紫意识到,这个女儿,实在是太不好控制了。她对自己的情绪,把握得当,甚至比她还要从容。她很会在危急关头搞平衡,而且她吃透了她,知道她不会对她做出什么要命的事情来。
乔茵去洗澡了。进浴室之前,还大声对万紫回了一句:“你要嫌我多事,把我送回成都去吧。”
水哗哗地响着,传到客厅里来,万紫一片茫然,这一回合,她显然一败涂地。她怎么就说不通女儿呢,女儿怎么就敢一点也听不进去她的话呢?
她吃她的,喝她的,用她的,花她的,却比她还要理直气壮地收拾她?她要学音乐,就可以不上学?这么说,她逃学,还是她万紫逼的了?
问题出在哪里呢?
她苦思冥想,想找出一句话,让孩子哑口无言。然后,她就可以乘胜追击,让她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
她听见乔茵出来了。听见她抄起了电话,声音很大,是给那个叫遥遥的女生打的:“我今晚不回来了。明天?明天当然就回来了。”
万紫跳了起来。明天,明天她还要去遥遥那里?几个男生,几个女生住在一起?遥遥的父母,到底是干什么的?这几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又是怎样的?为什么没有大人管呢?
不行,她绝对不许乔茵再这样下去了。她得想办法,她不能让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她把她这个妈妈,当做什么人了?
她追过去大声说了一句:“明天在家给我好好待着,哪里也不能去!”
乔茵没有理她,转身进了房间。门嘭地一声,关上了。
万紫这才想起什么来,跑进厨房看,锅里的面条,早已经烂成了一堆。味道,都不是那个味了。
她一边铲起来往垃圾桶里倒,一边咬牙切齿地恨自己:“让你没用,让你没用。”
她发誓,明天一天,非得把那几个孩子的情况搞清楚不可。所有的问题,就出在这搞不清楚上了——她以为学校能管住周一到周五,她可以管住周六到周日,可事实呢,从周一到周日,敢情她全蒙在鼓里哪!
这都是什么世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