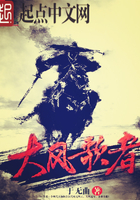这时,在离舞池不远处的另外一张桌子那里,有两个女人不仅关注阿乔的举动,而且关注柳绍禾对于阿乔的举动的反应。这两个女人,是年纪约在三十岁左右的金发暗娼t和y。
暗娼t对暗娼y笑了笑:“那两个家伙虽然都很年轻,但毫无疑问,跳舞的那个是风月场上的‘老油子’,静坐沙发的那个是不懂风月的‘小木雏’。”
暗娼y向阿乔跳舞的方位以及柳绍禾静坐的方位望了望:“那你说说,是‘老油子’有趣味一些,还是‘小木雏’有趣味一些?”
这座赌场的规模比较小,然而装潢得熠金烁彩,连赌具都是通过现代化的工艺制造的。至于赌博的方式——“轮盘押注”和“扑克押注”,却很古老,在法国可能流传了好几个世纪了。此时,约有十多个赌徒正在押注。赌徒里面有亚裔,有西方白种人,还有黑种人。
阿乔在收银台换了五百法郎的筹码,全部交给柳绍禾,又向柳绍禾解释了“轮盘押注”和“扑克押注”的赌博方法,接着怂恿道:“阿柳,你要放开手脚、勇敢押注,不要畏畏缩缩、小家子气!”
柳绍禾受到鼓舞,紧了紧眼神,颇为果断地押了第一注,赢了一百五十法郎。
如此“开门红”,使阿乔乐不可支:“阿柳,真牛啊,继续!”
柳绍禾押出第二注,赢了两百法郎。
阿乔在一旁激动得手舞足蹈:“阿柳,来劲啊,加油!”
柳绍禾的手气还真不错,竟然注注皆赢。那些输了钱的赌徒见此情景,纷纷发出羡慕的感叹声。柳绍禾在总计赢了一千法郎的时候,揩了揩脑门上的热汗:“阿乔,适可而止吧,我累了。”
阿乔赌兴正酣:“押注,就得讲究趁热打铁、乘胜出击。你再押它几注,会赢更多的钱咧。”
柳绍禾说:“我没想到,赌博竟然这样使人容易疲劳。”
阿乔说:“你这是第一次上阵,所以觉得疲劳。以后多来几次,就不容易疲劳了。”
柳绍禾说:“我尝试了这一次,就够了。我以后不会再进赌场了。”
阿乔说:“你的赌运多好啊。第一次上阵,就赢了上千法郎。”
柳绍禾的意志不为所动:“这不过是巧合罢了。我是不信什么赌运的。我对赌博永远不会有兴趣。我们走吧。”
阿乔恨铁不成钢般地叹了一口气:“可惜啊,可惜。”他拿着作为本钱的五百法郎的筹码,以及作为赢款的一千法郎的筹码,到收银台换了一千五百法郎的现金。他递给柳绍禾一千法郎:“阿柳,这是你赢的,收下吧。”
柳绍禾立即推辞:“我们不是讲好了吗?无论输赢,都算你的。再说,我如果收下这笔钱,就等于承认自己真的是赌徒了。”
阿乔只得揣回那一千法郎,很感激地说:“阿柳,那我就谢谢你了!”
柳绍禾显出一副轻描淡写的样子:“不必客气。这不过是游戏罢了。”
阿乔说:“我们现在就去迪厅。我请你欣赏欣赏我在迪厅的舞姿,还能消除你刚才押注时的疲劳咧。”
柳绍禾说:“那好吧。”
阿乔自己往常赌博的时候,总是输多赢少。现在,阿乔凭空得了一千法郎的赢款,心里十分欣喜,因此不乘公交车,而是打了的士,将柳绍禾带到了一座比较豪华的迪厅。门票、饮料等等费用,自然都由阿乔支付。
这座迪厅的舞池比较大,而且安装了好几个供人单独跳舞用的比较高的小圆台:既有迪厅的职业舞女只穿了“比基尼”在上面表演,也有临时起兴的男女舞客站到上面单独过一把劲舞之瘾。舞池里的舞客们舞成一片,加之电子舞曲节奏很快、分贝很高,所以气氛很是热烈。
在离舞池不远处桌子旁的沙发上,阿乔与柳绍禾坐着喝饮料。
阿乔一边喝饮料,一边却随电子舞曲的节奏颤动着双腿:“阿柳,要不要到舞池里去扭几下?”
柳绍禾摇了摇头:“我没那个习惯。”
阿乔放下饮料,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并把上身外衣脱了,递给柳绍禾:“那我就去扭了。这衣服,你给保管一下。”
柳绍禾笑着接过阿乔的上身外衣:“祝你扭出水平来。”
阿乔先是夹在舞池的人群里左扭右扭,同时物色值得自己上去过瘾的小圆台。终于,他发现有一个小圆台很具刺激性。
那个小圆台上的金发靓女只穿了“比基尼”,正自陶醉地使劲扭着魔鬼般的美丽身材。阿乔一鼓作气地站到那个小圆台上,在金发靓女的近旁比较有分寸地扭了起来。
金发靓女对于阿乔的到来似乎没有察觉,只顾半眯着眼睛陶醉在自己的舞蹈之中。但阿乔渐渐狂野了,动辄用手背蹭一蹭金发靓女的大腿,或者用手掌摸一摸金发靓女的腰腹,并且频率颇密。金发靓女一边扭着舞着,一边尽量躲闪阿乔的进攻,然而越来越躲不赢了。
情急之下,金发靓女停止了舞蹈,向阿乔厉声喝斥道:“你必须管好自己的双手,先生!”可阿乔装作没有听见,仍然我行我素地扭着、蹭着、摸着。
舞池里有些舞客发现了这一幕,于是起哄地尖叫了。
这个当口,走来一位身穿保安制服的大个子黑种人,将阿乔从那个小圆台上拽了下来,并且顺手将他搡进了舞池的人群里。
柳绍禾已把刚才的一幕看得清清楚楚。对于阿乔的这一番举动,他感到又好气又好笑。他想尽快离开这里,无奈还要保管阿乔的上身外衣,走不开。
这时,在离舞池不远处的另外一张桌子那里,有两个女人不仅关注阿乔的举动,而且关注柳绍禾对于阿乔的举动的反应。这两个女人,是年纪约在三十岁左右的金发暗娼t和y。
暗娼t对暗娼y笑了笑:“那两个家伙虽然都很年轻,但毫无疑问,跳舞的那个是风月场上的‘老油子’,静坐沙发的那个是不懂风月的‘小木雏’。”
暗娼y向阿乔跳舞的方位以及柳绍禾静坐的方位望了望:“那你说说:是‘老油子’有趣味一些,还是‘小木雏’有趣味一些?”
暗娼t似有满腹经纶:“若论床上的新鲜感觉,应该是‘小木雏’有趣味一些。若论钱财上的含金量,应该是‘老油子’有趣味一些。”
暗娼y兴致盎然:“理由呢?”
暗娼t说得头头是道:“‘小木雏’在床上的经验,自然比不过我们。我们和‘小木雏’上床,就不是‘小木雏’玩弄我们,而是我们玩弄‘小木雏’了。不过,一般来说,‘小木雏’逛街消费的时候,身上不会携带很多钞票。至于‘老油子’,基本上都爱携带大把大把的钞票,到外面寻欢作乐。我们如果钓上了‘老油子’,就等于宰着了肥猪。可是,‘老油子’一般都是‘床上高手’,我们很难对付得了,结果往往是我们赔了身子白辛苦。”
暗娼y撇了撇嘴角:“未必像你说的那样。”
暗娼t侧了侧脑袋:“试试?”
暗娼y耸了耸肩膀:“试试就试试。”
暗娼t建议:“我们明确分工:我这回不图钱财,只图那个‘小木雏’的新鲜感觉;你若有把握,你就去对付那个‘老油子’。怎么样?”
暗娼y很妖冶地打了个响指:“一言为定,各自行动。”
此刻的阿乔,虽被暗娼y盯上了,却浑然不知,仍在舞池的人群里心猿意马地扭着。他的目光一直瞟向那个小圆台上的金发靓女,极想再次上去蹭啊摸啊,但他知道又将被迪厅的保安强行拦阻,使自己讨个没趣。他很扫兴地从舞池返回到柳绍禾身边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柳绍禾要用言语敲打敲打阿乔了:“你刚才的闹剧,我都看见了。你在大庭广众之中,干出这样下流的事情,丢人现眼,我都为你脸红。”
阿乔恬不知耻:“小事一桩,用不着大惊小怪。人生在世,逢场作戏,只要自己快活就行。”他说着,余兴未尽般地瞄了瞄自己的手掌,似在回味刚才揩摸金发女郎腰腹时的那种“美妙感觉”。
柳绍禾掷回阿乔的上身外衣:“你以后如果还要干出这样下流的事情,我就不认你这个朋友了。”
阿乔一边穿着上身外衣,一边笑道:“呵呵,你这温州蛮子,还真的生气了。行行行,我以后不在大庭广众之中这样干了。但若关起门来干,应该不会丢人现眼吧?”
柳绍禾莫名其妙:“什么意思?”
阿乔腔调油滑:“你跟我去‘红灯区’尝尝‘洋荤’,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柳绍禾说:“你呀,看来是积习难改。你要去‘红灯区’,那是你的自由。反正我是不会去的。但我希望你可别惹上什么祸子。”
阿乔说:“你放心。我已是轻车熟路了,不会惹上什么祸子。”
柳绍禾从沙发上站了起来:“那我回店里了。”
阿乔看了看自己手机上的时间:“快到晚饭的时间了。你和我一起吃了晚饭再走吧。”
柳绍禾说:“不用了。我回店里吃。”
阿乔说:“你今天为我赢了上千法郎,我还没有痛痛快快地感谢你啊。”
柳绍禾不以为然:“我不是说了吗?今天进赌场,纯粹是我做的一次游戏,而且我以后不会再做这样的游戏了。所以,你别再提什么赢不赢钱的事。”
阿乔再次殷勤地建议:“那我打个的,送你回店里。”
柳绍禾自然不会同意:“我用月票坐公交车,方便得很。何必打的多花钱?”
柳绍禾与阿乔都购有巴黎公交车的月票。在巴黎,地铁和公交车皆属一个交通系统:人们购买了月票或者年票,既可以坐地铁,也可以坐公交车。
用月票坐公交车,当然比打的要省钱得多。柳绍禾自己每次上街,都是用月票坐公交车。阿乔却有些不同:手头宽裕的时候,比如赌博赢了钱,他眼里就神气得只有的士的份了;手头拮据的时候,比如赌博输了钱,那才蔫头蔫脑地将视线从的士移向公交车。
阿乔看柳绍禾不愿打的,于是假惺惺地谦虚了一通:“我真得学学你这温州蛮子勤俭朴素的好作风。我到巴黎打工已经五年多了,花钱总是大手大脚的,确实不应该啊。”
柳绍禾一针见血似地指出:“你这种言不由衷的遁词,已经在我面前说了很多遍了,几乎要将我的耳朵磨出茧子来。你还是自己说给自己玩吧,我走了。”说着,他走出迪厅,去乘公交车返回福稳中餐馆。
阿乔看柳绍禾走了,于是颇为滑稽地像法国人那样侧侧脑袋耸耸肩:“阿柳呀阿柳,你真是做不起种的‘窝囊废’哟。”他买了单,准备离开,打的去“红灯区”。
暗娼y翩然而至,一双碧眼半媚半嗔地逼视着阿乔:“怎么?见我来了,就害怕得想躲开!是不是啊,我的亚洲帅哥?”
阿乔一时措手不及:“噢……你……什么?我害怕了?我又不认识你,我为什么害怕?”
暗娼y单刀直入:“但我认识你!你是‘红灯区’的‘老油子’。”
阿乔恼羞成怒:“你这是血口喷人……”
暗娼y搔首弄姿:“你别急,也别装疯卖傻,我们彼此彼此。”
阿乔终于明白了对方的身份,遂将对方妖艳的身姿贪看了几眼。
暗娼y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你真是聪明人。我的姿色,我想应该能够让你动心。”
阿乔嗫嚅着:“我……我没有动心……”
暗娼y挑战了:“在我这样的巴黎女人面前,你不必虚伪。都说法国男人很虚伪,我看你们亚洲男人更虚伪。”
阿乔很不服气:“那……你不虚伪,你就直说:你要干嘛?”
暗娼y妖娆万状:“我送上门来了,省得你费神费力去‘红灯区’……”
阿乔止不住在心里打起了“小九九”:“这倒不错。但不知她的价钱会不会太贵……”
暗娼y仿佛看透了阿乔的心思:“这附近就有钟点旅馆。你玩两个小时,我随你怎么玩,只需五百法郎,而且房费包括在内……”
阿乔听了,正中下怀。他以前到“红灯区”玩妓女,基本上都是每个小时三百法郎;现在两个小时五百法郎,倒更划算了。他这样想着,不禁嫖兴骤涌,于是颇为老练地去拉y的手腕:“我们真是有缘了,这就去旅馆吧……”
不料,暗娼y将阿乔闪开了:“我有些担心……”
阿乔很是不解:“担心什么?”
暗娼y似很忸怩:“担心你‘吃白食’……”
阿乔赌气地将身上的一千多法郎都掏了出来:“你瞧好吧,我从来都不‘吃白食’!”
暗娼y故作委屈地让阿乔收起那些法郎:“嗨,收起来,收起来。我不过开了一个小玩笑,值得你生气么?”
阿乔自嘲地笑道:“呵呵,不生气,不生气……”
暗娼y这才风骚无限地挽紧了淫欲高涨的阿乔,动身前往附近的钟点旅馆。
色令智昏的阿乔,根本觉察不出暗娼y正在心里发笑:“这样的‘老油子’,其实太蠢、太幼稚了!”
此刻的巴黎,已是华灯初上的傍晚时分。
暗娼y与阿乔相偎而行的样子,被暗娼t远远地望见了。暗娼t知道暗娼y已经稳操胜券了。她很嫉妒暗娼y,然而因与她有言在先,所以不能来搅y的局。刚才,暗娼y和她分头行动的时候,她在迪厅的门口,倒是跟自己心目中的“小木雏”柳绍禾搭上了话,但她的勾引却被柳绍禾严词拒绝了,使她殊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