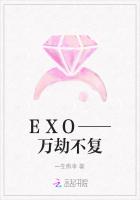我进新闻界,纯然是出于自己有意识的选择。
1934年,上海《文学》杂志通过郑振铎先要我写一篇《我与文学》。那是我平生第一篇自述。前一年(1933),我就已经从英文系转到新闻系。在文中,我谈的实际上是自己转系前的考虑:“除非是为了教文学或研究文学,我一点也不认为一个喜好文学的人有入英文系或国文系的必要。文学没有方程式,黑板画不出门径来。如果仅为个人欣赏,则仍应另外有个职业。不应让社会背起这份负担。如果是为创作,则教室不是适宜的工场。文学博士会写文艺思潮,但写人生的则什么士也不需要。”
接着我又从正面申述自己那次转系的想法:“我希望目前这点新闻训练能予我以内地通讯员之类的资格,借旅行及职务以扩展自己的生活视野。如果在经历中我见到值得报告给大众的,自己纵不是文人,也会情不自禁地提起笔来。如果我什么也不曾找到,在这大时代里,我至少曾充当了一名消息传递者。”
这就是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在投入报业时的一套逻辑,一份抱负。无论如何,现在回顾起来,在我考虑、设计自己的生活道路时,目标是明确的。
1933年夏天辞了福州的教职回到北京,我就是基于上述考虑,才从辅仁英语系转到燕京的新闻系的。
我是蒙族人。毕业之前,本来有个去内蒙工作的机会。当时主管内蒙事务的傅作义将军看了我的《平绥琐记》,曾通过吴文藻老师约我见一面。也许为了表示器重,他要给我个小官做做。可是把我吓跑的,正是他这番礼遇。我早就拿定主意,此生绝不当官。
我进《大公报》,一点也不偶然。1933年10月,我的第一篇小说《蚕》就是发表在《大公报·文艺》上。那时编者沈从文先生要我每月交他一篇。我写旅行通讯也是以《大公报》为起点。第一篇《平绥琐记》(1934)发表在《大公报》所办的《国闻周报》上。然而我是从1935年7月才成为它的工作人员的。自那以后,如果把在英国头五年的兼职算上,我同这家报纸的关系至少也有十五年。然而只在1935至1939年、以及1944至1946年这两段期间,我是它的专职工作人员,其余都属兼差。
《大公报》是我走出校门后的第一个岗位,也是我一生工作最久的地方。它为我提供了实现种种生活理想的机会,其中最主要的是通过记者这一行当,广泛接触生活,以从事创作。
1935年初春的一个下午,杨振声老师约我去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吃茶,在座的有沈从文先生和天津《大公报》的胡霖总经理。我原是在杨、沈二位主编的《文艺》上同报馆发生关系的,他们很自然地成为我的引见人。胡总经理个子矮胖,方脸上闪着一副度数很高的近视镜。和善之外,他给我的印象是精明,表现在听人讲话时注意力十分集中,而回答时干脆果断,不拖泥带水。
当时《大公报》除了以青年知识界为对象的《文艺》,还办了个以小市民为对象的《小公园》,先后由何心冷及马二先生主持。另外,报纸还有十一种由社会上的专家学者主编的学术副刊,如《艺术》(画家司徒乔编)、《哲学》(哲学家张申府编)、《史地》(地理学家张其昀编)等,胡总经理当时想物色的是一个既编《小公园》,又兼管那十一种副刊发稿工作的人。其实,这并不完全符合我的设想。但是我明白一个青年初出茅庐,不能挑肥拣瘦。同时我也估计到,倘若把雇主规定下的任务全完成后,提出额外再讨点活儿干,他只有欢迎,决不会拒绝的。因此,我就问:“要是我能预先把《小公园》编出若干期,您肯不肯临时找人替我发发旁的副刊,放我做点外出采访的工作?”老板听了,知道他收下的大概不是个懒汉,就眉开眼笑,一口答应了我这个要求,并且说定7月1日走马上任。
每年快到放暑假时,总有一些通讯社和报社到我们那个新闻系来物色人材,胃口最大的是国民党的中央社和《中央日报》。那阵子走进系办公室,就觉得像个谈生意的交易所,或者更像个骡马市。来聘者不免对同学要评头论足一番。毕业班有两位是夏威夷来的华人,我和他们都属于早已有了婆家的,一时感到格外轻松。
领到文凭后,我足玩了几天。去天津上任那天,在火车上刚好坐在一位低班女同学对面。她问我这是去哪儿,我兴冲冲地告诉她,是去我一直向往的一个地方。
北平之外,以前我曾到过上海、汕头和福州。这是第一遭去华北大商埠天津。一出东站,人山人海,乱嘈嘈的。同北平的东车站差不多,只是街道窄多了,人讲话嗓门大多了,这里胡同变成了“里”,街变成了“道”。洋车一拐弯,进了英租界,立刻整齐许多。只是同上海一样,站岗的都是些头上扎了红布、满脸胡子拉碴的印度巡捕。又一转,进了日租界。窄巷里挂的净是些写有妓女艳名的木牌。一下子就又拐入了《大公报》所在的法租界。洋车拉到三十号路,就在临街的一溜两层灰砖楼房跟前停下了。一抬头,《天津大公报》的木牌赫然在目。
我想象中的大公报馆是一座高大楼房,里面一个个房间门外都掛着什么什么版的牌子。万没想到这家大报馆竟然那么简陋!编辑部在二楼,只是个长长的统间,一排排地摆了五排三屉桌。迎门两排是由曹谷冰、许萱伯和王芸生坐镇的要闻及社评版(胡政之和张季鸾两位老板另各有小办公室),然后是国际版的赵思源、马季廉和费彝民,再进去是本市版的张逊之、何毓昌和高元礼。副刊和体育等在最后一排(所以是“报屁股”!),校对和译电人员则挤在角落里。
胡老板把我作为“生力军”——介绍给各版的同事——那是下午,上白天班的全在,上夜班的也来照个面儿。我同他们一边握手,一边彼此打量着。
编辑部里这时正弥漫着浓烟,到处还飞着煤屑。原来它的正对面便是法租界的发电厂,报馆就在发电厂那高大烟囱的阴影下。我是刚刚来自山青水秀的未明湖畔的。对这霉湿、拥挤、泛着机器房臭气的环境,立时感到颇不习惯。
宿舍是个方形房间。正好每个角落放一张床,中间摆一张公用的书桌。晚上会到屋友,才知道我们四人恰好来自四家不同的大学:南开、清华、北大和我这个燕大的。年龄相仿,同背景,自然很谈得来。他们大致向我介绍了这家报馆的机构:真正的东家吴鼎昌新近才辞去职务,去南京当实业部长了。他们也只见过一次。守在报馆的是胡霖和张季鸾,两位基本上是这么分工:胡主管经理方面事务,张主持笔政,但分工并不严格。下面究竟有几大金刚,他们也说不准,他们告诉我,《大公报》的一个特点,就是管经理部的有时也写社论,而负责编辑部的时而也过问经理方面事务。编辑部里好像分胡派张派,自然还有更硬的吴(鼎昌)系的人。不过,他们也搞不清,因为他们采取独善其身的办法,不参加报馆里的生日会,也不搓麻将。我听了,十分赞成。实际上,我们也成了一派——大学生派。
凌晨,我被连续不停的隆隆巨响吵醒了,连睡的木板床也被震得晃悠起来。以为发生了地震,就赶忙跳下床,把对过儿的那个北大屋友推醒。
“这是一楼在开机器印报哪。”他嘟囔了一声,揉揉眼又入睡了。
知道不是地震,我自然放了心,但一想到报纸天天出,机器每夜在这鬼时候开动,心里又不免发怵。
清晨,屋友一边漱口,一边宽慰我说:“日子一长就习惯啦。谁让报馆就趁这么一座小楼呢。”果然,很快我就对煤屑、烟雾以及隆隆声都习以为常了。我总幻想自己是在乘船,而且坐的是统舱。
原来那时《大公报》楼下是经理部,后边就是排字房和印刷间。
副刊工作有个优越点:既当报人,可又不必熬夜。那时编要闻和国际版的,都得等中央社及路透社、哈瓦斯社、德通社、美联社等外国大通讯社发完稿,再拼大版,看大样;时常还就当日新闻为三版写个短评,快天亮了才能回家睡觉。也正因为如此,我始终也没练出记者必须具备的熬夜这个本领。
每逢来到一个新地方,我总喜欢先勘察一下周围的环境,特别着意找个适宜散步的所在。出了报馆门往北走不多远,就来到繁华的天祥市场。一路看到墙上贴的除了“仁丹”广告就是治杨梅大疮药品的招贴。使我感兴趣的是鼓书大王刘宝全演出的海报。
我走进了天祥市场。这可能是仿照上海大世界修建的一座娱乐场所。一爿爿茶楼饭馆,倚门站着艳装的女招待,窗玻璃上贴着“谈心室”的原来是占卜处。叫卖最响的是“大糖葫芦”。好容易在三楼找到游艺场。一问,说刘宝全老板每晚要过午夜才出场!
我又往南探路。首先是一座红砖哥特式天主教堂。拐过去就是又脏又臭的墙子河。沿河走去,人行道倒是宽了,可这么臭,怎么能散步!我不死心,继续往前走。不知怎么一转,就转到通往八里台的伦敦道了。哦,总算找到一条供散步的路了!在《道旁》里,我曾这样描写过它:“道旁散栽着硕长多眼的白杨,地上蔓长着各种无名野草。远远地,东面剪平的一块草坪是洋商自建的跑马场,白栏杆上漆着距离的标志。邻近看台一带的花墙是万寿公墓。”
北京虽然也有中国主权行使不到的东交民巷,但那毕竟只是位于城南一块狭长地带。除了游行示威时向它举过拳头,那毕竟不涉及日常生活。天津可不然!走上一段就又是一国的辖界,等于每天都在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之内。
天津是个非常讲究吃喝的城市。报馆里有个生日会,三天两头聚在一起吃寿宴。有的能成斤地喝酒,有的是划拳能手,有的喜搓麻将。我们四个大学生相约,概不参加。人家在吃甲鱼喊“五魁手,八匹马”时,我们不是在伦敦道上散步,就是在踢足球。
好在从来没有人强迫我们去参加,我们也从未因而受到孤立。
接过《小公园》的编务之后,我立刻发现一个矛盾:拿起移交过来的稿子一看,才知《小公园》原来是个以传统曲艺及旧闻掌故为主的副刊,下面满是五花八门的广告:从航空彩券到性药和火车时间表。刊物上登的有关跑马、回力球和围棋,我都外行。待用的存稿如“七夕考证”,“小白玉霜的艺术观”和正连载着的“剧坛”以及探讨戏曲源流版本的文章,我都既不懂,又不感兴趣。当胡老板问起我接编后的情况时,我就据实地把我面临的矛盾对他讲了,觉得由我来编这样刊物怕不对头。
至今我仍记得胡老板那席使我大为开窍的话。他说:
“你觉着不对头,这就对头了。我就是嫌这个刊物编得太老气横秋。《大公报》不能只编给提笼架鸟的老头儿们看。把你请来,就是要你放手按你的理想去改造这一页。你怎么改都成,我都支持你。”
我听罢着实兴奋了。可转而又想:抽屉里还有那么一大叠存稿,是给老头儿们看的呀。问他怎么办好,他眼睛滴溜转了一下,说:
“总得有个新旧交替的阶段嘛。约好的稿子当然不便于退。这么办吧,你就把那些登在刊物不起眼的位置。登完了为止。你可以在刊物上公布你的新的大政方针。这样,一看换了人,变了样,旧的也就不来了。”
胡总经理真是位有魄力的事业家,又碰上我这个二十几岁愣头愣脑的小伙子。我就真地大干起来了。
然而把一个老头儿看的刊物变成青年人的,并不如我想的那么容易。七、八两个月,在友人巴金、勒以和凌叔华的支持下,我挽袖子认真闯起天下了。知名作家如叶圣陶、冰心、知堂、光潜、巴金、靳以、芦焚、健吾,还有更多更多当时还不怎么知名的文艺青年如柳杞、韦芜,以及今天在台湾享有盛誉的张秀亚的名字,陆续在《小公园》上出现了。我感谢他们的支持。
然而每天成批地寄到的来稿,却大都属于中学作文水平。怎么办?我自己是投稿人出身的,那时也还是个文艺青年。我充分体验过投稿人的种种健康和不健康的心理,以及他们的心血变不成铅字、见不到天日的苦恼。我决心要让手里这《小公园》成为千千万万个文艺青年自己的园地,然而我又不能在质量上对文章过于迁就。
于是,在一封《致文艺生产者》的信中,我首先以过来人的身份,对投稿者表示了深切的理解:“天气是这样热。别人都寻凉快去了,他(投稿者)却得独自躲在屋子的一角,对着一叠白纸发愁……写就之后,他小心翼翼地封进一个信袋里,生怕别人和他作对,自己亲身把它寄了。从那时候起,他的心跳了。见着人不免脸红了。一向不大看报的他,竟沿街迎接起卖报孩子来。见了报纸眼睛竟不自抑地眩晕了。那种关切的心情初写东西的人是都曾经验过的。这个刊物的编者也不例外。”
然后就谈到取稿的标准:“文章不像布匹,原没有固定尺度来衡量。但不能衡量并不是可以马虎。好的文章,像一切好的艺术品一样,一看便能辨认得出。像尊名窑出的瓷器,好的文章有着一种光泽:也许是思维的透彻,也许是想象力的奔放,文字间焕发着光彩。然而这样的文字我怎样瞪大了眼睛也见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