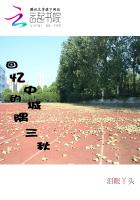柳岸坐在自家别墅的露台上长久地陷入一种沉思之中,紧锁的眉头一直没有舒展开。这幢别墅通体白色,结构颇有欧陆风格,回廊曲折幽深,二楼向水的一面伸出了一个大露台,四周绿树葱茏,南面有一个人工挖掘的弧形水池,里面栽种着睡莲,正有些零星的白色或紫色的花朵悄然开放着,池水不是十分清澈,但可以看到水面下有一群群色彩缤纷的金鱼在四处游动着。
这座别墅是柳岸在制衣厂步入全盛时期在柳镇买下地皮自己请人设计建造的,长期以来,成了他一个身份地位的极好象征,每次从公司回到自己的别墅,他心里总会有一种特别踏实的感觉,仿佛是走进了一个万世永固的城堡,他可以在这个城堡里安度无尽祥和的岁月。现在,这城堡竟然有点摇摇欲坠了。这么多年来,他这还是第一次陷入这样巨大的不安之中。
“爸爸,你该吃药了。”这时,柳笛端着一杯白开水,手里拿着一个药盒走过来说道。
“你先放着吧,待会儿我自己会吃的。”柳岸见女儿要拆开药盒拿出药丸,就对她挥了挥手。
柳笛顺从地住了手,看着她爸爸,说:“那你可要记住了,昨天的药就忘了吃,这样对身体不好的。”
“知道了,你去忙你的吧。”柳岸有点疲倦地垂下花白的头颅,昨晚他好像又是一夜没合眼。
“爸爸,公司的事你不用发愁,有我呢。”柳笛走了几步,又回转身,走到她爸爸身边安慰道。
“我没有操心公司的事,你放心。”柳岸说,声音里透着苍老和无力。
见女儿出了门,柳岸才长长地叹了口气。其实,他这些天一直在担心着女儿公司里的事,三百万订单被跳蛋龙公司抢走,加盟的米尼可尔公司又要终止与稻草人的合作,工人工资上涨了许多,这都让女儿的公司面临着巨大压力,简直可以说是四面楚歌,作为稻草人制衣公司的创始人,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他毕竟上了年纪,人不服老不行,对公司陷入这样的窘境,他这个原来的掌舵人也是一筹莫展。稻草人从起步发展到今天,他付出过无数的心血和汗水,就如同是一个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孩子,他怎能忍心看着稻草人就这么垮掉?
十六年前,在BJ帮人家卖过五年羊毛衫的柳岸和妻子在柳镇金兜村的自家房子里,买了几台缝纫机,雇了几名工人,开始做童装。那时候在柳镇做服装的人中,外地人占少数。他最初的创业经历,跟现在的外地人同样艰苦。他是靠借来的一万元起家的,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是自己动手,裁剪、踩缝纫机、钉纽扣、包装,晚上几乎不上床睡觉的,常常是做到凌晨两三点钟,累了就躺在裁床上。在作坊里当厨师的也是他,节约时间的办法是,搞个大冰箱,一次性买上两三天的菜。
最初的三年,他每天差不多只睡两三个小时。早上4点起床,几个人合租一辆小车,去外地的批发市场把坯布买回来。一般是带上5000块钱,买上五六匹布,这样够做两天。
柳岸的大跨越是从第六个年头开始的。那时,他已经从有点偏远的金兜村搬到了柳镇德盛路271号,有个朋友把带两个门面的房子租给了他,而且租金可以等赚了钱再付。而他这个做面料生意的朋友让他在搬来镇上的第一年就欠下了四十万元的面料钱,这笔债务一度压得他有点喘不过气来。不过,他翻身很快,第二年他就将欠的钱还清了。三年后,他的工厂已经有四五十名工人,还买了三间门面楼以及柳镇街头第一辆奥迪车。十年前的生意都很好做,一年就做三四个款式,一个款式能做七八万件。
此后,他服装生意的快速发展一直在持续,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台阶。又过了两年,柳镇开始修大兴路,搞产业园区。作为镇上的童装“典型企业”,柳岸拿到了一块15亩的地,凭借手中的四五十万元现金,用房产拿到的抵押贷款以及客户预付的货款,付清了100多万元的土地款,随后也盖起了现在的厂房,从那时起,他就和柳镇街上的“四合一”工厂店彻底告别了。
柳岸自认他的公司在产业园区的四五十家规模服装企业中,可以排到前五名。他的企业不需要向柳镇的工厂店及加工厂下单,也没有其他生意往来。他已经进入另一个周期,工厂店老板们一天十几个小时的超长工作时间,对他来说已成过往。他一般早上八点半来办公室,下午5点钟会准时回到家里,生活看起来自在悠闲。
在他工厂里打工的的工人,每月能拿到三千至五千元,像裁剪工这样的技术性岗位或者少数熟练车工甚至可以拿到五六千元。他不知道童装带动了多少产业,养活了多少人。柳镇周边一带,田地全部被征用了,像他这个年龄段的村民,以前家里基本上都是做衣服的,现在不做了,就靠安置房的租金生活。没有其他收入,烟要抽中华的、车要开小车,没事就闲逛,打牌,日子过得跟神仙似的。
可柳岸清楚地意识到,危机正在悄悄逼近。做童装这一行,也是一个靠天吃饭的行业。这两年的暖冬,让柳镇童装老板们的冬装生意大受影响。当然,天气因素是整个服装业都要面对的,柳镇童装工厂的突出问题是款式少,走的是单件大批量的批发销售模式,每天等着客户上门打货。这是一种不确定的生意,“船小好掉头”,但船太小也很难跑得远。
柳镇的童装工厂都是密集的小作坊,无论是加工厂、工厂店还是大兴路一带规模化的大厂,都是在实行整件加工模式而不是流水线生产,这是与批发销售模式相适应的生产方式。
让柳岸最忧心的是,除了产区名气,柳镇服装说不上有品牌。在柳镇的工厂区找人得说“XX街XX号”,而不是报厂名或者品牌名。在大兴路一带的街上看到,“赛格格”、“小米兔”、“登卡亮”等不假思索的商标修辞比比皆是,这些名字一般都是店家随便起的。
好在这两年女儿柳笛接手稻草人开始做起了品牌规划,她去英国留过学,喝了点洋墨水,眼界比他开阔,正在启动连锁专卖的“稻草人”,已经在全国各地开起了30家直营店。女儿曾经信心满满地跟他说过,这个牌子在5年内可以成为全国知名品牌。可要做成全国品牌又谈何容易啊,别的不说,就是人才的引进就是大难题。现在的人才,包括做设计的,做营销的,做管理的,更愿意去SH、杭州,谁愿意到柳镇上来?现在他们的设计师都是内部培养的,几年前就跟杭州的美院挂钩,在他们这里搞实习基地,然后才慢慢留下了一些人。
这个产业做到这个份上,再怎么发展,柳岸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柳镇童装业是一个年轻的产业,产销量上亿的没有超过两家。但互相之间的竞争已经白热化,这次跳蛋龙对稻草人虎口夺食,就是一个最明确的信号。稻草人如果不奋起反击,那只有坐以待毙了。
“绝对不能让稻草人这个品牌倒下!”柳岸想到这里,抡起拳头在桌角狠狠地击了一掌。
太阳从高大的梧桐树梢上升过来,露台上洒满了金黄的阳光。置身于阳光中的柳岸身上那些正在萎靡的细胞似乎瞬间被激活了,整个人一下子年轻了许多,他抬起眼睛,目光越过水池边飘拂的垂柳和外墙边高大的梧桐树,望向柳镇湛蓝而阔大的天空,一直紧缩的眉头也渐渐舒展开来。
柳笛从家里出来,心事重重地走到街上。父亲的糖尿病让她很揪心,这都是当年打拼厂子的时候落下的病根。可让她揪心的还不仅是父亲的病情,父亲和母亲二十多年来的感情不合才最让她揪心。
按理说,父亲和母亲,一个郎才一个女貌,正是天作之合,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两个人碰到一起就像是点着了火药桶,总是要吵个昏天黑地、两败俱伤才肯罢休。一开始,她年龄小,对父母经常吵架的事懵懵懂懂的,后来上了初中渐渐有点懂了。她听说曾经是村里一枝花的母亲在嫁给父亲之前,竟然有一段初恋,后来她的初恋去东北当兵了,他们俩也就断了。母亲嫁给父亲之后,生下了她,又在村里办起了一个服装加工厂,日子渐渐红火起来。可是好景不长,母亲那个当兵的初恋情人复员转业到镇政府谋了个差事,时间一长,他很自然地找到了她母亲,两个人旧情复燃,有一次两人正在镇政府他的宿舍里幽会,被跟踪而来的父亲堵了屋子里。那年她正读初三,快要中考了,晚上放学回家得知此事,她做出了一个让她至今想起来还后悔莫及的举动,当时听了父亲的诉说之后,她冲到母亲跟前,挥手重重地给了她一个耳光,母亲漂亮的脸孔上立刻起了几个红红的手指印,她捂住脸惊愕地看着女儿。直到现在,母亲那一刻的眼神还深深地嵌在她的心里,像在一块白布上泼洒的油污,怎么洗也洗不掉。后来,母亲虽然原谅了她,但她心里一直为此自责。只是母亲那个初恋成了他们家幸福生活不可逾越的一座山,不管母亲怎么承诺再也不会跟他有什么瓜葛,但父亲的自尊和信心显然受到了致命打击,他再也不相信母亲说的话,这些年父母之间的冷战一直继续着,带给这个家的是一种彻骨的寒冷,虽然他们家住上了别墅,有了很多钱,但恰恰没有她要的温暖和幸福。这场冷战最终导致了母亲和父亲分居,但他们一直没有离婚,因为父亲一直不同意。其实他是不愿意自己的失败,他实际上败给了母亲的那个初恋,现在这个人已经是柳镇的副镇长,还是分管企业的副镇长,这个人她也必须经常和他打交道,为了稻草人,她无法绕开这个人。这也许是宿命吧,明天她就得去找他,为了在柳镇新建的童装城里能有稻草人的一席之地。
“所有的压力都来了!”柳笛咬着牙,感到肩头沉沉的。太阳照在她的脸上,她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多出一个刺儿头何天龙,跑了一个得力助手李少阳不说,现在是生产旺季,而厂里却人手不足,眼下当务之急是得去街上看看能不能招到一些熟练的工人。前几天,厂子里又一下子走了十几个工人,都是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走的,其中还有好几个是技术非常熟练的工人,她一时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走。
在镇北街一路口,柳笛看到那儿聚集了一群外乡人,男男女女的,面孔看起来都很年轻,显然是在这里等待着用工企业来挑选。
她走到一个头发梢染得黄绿相间的年轻人跟前,问道:“你是哪来的?”
“YN,前天过来的,准备找工作,在柳镇做了五年了。”小伙子回答。
“那原来的厂子怎么不做了呢?”柳笛问。
“工资低呗,谁愿意在一棵树上吊死?”小伙子扬了扬眉毛。
“那你要多少?”柳笛问。
“至少也得有个四五千吧?”小伙子瞄了她一眼。
“你是熟练工吗?”柳笛盯着他问。
“那当然了,我做裁剪都五年了。”小伙子的语气里明显有几分自豪和得意。
“好的,我要你了。”柳笛说,“你把手机号码留给我。”她对小伙子说。她知道这两年柳镇服装企业工人的工资虽然已经比以前涨了好多,但工人们的胃口好像越来越大,企业不涨工资要招到熟练的机工是很困难的。现在养个机工要七八千每月,剪裁要七八千每月,打零工三千多每月是最差的,每半年涨一次,再这样涨下去,他们这样的童装企业老板都得关门回家种田去。
但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工人的工资在涨,生产成本也在加倍往上翻。去年前年的棉布九块、十块,现在是几十元了。柳镇童装以前主要靠价廉物美取胜市场的,到如今优势已经很少了。他们稻草人上半年销售额还不错,但是企业效益出现了明显下滑。这真叫看上去很美,其实内瓤子都上来了。
脚穿在谁的脚上,谁知道这鞋子硌不硌脚。
柳笛又一口气问了好几个外乡人,他们大多来自SC、GZ、YN一带,开口要的工资都不低,没办法,现在是他们的天下,柳笛心里想的是招到技术熟练的工人就行,别的她现在没心思去考虑。
这招工人的事原来不用她亲自操心的,但负责招聘员工的公司副总安雅最近到外地出差了,她干脆就自己来找,何况她顺便想找找李少阳,李少阳因为受了春妮妈妈的羞辱一气之下辞职跑掉了,她很是舍不得这样一个人才,可打他的电话一直是处于无法接通的状态,难道他一下子从人间蒸发了不成?她知道表妹一直爱着李少阳,一直放不下他,在潜意识里她还是希望能帮表妹把李少阳给找回来,如果李少阳还没有离开柳镇,她应该能找到他的。
和几个工人谈好之后,柳笛沿着街道向自己的公司走去。她很喜欢这样不开车,一个人走走,把自己淹没在柳镇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这个小城人口还在疯狂的膨胀中,外来人口像潮水一样地不断涌进来,现在真的是人满为患,大街上到处都是横冲直撞的车辆,运送布匹服装的三轮车比比皆是。在她的印象中,柳镇不应该是这幅样子的,在她小时候,柳镇就是一个烟雨迷蒙的安静的江南小镇,她可以撑着一把伞,在那条铺着青石板的路上走上一个下午。
现在,一切都变了,那个宁静的江南小镇不复存在了。
她是开了一家服装公司,被人称为老板,是有了点钱,但却陷入了无尽的烦恼中。
眼下,不光是工人的流失,跳蛋龙公司对她的挑战,还有米尼可尔要收回他们的加盟权,更令她头疼的是新厂区的扩建。这段日子,她东奔西走,从贷款融资到地皮审批,她跑了很多部门,冷脸也看了不少,感到有点心力交瘁,一个女人,想做成一点事情,比男人付出的要多得多。父亲已经老了,还有糖尿病,公司这副重担都加在她一个人柔弱的肩上,她不知道自己到底能撑多久,但只要她还有一口气,她就不会服输,会一直顽强地走下去。
正走着,她的手机响了,她低头一看,是焦森打来的,眉头不禁皱了起来,随即按了拒接键。可手机立马又响了起来,她只得无奈地按了接听。
“焦总监,什么事啊,我正忙着呢。”她没好气地说。
“你晚上空吧,我们一起吃饭。”焦森在电话里说,是那种半中不洋的语气,他是米尼可尔SH总部派到稻草人的技术总监。
“我没空,最近有点忙,过几天再说吧。”柳笛说,心里一下子烦乱起来。她对焦森的追求越来越反感,平心而论,焦森长得也挺帅,还有几分混血儿的味道,但与何天龙相比,焦森身上缺少一种男人的阳刚之气和直率坦诚,那种黏糊糊的腔调她很不喜欢,但碍于他是米尼可尔的人,她也不好明着得罪他。
“我都约了多少回了,你总是说没空。”焦森说,语气里好像带着一点火气。
“那你就不要约我了啊,我真的很忙,你也知道的,最近公司里的事情太多了。”柳笛说,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难道加盟米尼可尔的事情就不重要了?”焦森反问道,话里藏锋。
“也重要,但事情要一样一样来。”柳笛见焦森是要挟她的口气,心里窝着火,她真想痛痛快快地说出一句“不加盟你们米尼可尔又怎么样”,但她还是在心里将这股火气给死死地压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