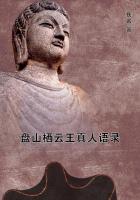(姜越)
认识念荷那年我十岁。
在周国,不是纯血统的孩子,一出生就会被上天诅咒,注定得不到垂帘。我的父亲是周国人,母亲却是南朝人,我对他们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只隐隐的知道,爹是个知书达理的文人,而娘,她的手很小很暖,每每总喜欢抚着我的脸说我很乖。
他们过世那年我才五岁,连方向爱恨都不太知道的年龄。也就是这样的年龄里,我守着他们的遗体,在空屋子里坐了整整三天。
原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总是很穷,为什么别人都有阿爷阿奶而我没有,为什么别人都有玩伴而我没有。后来,当我坐在街边一口饭都要不到的时候,终于明白了。
因为爹娘是不同国家的人,他们成亲了,就要被人抛弃排挤。而我,因为是他们的孩子,所以一出生就要被人指着脑门骂杂种,不能还口。
恨么?
其实那时候年龄小,又哪知道什么是恨?只是在每次被人欺负的时候捂着头哭。可每当我哭的声音大,打我的人就越用力。次数多了,我就不哭了。我笑。被打得满脸血时我笑,被饿得只剩一口气时我还是笑。
也许,就是这笑引起了她的注意。那个冬日午后,我躺在路边的石阶上,好几天没吃东西饿得只剩一口气。我想,我要死了,终于要去见天上的爹娘了,辛苦熬过的日子突然都有了价值,我发自肺腑的笑,笑出了声,然后眼光迷蒙中,我看见了她。
跟母亲一样小小的手,笑起来暖暖的。她将手钻成拳头向我递来,对我说:“给,这个给你,你拿去买东西吃。”
笑陡然僵在脸上,我皱眉,用能想到的,最凶狠的表情朝她吼。“走开!”她以为仅凭这点示好就能戏弄于我?我是很饿,饿到快死了,可也不会这么轻易上当,由人戏弄!
她有些怕,绣鞋一点点朝后退,却还是不肯走。小声道:“你别生气,我只有这些,等明天,我还来给你送。”说着就弯身,将她手中的耳坠子放到我脚边跑开了。
那是我第一次收到别人的恩惠。还是这般让人啼笑皆非的恩惠。一副耳坠子,怎么能解我的燃眉之急?如果拿去典当,别人会以为是我偷的,不但拿不到钱,还会挨一顿揍。拿去换吃的?结果恐怕还是一般无二。
如是想着,还是将它好好的收起。我奄奄的躺回原地,经她这么一闹,倒陡然精神了。手掌心,她的那副耳坠子灼灼发热,隔得我生疼。
第二日。她真的如约来了。
这次倒是实在很多,带了一大包肉包子来。我怔怔的看着她,没动手。她以为我是怕包子有毒,示范似的从中拿了一个往口里塞,噎得半天说不出话。
我笑。流浪后第一次真心的笑。她傻傻瞧着,半晌后说:“你笑起来真好看,以后应该多笑。”
这句话,我记了一生。直到被人数剑穿身时,仍笑着。主子说我傻,我却不觉得。这是我生活的全部。
后来,我知道她叫念荷,是跟着哥哥从南朝来的。我问她,南朝的女子是不是都像她一样温温软软,她摇了摇头,呲着牙唬我道:“谁说我温软,以后我若是成亲了,可是会把夫君管得死死的,若是他敢纳妾,我定是不饶的!”
我低着头笑。边笑心里边想,若是我能娶你,一定不纳妾,只专心对你一个。想着又摇头,觉着自己傻得紧。一个乞丐,我又能娶谁呢?
她却死死的盯着我瞧,拿手抓我的胳膊,忸怩的样子。“你以后会娶妾么?”
我愣住,茫然摇头。
她好像很高兴,起身空打了个悬儿,咯咯的笑。她说:“晌午饭后,我还来。给你带好吃的,你等着我!”
那是我见过最明媚的笑靥。照得我耳边发热,我不好意思的低头,轻轻的说了声好。
可我却没能遵守约定。那天,我遇见了大皇子。此生我第二个恩人。他说,我给你饭吃,教你武功,让你成为人上人。你可愿把你的命交给我?
说这话时他表情郑重耐心,没有旁人脸上惯有的鄙夷轻蔑。
我想了想决定跟他走。不是因有饭吃,也不是因雄心壮志。而是,他让我有被人尊重认同的感觉,那是我从未得到过的。
走之前,我再三的瞧她总出现的那个路口。大皇子问我怎么了?我却摇头。跨上马车,再未回头。
我想成为能配得上她的人。
待到那时,我定会去南朝找她,娶她为妻。
十年后。我成了周国最年轻的将军,也再见到了她。在最不合适的时机。
那日,我去南朝探营,被发现后无意间躲进了将军府的一间厢房。本是想停停就走,不料被人察觉,只得除去灭口。
她就在此时走进我的视线,像十年前一样,瘦瘦小小,除五官丰盈了些,几乎没怎么变化。
瞧了瞧地上的尸体,又去望她。我手握长剑,第一次懊恼到急欲遮掩。转身想走,可她已看到我的脸,如若此时走了,怕以后和她就再没有相认的机会。踟蹰再三,决定带她一起走。我压着腔子里不断上翻的血气,带着她一路盾进深山。
为什么这么做?
别问我,我真的自己也不知道。只是单纯的想着,能和她在一起就是好的,哪怕被抓到,哪怕死无葬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