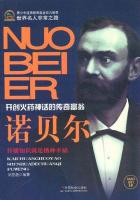中外文学交流与现代“小说”概念的确立
中国“小说”从古典走向现代,重新确立自己的内涵和意义,与近代以来中外文学交流的诸多事实有着密切的关系。最先对19世纪中国文学带来西方影响的要数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所进行的译介活动。他们不仅最早将现代用法的“文学”一词由英文“literature”翻译而得来(例如早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就在自己的中文著作里使用“文学”这个译词),而且直接译介了《伊索寓言》、《天路历程》以及部分《圣经》故事。这在某种程度上为近代文学的现代转化塑造了一种文学现代性的起源语境。而正是在这一语境中,近代国人开始翻译西方的各种叙事性文学作品,并经过早期翻译家林纾、严复等人的精心格义将“novel”、“fiction”一律以中文“小说”一词译之。由此,我国古已有之的“小说”便具有指称西方散文体虚构叙事作品的含义。因此,有人认为古代“小说”从而完成了“由文化学向文艺学的彻底转换”。但需要再一次明确指出的是,刚刚由文化学转入文艺学的“小说”是在我国早期对西方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获得的新含义。这一看似简单的词语翻译,其中至少有两点值得特别指出:
其一,由翻译西方文学作品而将“novel”、“fiction”译成中文的“小说”,实质上它所对应的是当时国人思想观念中的“西方小说”而并非“中国小说”。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当时的“小说”指的应是近于西方近代文学意义上的小说(虽然与“novel”、“fiction”相比,其内涵显得并不那么纯粹),但正是由西方翻译而来的“小说”为中国古代“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转变提供了新鲜的因素与宝贵的经验;其二,也正是因为由翻译而来的“小说”在其意义指向上更多地倾向于西方的“novel”、“fiction”,所以与我国古代“小说”相比,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当谈到古代“小说”与西方“novel”、“fiction”的不同时,蒲安迪的一段话经常为人引用:严格地说,中国明清章回体长篇小说并不是一种与西方的novel完全等同的文类,二者既有各自不同的家谱,也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功能……把novel译成“小说”,在当时实在只是一种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小说”不惟成为今天novel的约定俗成的译名,而且在读者的心目中渐渐潜移默化地变成了novel的同义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人们说“狄更斯的小说”、“巴尔扎克的小说”,殊不知严格地说,狄更斯和巴尔扎克只写过no-vel,而从未写过小说。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当林纾、严复等早期文学翻译家将“novel”、“fiction”译成中文“小说”一词之后,在近代中国的文学观念中,便同时存在着三种“小说”的认识(而这些认识又是含混不清的):1.中国古代意义上的“小说”;2.西方的“novel”、“fiction”;3.由文学翻译而来的当时国人心目中的“西方小说”。我们以为,正是以第三种由近代西方文学翻译而来的“西方小说”为线索、导引,并在今后更加接近于西方的“novel”与“fiction”的文学认识中以及在中国“小说”自身演变的轨迹上(尤其是宋代以来出现的通俗叙事“小说”的内部演变)共同推动了“小说”突破经学时代原有的混杂定义与边缘性价值定位,“小说”在现代民族国家所确立的新的价值系统中,最终由古典走向现代。这一过程与一系列人物的作用关系紧密。
1.王国维
现代“小说”概念的生成经历了两个至关重要的阶段:一是梁启超发动的小说界革命;一是王国维所倡导的审美自治与文学独立。如果说梁启超小说界革命运动及其新小说理论打开了重建“文学”的突破口,为“小说”成为“文学最上乘”创作了近现代的“文学”语境,那么是王国维最早在20世纪初通过引进西方美学体系,倡导审美自治与文学独立,批判中国传统文学的工具论,为小说返回现代审美文学开辟了道路,并为小说提供了一种更为文学本体的精神品格。
对中国文论界来说,常将诞生于20世纪初的两篇文章——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家和美术家之天职》看作中国古代文论实现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的标志,而这种转变却并非完全是中国古代文论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实际上,中国古代文论所发生的现代转变是在现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萌生及其建立的过程中进行的,从而构建了一套异于古典儒教中国建立在帝王一人权力之上的适于现代社会的价值系统与意义观念。梁启超、王国维对小说文学的看法则代表了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两条不同的文学观念道路:前者是功利的、政治的、为新民建国服务的;后者是超功利的、审美的、独立的。正是这两条道路的对立与统一为小说在现代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对晚清的学术思想界只注重政治功利的应用进行批判后,指出:“又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如此者,其亵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逭,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这可以说是王国维站在现代审美追求的立场上对视文学尤其是小说为教育工具这一在当时颇为流行的观点的强烈批判,因此,他提出了“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学术为手段而后可”的观点。这预示着一种对抗“他律”——以政治功利性规律小说性质——的现代文学“自律”现象的出现——文学审美自治的独立发展道路。这一点亦体现在《论哲学家和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的超功利文学观:
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日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至为此学者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当世之用,于是二者之价值失。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唯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
但在我国历史上,“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连占据正统文学中心地位的诗人都自忘其神圣独立之位置,更不用说“小说、戏曲、图画音乐诸家,皆以侏儒倡优自处,世亦以侏儒倡优畜之”,以致纯粹的文学作品“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由此王国维发出了“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的感叹,并祈望今后的哲学、美术家勿将哲学与美术视为道德政治之手段、勿忘其神圣与独立之天职。因此,王国维在反思我国哲学与美术不发达的同时,大力提倡学术(包括文学)的独立自治与超功利性,而这又是以宇宙人生及其所呈现的真理为目的。“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体现了王国维对西方现代学术普遍观念的接受与实践,而对真理的独立追求则又是建立在叔本华关于“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而有形而上学的需要”的观点之上,体现了一种以满足人性需要为目的的西方生命哲学家的人本主义思想。这说明王国维对哲学与美术之独立的提倡实质上是一种对宇宙人生之形而上问题的追问与解释,其根本归宿就是人生。对这一点的明确至关重要,因为它推翻了自古将文学视为抽象的“天道”即儒家“治国平天下”之“大道”的载体、工具的“原道”说,而确立了文学为人性、人生这一现代自我主体的需要。正因如此,中国文论以及呈现人生的小说与其他文学样式才获得现代转型的审美自治与独立发展的重要质素。因为“审美的特质就在于:人的心性乃至生活样式在感性自在中找到足够的生存理由和自我满足感”。“感性自在”强调的就是主体之人生对其所具有的此岸性与自主性的自由把握与体验,正是在这种“感性自在”中通过艺术的审美活动来实现主体人生生存依据的获得与自我满足。而对王国维来说,“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使人“在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斗争,而得其暂时之和平,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这亦如同尼采所言:“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的本来的形而上活动。”正因如此,王国维认为文学当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因为“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这体现了王国维主张审美和艺术的独立性及其形而上的本意,从而实现了一种迥异于传统经学时代视文学为经世致用、治国载道的文学观。这使小说在获得“文学”身份之后,突破了直接与治国大道相联系的文化等级差序结构,构建了从现代审美的角度对小说性质的规定与价值判断。
基于人生与美术(文学)的关系,王国维又将一种全新的审美观——悲剧,引进文学价值的评判中。他认为要摆脱与生俱来的苦痛,关键是使人超越生活中的欲望,实现心性的平和与自我的满足。这正是艺术价值之所在:“美术之价值,存于使人离生活之欲,而人于纯粹之知识。”但艺术对于人生之欲的摆脱与超越,并不是通过艺术的美(王国维所言之“优美”与“壮美”)使苦痛得以暂时被忘却与麻痹,而是使人“人于纯粹的知识”以获得形而上之意义的自律的醒悟而非“眩惑”。通过艺术的美使人获得对痛苦的醒悟,这正是悲剧所具有的审美效果以及王国维特别重视悲剧的原因所在。王国维由叔本华之说,将悲剧分为三种:“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通过悲剧美学的角度,王国维审视了中国文学,结果只有《桃花扇》与《红楼梦》具有厌世解脱的悲剧精神。但在王氏看来,《桃花扇》对于人生苦痛的解脱是“他律”的,换言之,《桃花扇》没有使人获得一种对苦痛的清醒的觉悟。而、《红楼梦》却大背我国的乐天精神,是一种“自律”的超脱、一种超越苦痛的醒悟。因此王氏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彻头彻尾、悲剧中的悲剧,即他所推崇的第三种悲剧小说“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古之所为小说家者,与今大异)。私衷酷好,而阅必背人;下笔误征,则群加嗤鄙”,而今却是“出一小说,必自尸国民进化之功;评议小说,必大倡谣俗改良之旨。吠声四应,学步载途”,进而“一若国家之法典,宗教之圣经,学习之课本,家庭社会之标准方式,无一不赐于小说者”。
王国维在20世纪初的我国文学及其文学批评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他基于对叔本华、康德等人的哲学与美学思想的领悟与引介,在中国确立了西方的美学体系。他通过《红楼梦评论》揭示了文学表现人性与人生的基本特质,更为重要的是,他为构建现代民族主义国家这一政治目标支配下的“文学想象”引入了现代审美文学观及其独立的品格,批判“文学工具论”,为“纯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苏曼殊、黄人、徐念慈
梁启超在其小说界革命的“宣言书”-《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通过对小说“两界”、“四力”的论述,“从小说之为体其易人人也既如彼,其为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的人性心理学的角度将“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归于中国旧小说。梁氏之所以持此论是为了实现其现代政治救国的根本目的,顺应社会改革的潮流,以取得作为思想传播之利器的小说“革命”的社会合法性。但在其犀利动人又颇中肯綮的论述中,又分明夹杂着绝对与偏颇。
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的《新小说》上,曼殊从小说为社会之反映的角度对梁氏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并明确地指出“小说者‘今社会’之见本也。无论何种小说,其思想总不能出当时社会之范围,此殆如形之于模,影之于物矣。虽证诸他邦,亦罔不如是……今之痛祖国社会之腐败者,每归罪于吾国无佳小说,其果今之恶社会为劣小说之过乎,抑劣社会为恶小说之因乎?”曼殊认为小说是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国民文明程度以及社会风潮的反映,因此他认为“盖小说者,乃民族最精确、最公平之调查录也”。这与梁氏将中国旧小说视为社会腐败的总根源则是“背道而驰”的。
黄人在《小说林》发刊词中,虽然认为可以将“吾国”、“今日”与“异日”的文明称作小说的文明,但他却指出有一弊焉:“昔之视小说也太轻,而今之视小说又太重也。昔之小说也,博弈视之,俳优视之,甚至酰毒视之,妖孽视之。”言叹道:“此其所见,不与时贤大异哉!”这既表明了当时社会以小说为开民德、民智、民力之教育工具观念的流行,又表明他“逆众流而上”,使小说成为“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的自信与魄力。
与黄人相比,徐念慈更加系统地指出了小说的性质。徐念慈认为“所谓小说者,殆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其最上乘者乎”?理想美学、感情美学的提出,表明在20世纪初年,随着西学的大量涌入,时人已经逐渐接受西方的美学思想与文学观念,孕育着一套迥异于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与价值系统,徐念慈就是从小说的审美价值与功用出发,提出了近于现代的小说认识。对于理想美学,他引用黑格尔“艺术之圆满者,其第一义,为醇化于自然”的观点,认为“满足吾人之美的欲望,而使无遗憾”。换言之,徐念慈认为小说应该满足人们对于美的欲望的渴求,通过艺术的审美来使人的精神得到圆满而没有遗憾,以此达到“合于理性之自然”。他进而从“事物现个性者,愈愈丰富,理想之发现,亦愈愈圆满”的角度认为正是小说人物之多而个性丰富适合了美的特质,并认为我国小说因人物事件多于西国小说而略高一筹。这显然不同于梁启超对我国小说的评价,他在接受西方美学的影响与中西小说的对比中,一定程度上重新发现并肯定了中国小说的艺术价值。对于感情美学,他引用了感情美学之代表的邱希孟氏(Kirchmann,1802-1884)“美的快感”是“对于实体之形象而起”的观点,说明小说中的不同人物能够引起读者的快乐、轻蔑、苦痛、尊敬等感情上快感之美的享受,突出了小说中特有的人物形象的艺术感情冲击力。同时指出了作为“实体之模仿”的形象性人物与非形象性人物,两者所引起“美的快感”的程度是不同的。而艺术就是要将感兴的实体达到一种“纯化”的境界,除去对于艺术无用的部分使其展露艺术的本性,这就是徐氏所谓的美的理想化。徐念慈在西方美学的影响下,比较准确地抓住了小说作为艺术所具有的形象性、典型化以及美的快感的特征,并努力在美学的范畴内论述小说作为文学艺术的特点。
黄人、徐念慈等人将小说纳入现代审美的范畴,并努力从美学的角度揭示小说的性质,这就与王国维的审美自治与文学独立的主张相呼应,对将文学尤其是小说视为政治教化工具的功利文学观起到了纠偏的作用。
3.周氏兄弟
周作人在1907年的《红星佚史》序中说:“中国近方以说部教道德为桀,举世靡然……读泰西之书,当并函泰西之意;以古目观新制,适自蔽耳。”周作人针对梁启超所提倡的“文学救国”予以批判,并指出梁启超等人虽然接触西学,但他们对小说的认识却还是“经世致用”、“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文学观念,而不是西方近代的文学观念。周作人在1908年的文章中更明确地说:“故今言小说者,莫不多列名色,强比附于正大之名,谓足以益世道人心,为治化之助。说始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篇。”并进而指出当时文坛状况:“若论现在,则旧泽已衰,新潮弗作,文字之事日就式微。近有译著说部为之继,而本源未清,浊流如故。”这表明20世纪初的中国传统文学观已经开始衰微,但“新潮弗作”也就是来自西方近代的文学观念还没有在当时文坛产生广泛影响。因此,接受了西方近代文学观念的周氏兄弟开始批判传统旧思想,倡导西方新观念。
鲁迅说“美术为词,中国故所不道,此之所用,译自英之爱忒(art or fineart)”,并说“美术者,有三要素:一日天物,二日思理,三日美化。缘美术必有此三要素,故与他物之界域极严”。其实,当时的美术指的是,以美为最高本质的艺术,包括绘画、雕塑、文学、音乐等各种艺术门类。而在王国维等人的倡导下,人们往往将文学明确地视为“美术”的一种,由此,审美体验成为文学的最高追求,而以这一追求为目的的文学,才称得上是“纯文学”。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明确地指出:“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亦当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周作人认为“文章者必非学术者也。盖文章非为专业而设,其所言在表扬真美,以普及凡众之心,而非权为一方说法”,进而表达了与鲁迅相似的观点,认为“文章中有不可缺者三状,具神思,能感兴,有美致也”,并将“意象、感情、风味三事合为一质,以任其役,而文章之文否亦即以是之存否为平衡”。周氏兄弟在指出文学的审美本质外,对文学的职用也作了说明,尤其是他们将文学与人生相连,将文学视为表现人生的艺术,为文学价值的独立做了理论上的论述。鲁迅说:“盖世界大文,无不能启人生之閟机,而直语其事实法则,为科学所不能言者。所谓闷机,即人生之诚理是已。此为诚理,微妙幽玄,不能假口于学子。”因此,他认为“文章之于人生,其为用决不次于饮食,宫室,宗教,道德……近世文明,无不以科学为术,合理为神,功利为鹄。大势如是,而文章之用益神。所以者何?以能涵养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周作人亦认为“文章者,人生思想之形现,出自意象、感情、风味,笔为文书,脱离学术,遍及都凡,皆得领解,又生兴趣者也”,并进而提出了“虽非使用,而有远功”的文学使命观:“一日裁铸高义鸿思,汇合阐发之也;二日在阐释时代精神,的然无误也;三日在阐释人情以示世也;四日在发扬神思,趣人心以进于高尚也。”周作人所言也就是:一、真正的文学应寓“博大精深”的人生真谛于融意象、感情、风味等为一体的文字当中予以阐发,使读者能得闻妙理,豁然开朗,并最终“进于灵明之域”;二、文学要忠实再现特定时代的国民精神与生活情趣,让读者了然无误的理解;三、文学要通过人生性情的表现来反映社会的真况;四、创作主体要在文学作品中呈现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以导读者进入崇高的人生境界。
在王国维与徐念慈等人的文章中都有着文学与人生的自觉联系,他们都认为文学应表现人生。但与王国维相比,周氏兄弟的文学人生观更显得乐观积极;与徐念慈等人相比,周氏兄弟则显得更加深入,切中本体。
其实,在将小说视为文学之最上乘的梁启超的文学观念里,“小说”实际上还包括新乐府、广东剧本等其他文学样式。这个看来并非纯粹的“小说”,更多的是因为其本身所具有的通俗易懂、便于传播等特点而有助于开启民智、民德、民力,从而借助政治的阶梯将小说与戏曲一起抬人文学的殿堂。但“小说”外延的这种模糊性并非在于梁启超一人,这在晚清有着较大的普遍性。夏曾佑在1903年《绣像小说》第三期中详细地指出了戏曲摄入小说的原因:“至本朝乃有一种,虽用生、旦、净、末、丑之号,而曲无牌名,仅求顺口,如《珍珠塔》、《双珠凤》之类,此等专为唱书而设。再后则略去生、旦、净、末、丑,而其唱专用七字为句,如《玉钏缘》、《再生缘》之类。此种因脱去演剧、唱书之范围,可以逍遥不制,故常有数十万言之作,而其用专以备闺人之潜玩。乐章至此,遂与小说合流,所分者一有韵、一无韵而已。”现代学者亦指出:“晚清小说是一个大坩埚,传统叙事手段和实验性的革新手段在此融为一体。这种情况反应在‘小说’一词的广阔外延上。以前小说只包括轶事、白话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晚清理论文章中所使用的‘小说’一词则进而包括文言的古代小说、弹词、杂剧和传奇,甚至包括西方小说。”“小说”外延在晚清的“广阔性”或者更显“包容性”中,正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过渡性。在梁启超看来,当时之中国就处于过渡的时代:“过渡时代者,希望之涌泉也,人间世所最难遇而可贵者也。”因此,整个近代中国直至现代的前数十年都处在一个传统社会解体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对于当时的“小说”而言,其外延的“含混”与“复杂”正是走向“单纯”与“明晰”之前的中与西、新与旧的种种观念的剧烈碰撞、融合与艰难蜕变。这一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也只有经历这一过程,小说在今后的发展才会有更加清楚的价值判断与明晰的艺术指向。
正是在过渡时代的中国,周氏兄弟接受西方近代文学观念从而展开对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批判与现代文学审美观及其独立价值的倡导。“小说”也就像周氏兄弟一样,由原先受传统文学的熏陶,到接纳西方近代文学观念影响,从而“脱离”传统走向现代。因此,周氏兄弟提出:“文章一科,后当别为孤宗,不为他物所统。又当摈儒者于门外,俾不得复煽祸言,因缘为害。”通过周氏兄弟的提倡,使近代的“文学想象”更加趋于审美与独立。尤其是周作人在采纳了美国理论家宏德的论述后,通过正确的标准将文学与具体的学术专业以及哲学等分开,并进而明确了文学与非文学的划分标准。
“历史一物,不称文章。传记(亦有人文者,此处指记叠事实者言)编年亦然。他如一切教本,以及表解、统计、方术图谱之属亦不言文,以过于专业,偏而不溥也。”取消“历史”的文学地位,这就彻底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以“史乘观”来抬高地位,但最后却沦为历史附庸的命运。进而,周作人从文体上区分了“纯文章”与“杂文章”:“夫文章一语,虽总括文、诗,而其间实分两部。一为纯文章,或名之日诗,而又分之为二:日吟式诗,中含诗赋、词曲、传奇,韵文也;日读式诗,为说部之类,散文也。其他书记论状诸属,自为一别,皆杂文章也。”
“文学的本质最清楚地显现于文学所涉猎的范畴中。”经过“纯文章”与“杂文章”的区分,小说在文体上被周作人划为散文体的叙事文学,与诗赋、词曲、传奇等韵文区分开来。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在现代纯文学的范畴中,对小说这一文体最为明确细致、最具现代文学本质意义的划分。因此,我们从周氏兄弟对纯文学的文体艺术分类、对文学“兴感怡悦”的审美本质的领悟与倡导、对“涵养人之神思”的非功利性目的的认识与推崇、对“文章一科,后当别为孤宗,不为他物所统”的文学独立品格的珍视与维护中可以断定: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概念已初步生成。
4.管达如、吕思勉
1912年,管达如在《小说月报》第三卷第五、第七至十一号上发表了论述小说的文章《说小说》。其中借助和发挥了梁启超的小说论,但亦有新观念的启发。
在小说的分类上,管达如没有周作人那么“纯粹”,但他认为白话体小说是小说的正宗,即使“传奇之优美,弹词之浅显,亦不能居小说文体正宗之名,而不得不让之白话体矣,”透露出“纯小说”的倾向。对小说在文学上的位置,管达如明确指出:“文学者,美术之一种也。小说者,又文学之一种也。人莫不有爱美之性质,故莫不爱文学,即莫不爱小说。”将文学归属于以“美”为本质的美术,文学自身便获得了“美”的本质属性,而小说又是文学之一种,由此,小说因“美”而成为文学的一员。进而,管达如指出小说与他种文学样式的五个“异点”:“小说者,通俗的而非文言的也……事实的而非空言的也……理想的而非事实的也……抽象的而非具体的也……复杂的而非简单的也。”管氏对小说五个特征的归纳,虽然一定程度上沿用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术语,但其中亦显露出新的认识。
他认为“通俗文,如向来通行之白话小说……其语法字法,全与今日之语言相同,直不啻举今日之语言,记载之以一种符号而已,故了解之甚为容易……夫社会上不能尽人而为文学家,亦不能尽人皆通知文学,而文学之思想,则人人有之。人未有不欲扩其见闻,且未有绝无爱美之感者,此即文学思想也”。管达如主张用今日之语言创作小说并表现美的文学思想,以满足人人对文学欲望的需要。这与他认为白话体小说是小说文学的正宗的观点是一致的,并且指出人都有文学思想,进而将文学与人生爱美的欲望联系起来,彰显了小说审美的本质与人性需求的联系。管氏所谓小说的第二个特征——“小说者,事实的而非空言的也”,从他所主张的“小说者,社会心理之反映也”可知,他所指的是小说的内容应取材于社会本身,也就是小说应来源于人们社会生活的人生体验而非脱离现实生活以致失去人生根据而流于虚造的空言。即管氏所谓:“今设为事实以明之,而其所假设者,又系眼前事物,则不特浅近易明,抑且饶有趣味,其足以引人入胜宜矣。”但管氏所谓的事实“乃是理想的事实,而非事实的事实,此其所以易于恢奇也”。换言之,小说取材于社会人生之体验的事实并非完全照搬于社会,而应当加以合理的“理想”,也就是对“事实”要进行符合人生与事物发生、发展之逻辑的“假设”,如此才会使小说具有“恢奇”的特点,才会使读者津津乐道。在此,管氏多少透露出文学虚构的意味,但他又说“理想界之事实,无奇不有,斯小说亦无奇不有。其所以易擅胜场者,非著者才力使然,实材料使然也”。他将“恢奇”归于材料而非作者的自由假设,这就取消了作者在创作时自由虚构的可能。管氏又说:“理想界之事实,皆抽象的而非具体的,此其所以美于天然之事实也……小说所述之事实,皆为抽象的,故其意味较之自然之事,常加一倍之浓深。”自然具体的事实让人有一目了然之感,缺少自由与变化,但小说所记载的理想界的事实经由小说文本的阅读为读者提供一个自由开阔的文学想象空间,并在阅读期待的感召力影响下,让读者享受小说为他们带来的文学阅读的审美快感。管氏虽然将小说看作具有“美”的性质的文学,但他所谓的“美”并不是无功利性的,而是带有道德规训意味的。
吕思勉于1914年将累计三万言的《小说丛话》发表于《中华小说界》第三至第八期,他以近代西方的文学观念详细地论述了小说的本质以及其他方面。在文章中,吕氏提出了“近世文学”的概念。何为近世文学?他说:“近世文学者,近世人之美术思想,而又以近世之语言达之者也。”进而他以古今人“好尚”的差异来说明古今文学之美的不同,“凡人类莫不有爱美之思想,即莫不有爱文学之思想。然古今人之好尚不同,古人所以为美者,未必今人皆以为美也;即以为美矣,而因所操之言语不同,古人所怀抱之美感,无由传之今人,则不得不以今文学承其乏”。吕氏以清醒的“当下意识”自觉地将当时之文学称为“近世文学”,以区别“古代文学”。这显示了当时处在中西交汇的时代背景下,学人以西方近代文学观念重建中国近代文学的自觉与努力。近世的文学是文学,是以近世的语言创作的近世文学,是表达近世人们爱美思想的近世文学。正是在重建的中国近世文学的范畴中,小说实现着现代的转化。“今文学则小说其代表也,且其位置之全部,几为小说所独占。(吾国向以白话著书者,小说外,殆无之。即有之,亦非美术,性质不得称之为文学。)”
在20世纪初期,大凡理论家论小说时,必先论及文学,论文学时必先论及美术。因为在当时,小说是文学之一种,文学又是美术之一种。因此,吕氏在论及小说性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时,亦先论及美术。他说:“夫美术者,人类之美的性质之表现于实际者也。美的性质之表现于实际者,谓之美的制作。”进而指出美的制作所必经的四个阶段:模仿、选择、想化、创造。吕氏对“想化”与“创造”的认识突破了管达如认为小说“恢奇”的特点来于材料而非作者才力的局限。吕氏认为:“想化者不必与实物相接处,而吾脑海中自能浮现一美的现象之谓也……美的制作者,非模拟外物之谓也,而表现吾人所想像之美之谓也。”在此,吕氏指出了美术(文学)的突出特征:虚构性、创造性与想象性。在明了美术性质之后,吕氏指出了小说的性质:“小说者,文学之一种,以其具备近世文学之特质,故在中国社会中,最为广行者也。”由此,小说便具有了虚构性、创造性与想象性等文学的主要特征,即吕氏所谓的小说的“正格”,并在以后的论述中一再强调。
吕思勉从文学的角度将小说分为散文与韵文。他认为“凡文学有以目治者,有以耳治者,有界乎二者之间者”。以耳治者,指歌谣等;以目治者,指不论其为文言还是俗语,凡无韵之文都是,如《聊斋志异》、《红楼梦》等;兼以耳目治之者,则为有韵之文,如诗赋,如词曲,如小说中治弹词。但吕氏认为“小说之美,在于意义,而不在声音,故以有韵、无韵二体较之,宁以无韵为正格。而小说者,近世的文学也。盖小说之主旨,为第二人生之创造也。人之意造一世界也,必不能无所据而云然,必先有物焉以供其想化。而吾人之所能想化者,则皆近世之事物也。近世之事物,惟近世之言语,乃能建之,古代之言语,必不足用矣(文字之所以力世渐变,今必不能与古同者,理亦同此)。故以文言、俗语二体比较之,又无宁以俗语为正格”。吕氏认为以近世之言语(白话文)创造的、具有想象性与虚构性、表达近世人生之意义的小说才是近世小说的正格。
值得注意的是,继1908年周作人以近代西方文学观念的标准将文学分为“纯文学”与“杂文学”两个概念之后,吕思勉又一次表达了对这两个概念的认识。只不过他是着眼于文学的价值和功能,由此他先称之为“有主义”小说与“无主义”小说。他说:“有主义之小说,或欲借此以牖启人之道德,或欲借此以输入知识,除美的方面外,又有特殊之目的者也,故亦可谓之杂文学的小说。无主义之小说,专以表现著者之美的意象为宗旨,为美的制作物,而除此之外,别无目的者也,故亦可谓之纯文学的小说。”接着指出了“杂文学”小说兴起的原因:“近倾竞言通俗教育,始有欲借小说、戏剧等,为开通风气、输入智识之资者。于是杂文学的小说,要求之声大高,社会上亦几视此种小说,为贵于纯文学小说矣。”吕氏指出了20世纪初在梁启超以现代政治救国为目的发动的小说界革命影响下,“文学工具论”的兴起以及对“小说”、“戏剧”地位的提高。对此,吕氏表达了质疑:“夫文学与智识,自心理上言之,各别其途;即其为物也,亦各殊其用。开通风气,灌输知识,诚要务矣,何必牵入于文学之问题?”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以两者相牵混,是于知识一方面未收其功,而于文学一方面,先被破坏也。”可见,吕氏主张文学要脱离功利性目的影响,以保证文学自身的审美独立性。吕氏批判了梁启超视“小说”为“新民”工具的功利性文学观念:“近今有一等人,于文学及智识之本质,全未明晓,而专好创开通风气、输入智识等空论。”因而产生的小说、戏剧在吕氏看来毫无文学上的价值,由此观之,吕氏认为只有以美为本质的纯文学小说才是真正的文学,才更具有文学上的价值。
吕氏在《小说丛话》中一再强调小说作为文学所具有的虚构性、想象性、创造性等文学特征,例如:“小说所载之事实,谓为真亦可,谓为伪亦可。何也?以其虽为事实,而无一不经作者之想象变化;虽经作者之想象变化,而仍无一不以事实为之基也。”在吕氏看来,“小说者,社会之产物也”。小说的内容取材于社会现实,小说又是“第二人间之创造”,“人类能离乎现社会之外而为想象,因能以想化之力,造出第二之社会”。换言之,小说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吕氏同时又表现出了对小说作为叙事文体的自觉意识,“夫文学有主客观之分。主观主抒情,客观主叙事”。“惟小说与戏剧,则以其体例之特殊故,乃能将主观一方面之理想,亦化之为事实。”“夫如是,故小说与戏剧可谓客观其形式,而主观其精神。持是以与他种文学较,则他种文学,可谓为主观的形式之主客观文学;而小说戏剧,则可谓客观的形式之主客观文学也。”两者比较,吕氏认为客观的文学比主观的文学高尚,因此“小说戏剧之势力,驾他种文学而上之,谁日不宜?”从而确定了小说在文学中的高尚地位。
吕思勉不仅论述了小说作为文学之一种的美的本质,强调了小说所应具有的散文体的虚构与想象等文学特征,而且也简论了创作小说的方法。
第一,理想要高尚。吕氏认为小说以理想创造出第二人间,“理想者,小说之质也。质不立,犹人而无骨干,全体皆无所附丽矣”。在此,吕氏提出了作家的人格修养问题,“凡人之道德心富者,理想亦必高;道德心缺乏者,理想亦必低。所谓善与美相一致也”。进而,吕氏提出了真、善、美合一的艺术追求:“惟其真也,惟其善也,惟其美也……此作小说之根本条件也。”
第二,材料要丰富。高尚的理想要以材料来辅佐,“盖小说者,以其体例之特殊故,凡理想皆须以事实达之,故不能作一空语”。因为近世的小说是以近世的语言表达近世人的生命体验,所以近世小说应多取材于近世之社会。由此,吕氏又提出了作家创作的生活阅历问题,“小说为美的制作,贵乎复杂,而不贵乎简单;既贵乎复杂,则其所描写之事实,当赅乎各方面,而决不能偏乎一方面”,“此作者之阅历,所以不可不极广也”。作家生活阅历的广阔成为创作小说最主要的条件。
第三,组织精密。在提出小说作家人格道德修养与生活阅历的问题之后,吕氏又对小说的组织结构说明了两点:一是小说所叙述的事实要连贯,也就是在组织情节故事的时候,必须有一条清晰的线索以避免事实叙述的冲突;一是小说中主次人物要分明,谁为代表作者理想的主要人物,谁又是代表四周境遇的次要人物,这一点在小说中要明确。
管达如与吕思勉都从“美”的立场将小说视为文学的一种,确定了小说文体美的本质。尤其是吕思勉从纯文学的角度讨论了小说所具有的想象性、虚构性、创造性等文体特征以及小说自身所具有的审美价值,从而确立了迥异于古代小说概念的现代小说本体特征与美的品格。在纯文学的范畴内生成了现代小说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