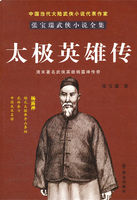再说1949年2月底,邓联佳、尹立言一起离开长沙回武冈,在汽车即将起动之际,李春花随后赶到,要跟他俩一起回家。
汽车开动后,邓联佳问道:“李小姐,怎么突然想起要回家呢?”
李春花说:“不是突然想起,是有个事情早就想请仇老板帮忙。”
“听你的口气,这个忙一定得我回家才能帮?”
李春花抱歉地说:“平时你那么忙,总不能为我的一点小事,劳驾你专程回一趟武冈吧。”
“是哪方面的忙,我有那个能力吗?”
“对我来说是大事,对你这样的大老板是举手之劳。”
“莫非是生意方面的?”
李春花狡黠地一笑:“对不起,等到了武冈,我才能告诉你。”
邓联佳听李春花如此说,也就不再多问。
长途车公路上颠簸了九个多钟头,下午五点就到了高沙镇。按规矩,长途车到了这里要停下来,一部分人在这里下车,司机和到城里才下车的乘客都要打尖吃饭。
汽车在站点停下,李精一带着两名卫兵已经等在那里。三个人一下车,李精一就迎上来,对尹立言说:“尹司令,晚饭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贺军长在屋里等呢。”
邓联佳想起什么事来,对身边的李春花说:“李小姐,你是跟我们一起下车,还是坐到城里去?”
“今天我还得赶回城口冲老家,当然要坐到终点站。”
尹立言也记起了刚上车时的事,便提醒李春花说:“你不是有事要求仇老板吗,现在不说要等到何时?莫非是什么秘密事,要我们回避一下?”
“哪有什么秘密事,是可以公开说的。”
尹立言也想知道,遂催促说:“那为何还不说?司机吃了饭就要走了。”
“李小姐也一起进去吃饭吧,我跟司机打声招呼,要他久等一会!”李精一说着就找司机去了。
李精一引着三人向部队驻地走去,没多久就听到操场上传来嘹亮的口令声。进入营地,里面果然有一种部队的氛围。尹立言满意地说:“不愧是带过兵的,果然像那么回事!”
李精一道:“都是贺军长的功劳,我不过是协助他工作。”
来到指挥部,贺子非急忙起身迎接,问候过后,就带到餐厅用膳。
贺子非端出酒来,尹立言制止道:“今天就算了,有人还要回城里去,不能让司机等得太久。”
贺子非不解地望着他们三个:“你们谁要回城里?”
李精一看着李春花说:“都是自己人,没什么不好说的。”
李春花犹豫很久,才对邓联佳说:“仇老板,听人说你和易豪是结拜兄弟,不知是否有此事?”
邓联佳道:“你是听细狗说的吧?那么‘是’又如?‘否’又如何呢?”
“如果你们是结拜弟兄,想请仇老板出面帮个忙——如果愿意帮我就说,如果觉得很为难,就当我开了个玩笑。”
城口冲是易豪的领地,邓联佳一听李春花这样说,就明白要帮的忙与易豪有关系,便认真地说:“我与易豪确实是结拜弟兄,正因为如此,我有义务对他负责任,太为难的事不会强求他。你的事如果早说出来,我做不到就会拒绝,可是现在你为这事五六百里路都赶回来了,明摆着是非要帮忙不可。你说吧,我会尽力的!”
尹立言这下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表情夸张地说:“没想到你还真有点人小鬼大,小小年纪竟然晓得用计谋!说吧,我也想知道,你到底要他帮什么忙。”
李春花认真地说:“是这样的,自从易豪在枫木岭立寨,周边十几里的人都按规矩向他交纳粮食,负担也不是很重,大家都能接受。这个就不说他了。在1947年的冬天,当时我还没满十八岁,那天易豪从山寨下来从我家门前经过,正好我坐在门口纳鞋底。他足足看了我几分钟没说什么就走了,谁晓得第二天他就派人送来了帖子,要我爹在腊八这天必须把我送到山寨去。”
李精一笑道:“当压寨夫人好呀,比你到外面流浪强了许多!”
李春花急了:“我家世世世代代是清白人家,要我当土匪婆,我宁愿去死!”
邓联佳见李春花要哭的样子,怕李精一再打趣她,忙说:“有这种事?我没听他说过啊。”
“不光彩的事,他当然不会说。为了躲避他,我逃了出来,先在武冈城里给人当佣人,因觉得城里容易被他找到,就想到去更远的地方,没想到被人骗到长沙,若不是仇老板搭救,现在……”
邓联佳打断她说:“你的意思,是还想回老家去,要我劝劝易豪不要再为难你?”
李春花摇头:“到外面我才发现,人如果躲在一个小山村,一辈子等于白活了,回去是不可能的了。”
“那你要我帮你什么忙?”邓联佳愣住了。
“我出来后,易豪出于报复,有意给我家里增加了一倍的份额,先前还能承担。去年我父亲死了,家里就剩一个母亲,更糟糕的是她因为想我,一双眼睛哭瞎了,可是份额还是一样没少,我母亲承担不起。”
“原来你是想要他减少份额,这个不难,能帮你办到。”
李春花破涕为笑:“那就谢过仇老板了。”
饭局很快就结束了,因怕司机久等,邓联佳就送李春花回车站。从车站回到指挥部,邓联佳见只有李精一一个人在,因问道:“人呢?”
“贺军长领尹司令看部队去了。”李精一等到邓联佳一坐下,就有点迫不及待地说:“怎么样,尹司令都向你承诺了什么?”
邓联佳不满地说:“哪有承诺!根本没有要收拾张云卿的意思,还要收编他呢!”
李精一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这就对了。”
“对什么呀?他想到的是要扩充势力,与我的事没有干系。”
“做军阀的,谁不想扩大势力?这个没有错,我们也不指望他办事,但是并不等于就不能利用他。”
“李师长的意思……”邓联佳满腹狐疑地看着他。
李精一道:“实不相瞒,这个正是我的计划!我让尹司令出面收编他,他不干,就收拾他;他干了,到了我的手里就由不得他了,到时新账旧账一起算!”
“这倒是个办法。”邓联佳随后又说,“当年的事,真是给你增加麻烦了。你不知道,自从姜定要回来说起你的情况,我的心一直悬着,真是急死了!”
李精一道:“那次确实悬得很,叶剑英非要杀我不可,总裁也很为难,若不是我的老上级孙连仲力保,今天我们就不能坐在一起了。”
邓联佳松了口气:“这叫吉人自有天相。”
李精一摇头苦笑:“过去的事就不说了,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辰溪兵工厂那边就快有行动了,等到大批武器到手,军队得到扩充,下面的路就好走了。”
“具体什么时候行动?”
“3月初吧,最迟不超过3月中旬,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什么是东风呢?”邓联佳很关切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湖南的局势,虽说程潜议和的态度十分明确,但毕竟还是国民党当政,若要抢夺国民党治下的兵工厂,总得有个理由吧?”
“要什么时候才能找到理由呢?”
“我说快了,当然是正在制造条件。”
“那我就拭目以待。”
说到此处,李精一突然神秘兮兮地起身到门口望了望,然后仍然把门掩上看着邓联佳:“你觉得贺子非这个人怎么样?”
邓联佳吃惊道:“你和他是故交,现在还在一起共事,你应当比我更清楚呀!”
“我当然了解他,我在问你呢。”
“我去年才认得他,后来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多,不是太了解。”
李精一点头:“我就知道你对他不是太了解。他这个人,大革命时期曾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又脱离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做事,历任高级军职,深得蒋介石的赏识。抗日时期,又入陆军大学学习。据他自己说,1938年,陆大由南京迁驻湖南时,他特地去长沙八路军办事处拜会了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要求介绍他去延安……”
“他去了吗?”邓联佳想不到,贺子非还有这样的传奇经历。
“徐特立没有同意,对他说‘只要不忘记革命,到处都可以革命,我们所缺乏的是军事技术理论,你应趁此机会好好学习。在这里所起的作用,比在延安可能还要大’。”
“他这么做,也可以理解。”
“还有一点你可能不清楚,成立大西南联军最早是他发起的。”
“可尹司令说,是他发起的呀?”
李精一冷笑道:“个中内情我最清楚,早在1948年春夏之交,贺子非见南京政府已濒绝境,就有了改换门庭的想法,因此脱离了蒋介石。当时他最苦恼的是,他离家多年,又未在湖南做过事,故旧不多,没有号召力,很自然就想到他的表弟尹立言。尹立言早年留学日本,又是中国陆军大学毕业,何键主湘时,在湖南办过‘明耻社’,和各界人士都有交往,人缘关系很好。你也知道,尹在国民党内部是个失意军人,二人一说即合,但又各怀鬼胎……”
“这话怎么说?”邓联佳得知两人竟然同床异梦,心里不安了。
“先说尹立言,他与贺子非说好后,马上又找到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并让李委派为西南联军总司令,这就说明,他走的路线是介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另一个方向。”
“你是说贺子非走的是共产党路线?”
李精一见邓联佳吃惊的样子,忙打着哈哈说:“我也没敢肯定他走的是哪条路线,我是姑妄言之,不当真不当真!不过对你而言,只要报仇,管他走的是哪条路线。”
邓联佳连连点头:“李师长言之有理,言之有理。”
两人沉默片刻,李精一又说:“你和张云卿之间的事,在这里除了我和尹立言,不能再让其他人知道。”
邓联佳明白他说的“其他人”指谁,因说:“尹司令应该说了吧?”
“不会,早在长沙我就嘱咐过了,该说的不多说,不该说的一句不说,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他还当什么政客!”
“说的也是。只是我回来,总得有个借口吧?”
“这个我已经和他说了,你是代表同乡会关心家乡时局,回乡考察的。你打出这块牌子,不光是贺子非,还有很多人都会争取你。”
邓联佳点头:“这个名义说得过去,往年家乡遇灾害,每次我都代表同乡回来捐款。”
“这就对了!眼下时局动荡,很多人都打着保卫家乡的牌子到处要钱要物,像你这样的财神爷,他们正要削尖脑袋找你呢。”
两人正说着话,尹立言、贺子非回来了。寒暄过后,李精一就把话题引到时局及大西南联军的事情上。贺子非见他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就说:“尹司令和仇老板劳累了,应当早点休息。今天就到这里吧。”
李精一见尹立言以呵欠回应贺子非的提议,略显尴尬道:“你看我,把最重的事都给忘了,还是贺军长懂得体贴人。”
贺子非对邓联佳说:“仇老板这次回家乡,除了来我这里看看,其他还有什么安排?”
邓联佳看了一眼尹立言说:“我们同乡会的成员,在我来之前就讨论过了,在武冈只认‘大西南联军’。”
贺了非高兴地说:“大西南联军,在武冈只有我这一个军啊!”
“那好啊,就认你一家可以了。”邓联佳也笑了。
“说出来让你见笑了,说是一个军,其实才500多人,尤其是武器装备严重短缺,仇老板可要多支持哟!”
“一定一定!”
“虽说现在才这些人,但我已经在城步、绥宁开始组建,估计要不了多久,就能名符其实了。”
“我都看到了,贺军长果然是大手笔!”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好好休息,我明天要去办事,就不陪仇老板了。”贺子非转向李精一:“这里的一切,就交给你了。”
“明天我也要走呢,刚才大家都听到了。”邓联佳贺子非也想起来了,说:“你是去城口冲吧,明天城步有一个连的新兵需要我去训导,正好与你同路!”
是夜无话,次日早饭后,贺子非着便服和邓联佳各骑一匹快马离开了高沙营地。一路上,邓联佳从贺子非口里得知,李精一目前在这里是任参谋长之职,具体事务是训练新兵。
两人在武冈城西五里处的天心桥分手,贺子非继续西行,邓联佳向北走了约十余里又翻了几座大山,终于来到枫木岭。
枫木岭自古以来就是土匪的老巢,“你怕是从枫木岭下来的”,这是武冈老百姓形容某一个人凶蛮不讲道理用得最多的一句话。
邓联佳上得山来,神经不知不觉地紧绷起来。没多久,果然从暗处传来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天上起乌云——”
对方怕邓联佳没听清又重复一遍,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回答或回答不对,枪就打来了。邓联佳立刻回应道:“有云就下雨。”
对方大声喝问:“下雨不怕雨淋吗?”
邓联佳应声回答:“雨不淋戴伞人。”
暗处的人出来了,一副砍柴打人打扮,手里拿了柴刀、扦棒,腰上别了盒子炮。邓联佳不认识这个人,这是山寨的第一道警戒线,通常情况下由小土匪负责巡防,接下来才是第二道警戒线。
前行半里许,又一个声音从暗堡里传出:“云里打火闪(武冈土话即闪电)——”
邓联佳回应道:“天要打雷了。”
暗堡里的人喝问:“打雷不怕雷炸吗?”
邓联佳回应道:“大水不冲龙王庙,雷不炸自家人。”
暗堡里跃出一个人,原来是周连生,他老远就喊:“我就觉得声音很熟,果然是仇先生。快来快来,我们豪哥正念叨你呢!”说着就令马弁给邓联佳牵马。
一路上,邓联佳问道:“连生,为何亲自回来巡哨,寨子里没人了吗?”
周连生道:“仇先生啊,你哪里知道,如今天下要大乱了。共产党还没打过来,地方上就冒出一支几千人的军队,说是要帮共产党剿匪的,这个时候我哪里敢偷懒,万一有探子进来怎么办呢?”
“你说的是贺子非吧?”
“没错,正是他!咦,你在长沙怎么也这样清楚?”
“从城里过,才听说的。”
“是在迎春亭听到的吧?那里的消息就是灵,有时候比探子还传得快呢!我和豪哥说了,到那里设个点,可就是迟迟没有行动。”两人说着话,很快就进入寨子里,周连生冲着守在寨门口的马弁喊叫:“有贵客来了,还不快去通知豪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