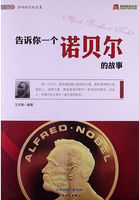1952年国庆节过后的一天,一辆苏式吉普车开出西直门,朝颐和园方向颠颠簸簸地驶去。
车尾很特别地挂了个拖斗,里面装有两个木板箱、两只皮箱,斑驳疤痕随处可见,看上去都是用过多年的东西;还有几个细麻绳捆了的铺盖卷儿。京郊的道路正在修建,路面凸凹不平,也有沙尘,车一颠簸,拖斗里的行李就左摇右晃,咣当作响。即使在当时世人的眼光里,也很难相信会有什么“长”字号的人物坐这种车。
但这已是当时的北京大学唯一能够拿得出手的好车,里面接的是他们的第一副校长江隆基。在此之前他是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接到调令后他立即携家眷进京,在教育部招待所住了几天,参加了新中国的第三个国庆观礼盛典,打发走西北军政委员会为他派的一位警卫员,这天去走马上任。
江的一侧坐着他的妻子宋超,怀里抱着不满周岁的小女儿小召;另一侧坐着大点的也是女孩儿,名叫小曼,小手扒着车窗,好奇地观望着沿途的景色。可以说,这辆吉普车载着江隆基的全部家眷和全部家当,将他事业的航船驶进了一个全新的港湾。
司机旁边坐着前来接他的校办负责人,主动搭话说:“听到您来北大,大家都很高兴。马校长派我发个欢迎您的电报,是在红楼外面的东四邮局发的。”
“哦,收到了,谢谢大家。”
江隆基这句话说得平平常常,不热不冷,例行公事式的。校办负责人期待着新校长的问话,像一般新上任的领导一样问长问短,了解情况,然而终究是一路无话。
他侧过身来好奇地注视着这位新到任的副校长,见他穿一身灰布中山装,两手搭在膝盖上坐得端庄笔直,目不斜视,像在出席某个重要的会议。脸膛方方正正,前额高阔,两弯浓眉,目光始终凝重而多思,大嘴唇不苟言笑。第一印象是位极严肃的领导,年轻的校办负责人油然产生一种敬畏感。当然他也或多或少地听说过一点江隆基的经历: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两度出国留学,在革命战争年代曾是陕北公学、华北联大、抗大、延安大学的主要领导。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的许多学生在新中国成立后都走上了领导岗位,有的成为省部级干部。他与吴玉章、蒋南翔、李达、匡亚明、成仿吾等人一样,被称为“党内教育家”或“红色教育家”,而北大现有的校领导中还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
金秋十月是北京最好的季节。路旁的农田瓦舍清新宜人。沿路的许多地方还是村庄样子,新建筑正在拔地而起,工地上热气腾腾人声鼎沸,使人明显地感到,北平改称北京之后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江隆基只是偶尔看一眼车窗外面的景致,更多的则是目视正前方,深深地陷入沉思之中。他曾是北大的学生,不过那时的北大在沙滩红楼,而现在的北大在他从未涉足的燕园;时隔二十五年重返北大,而且求学与当校长的本质含义就有天壤之别,他的心情怎么也难以平静。去年冬天他来北京开会,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曾征求他的意见:“你考虑一下能否离开西北。”他的回答很干脆:“服从工作需要。”回去后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习仲勋也问他对工作调动的意见,他仍答:“服从组织决定。”又问:“如果调动一下,你愿意干什么工作?”他答:“还干教育,我对教育有特殊的感情。”就这样,一纸公文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命运,也勾起了他对旧北大如烟往事的回忆——
1924年,十九岁的江隆基和二十岁的长兄江裕基同时从西安省立二中毕业,都想考北京的大学,但地处大巴深山、粗通文墨的农民父亲江廷瑜纵然有“耕读传家”的美好愿望,仅凭几十亩薄田和一个点心铺,怎么也无力供给两个儿子同时远赴北京就学,更何况下面还有两个小儿子,一个已经十五岁上了中学,一个十二岁也即将考中学。一个女儿已经出嫁,四个儿子是他的骄傲,哪一个的学业他都不想放弃。他要靠儿子改变恶棍横行乡里的社会,改变外国传教士颐指气使的风俗。正在一筹莫展之际传来好消息,这年庚子赔款分配给陕西的留学名额比较多,老大江裕基考上了日本东京明治大学的官费留学生。长兄的出国留洋鼓足了弟弟江隆基的勇气,也暂时地解除了老父亲的后顾之忧,他顺利地考进北京农业大学。
读了半年,江隆基萌发出一种意识,来北京这样的地方读大学,就应该读最好的大学——北京大学。当年的北京大学有最著名的校长蔡元培,有著名的教授胡适和鲁迅,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李大钊,还有他最爱读的《新青年》《小说月报》《独秀文存》《梁任公讲演集》等书刊。怀着这一美好的愿景,1925年春季招生时,他从北京农业大学转考到北京大学,佩戴上了由蔡元培恳请鲁迅先生设计的圆形校徽,来自穷乡僻壤的江隆基由此走上了更为广阔的人生天地。
当时的北京大学,学制分预科、本科、研究所三级。预科两年,分甲、乙两部。甲部修满学分后升入理科各系,乙部修满学分后可升入文史、政法、经济各系。江隆基考的是乙部,准备升入经济系。预科的课程分共同必修、分部必修和选习三种。共同必修课有国文、伦理学大义和第一、第二外语;预科乙部必修课有哲学概论、科学概论、中国及世界近代史、古体文及部分理化课程,打算升经济系的还必须选修经济通论。课程分量很重,占去了江隆基的大部分时间,当时马寅初已是赫赫有名的经济学教授,著有三大本著作,还成立了“中国经济学社”,经常在校园里发表演讲。他对马教授很崇拜,打算从师研究中国经济。虽然课业负担很重,但并不影响他尽量利用课余时间阅读各种进步书刊和参加各种学术讲座活动。当时正值孙中山主持召开第一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之后,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李大钊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的演说很受学生欢迎,江隆基几乎一次不落地聆听了他的讲演,原先进步的民主思想也得到了升华,认识到“以唯物史观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到来是有道理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才是拯救中国的导星”,并开始“赞同共产主义”。
然而好景不长。年迈的农民父亲即使累断筋骨,也无力供给他在北大的花费。是年底,江隆基断了经济来源,迫于家境贫寒而休学,回到大巴山下的西乡县老家筹措学费。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江隆基回家也没闲着,他把家乡的一批知识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了“丰东青年协进会”,由他亲自拟定简章,规定宗旨,主持活动。这个组织培育出西乡第一批共产党员,后来组建了红二十九军,为红四方面军建立川陕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他还积极参加地方上的教育活动,主持了一年一度的小学竞赛考试,过去都是考国文算术两门,他建议增加了自然常识,由他亲自讲课,亲自出题,亲自阅卷。“身穿蓝布长衫、留学生分头、板书工整漂亮、讲课神采奕奕”的青年江隆基给父老乡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翌年春,父亲千辛万苦筹措了些钱,准备好行装,再次送他去北大读书。西乡县位于大巴山北麓,当年从他的家乡丰东到省城西安,要跨越一条野马河和汉江,还要翻越整个秦岭,正是李白描写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那种艰险路程,没有火车没有汽车连马车也没有,只能徒步前行。为安全起见,老父亲还雇了个姓李的脚夫挑行李陪送。正常情况下,走完全程得十一天。万没想到,艰苦跋涉到第十天,在翻越秦岭到一个叫关石子的小地方,眼看出山有望,突然从峡谷里蹿出一股土匪,钱财被洗劫一空,人也被扣下来。土匪头子审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自豪地答:“北京大学的学生,去北京上学的。你看校徽!”土匪头子不识字,凝住神愣了半晌,突然狂笑说:“学生好哇,好哇,爷手下正缺个识字的,你就留下来,给爷的弟兄当师爷。”随后将他俩绑架到一个寨子,分别锁在两间吊楼里,不给任何自由。土匪们休息的时候,就请他当“师爷”。他就讲一通“人之初,性本善”和“不义之财不可取”“过而不改,是谓过矣”一类的道理,借以窥测时机。
这样苦熬了十多天,一日天亮时弥天大雪,土匪营中不知出了什么事一片慌乱,紧急集合,像是要拔营起寨。江隆基意识到有了逃离虎口的机会,给“师爷”的待遇是不上绑,他解救出被反绑的脚夫,拔腿就跑。积雪很厚脚印明显,土匪在后紧追不舍,边追边喊:“师爷不要跑!没你的事!”二人有意朝陕南方向跑了一程,发现这样跑不是办法,眼看土匪就要追上。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决定拐个大弯朝关中方向跑,而且是倒退着跑,边退边用手拨拉积雪掩埋脚印,终于摆脱了土匪的纠缠。
出山口,又一口气跑了三十多里,二人踉踉跄跄来到秦岭北麓长安县的一个村庄,已是饿火中烧饥渴难忍,疲惫不堪,便去一家农户讨口水喝。那家人听他俩是陕南口音,说村里最近来了一户陕南人,你们去看看,认识不?真应了“天无绝人之路”的古训,敲开门,竟是陈松乔、朱素秋夫妇!夫妻二人不仅是西乡人,又是江在二中的同学,为躲避西安城内的战乱,在长安县临时租了间农房安身。他乡遇故知。乡党见乡党。陈氏夫妇热情接待了江隆基,并给足了干粮打发姓李的脚夫回西乡向江的父亲报平安。叙清原委之后,陈氏夫妇倾其所有,资助路费,送他去北大继续深造读书。
回到北大刚刚办好复学手续,江隆基又遇上了被鲁迅先生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三.一八”。
离校半年,他对北京的时局变化不甚了了。复学后除听课之外,便一头扎进《西乡报》的编辑出版工作。该报是由西乡籍的北大毕业生薛祥绥创办的。其时薛在国务院统计局任主事,又兼任北大讲师,讲授中国文学,对江隆基很器重。江也很崇敬薛,认为他是个甘于清贫、厌恶世俗、为官而“不为官”的学者。《西乡报》以“振作精神,力求进步,能力所及,无不改良”为宗旨,以“习俗不善,写作讽刺;遇有不平,据理力争;发现黑幕,声罪致讨”为编辑原则。每月一期,十六开铅印,在北京印好后发行陕南各地,是一份颇有影响的致力改良、爱国爱乡的进步读物。江离开西乡时,薛正回乡为老母奔丧。临别嘱他回京后赶快将三十六期编好付梓,尽早寄来。
3月17日北大没有开课,红楼内外人迹稀少,一片静谧。江隆基去学校转了一圈,回来躲进寓所专心校对三十六期《西乡报》的清样。这期有他写的《替小学教员说几句话》一文,是他回乡调查研究,亲自参与对小学教员的考核录用,回校后一口气写成的。文章只有三千多字,但切中了小学教育的时弊,并切切实实地提出了五条改良措施。他对这篇文章颇为满意。
晚上,他正在灯下校对清样,陕西籍的同学张仲超冲进寓所,颇有怨气地责问:“你呀你,回来了怎么不跟我讲一声?”江说:“没看正在忙着?明日把清样送印刷厂,首先要拜会的自然就是阁下你。”边解释边将报纸清样递给张,“请学兄斧正,这一期有愚弟写的一篇文章,给你念一段,‘教员们辛辛苦苦卖一年到头的气力,差不多声也讲嘶了,嘴也拌烂了,而所得的报酬只才过二百来串铜钱。你想在这米珠薪桂百物昂贵的时代,拿这区区的数目,买饭恐怕吃不饱,哪还有能力养家?哪还有余资供子弟求学呢?替社会服务而叫父母妻子挨饿,教别人的子弟而叫自己的子弟失学。若不改良教员的待遇,而想教育发达,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事。’再看外国教育发达的原因,我是这么分析的……”抬头一看,发现张仲超拿着报纸,并没看他写的文章,目光却停留在中栏一幅题为《急起直追,毋落人后》的漫画上,不无讽刺地说:“好一个西乡人直追陕西人,陕西人直追中国人,中国人直追世界人!莫看世界上的帝国主义血口张得有多大?”江疑惑地问:“你是说这幅画的题旨不对?”张这才拍了拍江的肩头坐下来,以大哥哥对小弟弟的口吻说:“看来乡党你回家半年,叫秦岭巴山把耳目也关闭了。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眼看八国联军侵华的悲剧又要重演,在这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小学教员的待遇能占多大的比重?”头脑向来机敏善断的江隆基预感到时局的严重性,恳求说:“陕南那山沟沟你也知道,几乎与世隔绝着,学兄你讲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张仲超这才慷慨激昂地说道,就在五天以前,日本的两艘军舰悍然进入大沽口,被国民军驱逐出去。日本政府以此为由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并纠集《辛丑条约》签字国的驻华公使联名提出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现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二十多艘军舰已云集大沽口,驻天津的外国军队也磨刀霍霍准备参战。就在今天上午,北大等学校和社会各团体的代表在三院紧急磋商,决定要求国民政府立即驳回日本政府的通牒,驱逐签名的各国公使。下午5时,代表分两组到外交部、国务院去请愿,要求对日经济绝交,惩办卖国贼张作霖。一百多名代表到国务院要求面见段祺瑞,但卖国成性的段祺瑞为了讨好主子,竟下令卫队向学生代表举起了屠刀,砍伤了许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