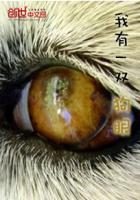我的家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山村,叫刘家镇。村子四面环山,只有两条通往外界的道路,一条在村北,越过北面的山梁,穿过山上浓密的松树林地,弯弯曲曲的通往县城。另外一条,在村西南,途径两座山连接处的一条山沟 ,沟里长满了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柳树,所以叫“柳树沟”。相传柳树沟是个乱葬岗,经常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吓人的事,所以很少有人从这里走,除了一些年纪大的人以外,几乎没人知道柳树沟通往哪里。
村子里只有百余户人家,分为上下两个生产队,西边的,是下生产队,我们通常叫“下队”,下队的居民,大多是蒙古族,姓包的最多,是大户。而我们家住在东边的“上队”,大多都姓刘,也基本上都有一些能数得上来的亲戚关系。
听我爸爸说,我们家是外来户,是在爸爸三四岁的时候,爷爷用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箩筐,一只装着年幼的我的爸爸,另外一只装着行李,奶奶领着十岁的大伯,就这样一家四口从一百多里外的一个叫赵家集的村子,迁徙而来。
在这个村子唯一沾亲带故的,是这个村子的赵村长。赵村长是奶奶娘家的本家,据说是个老革命,经历了抗日战争,还光荣的负了伤,后来部队把他留在这个村子养伤, 再后来就和村里的一个姑娘成了亲,扎根落户,还生了好几个娃。解放后,因为他是光荣的革命战士,政治成分绝对过硬,在队伍里打仗的那些年,又跟着政委多少学了一些文化,认识一些字,便理所当然的当上了村长。一当就是十五六年。
当然,外来户是不招人待见的,因为这个村子四面环山,耕地就那么多,人口越多,每户人家分得耕地就越少。而这个村子离县城有那么远,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村民们唯一的收入,就全靠那点少的可怜的耕地。所以这村子特别的穷,越穷人心就越自私,所以听奶奶说, 我们刚来的那几年,没少挨村子里一些多事的村民的欺负。要不是仰仗着奶奶是村长的家族里的堂姐,或许我们一家早就过不下去了。
后来奶奶又生了四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四个姑姑。其中三个长大成人后,分别与村里的刘姓的几个后生结了婚,从此我们家与村里的大户刘家成了儿女亲家。而且一晃我们家在村里落户也二十几年,早已与村民们融为一体。
其实我们家能在村里扎根,更多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奶奶。听奶奶说,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太姥爷是个“胡子”,江湖人称赵一刀。东北方言里“胡子”是土匪的意思。据说太姥爷得势的时候,也有百余号弟兄。太姥爷是个传奇的人物,曾带着这百余人,凭借二十几杆土枪和镰刀、棍棒、锄头,杀死了不少的小鬼子,在奶奶的老家--赵家集一带声名大震。
太姥爷有六个女儿,奶奶最小。奶奶的血液里多少有些匪气,年轻的时候脾气刚烈,一丁点儿的亏都不吃,一句矮话都不讲,是个惹不起的主儿。而奶奶又是村里有名的“大仙儿”,什么疑难杂症啊,丢魂招鬼啊,看好了不少人,所以村里的人都对他又敬又怕。
说起“大仙儿”,就必须要说东北农村人们普遍信奉的“保家仙”,保家仙有胡、黄、白、灰、柳五种,分别是 狐狸、黄鼠狼、刺猬、老鼠和蛇。而在我们这一带,却只有三种,那就是胡、黄、柳。她们分别被尊称为胡三太爷胡三太奶、黄三太爷黄三太奶和常三太爷常三太奶,柳仙是蛇仙,蛇在我们这土话儿叫“长虫”,所以蛇仙又被称为“常仙”,常仙的头领,就是这常三太爷和常三太奶。
这些保家仙,都是多年修炼成仙的动物,但她们却很少直面见人,所以要通过一些不同寻常的人把自己的想法传达给人类,并借助这样的人的躯壳来做一些事,从而保佑一户人家,甚至一个村子。
具备与仙家通灵的人,就叫“大仙儿”,一般这样的人天生就具备这样的能力, 需要经历一场灾难、一次大的变故,或这一段磨难才能一下子激发出潜藏在生命里的这样的能力,这个能力被激发的过程,叫做“出马”。
我的奶奶“出马”是因为她最爱的一个女儿去世,在我爸爸之前,我大伯之后, 奶奶还有个女儿,也就是我大姑,两三岁的大姑就饿死了。虽然那个年代每一家都有好几个儿女,饿死人也是常见的事,但奶奶却因为死了个女儿悲伤过度, 一下子“出马”,成了“大仙儿”,人们都称呼奶奶为“六姑”。
奶奶之所以在村里出名,并得到大家的尊敬,是因为两个原因,
第一,是奶奶的确给很多人看好了病,当然大仙儿看的 病,不是普通的头疼脑热,也不是肿瘤癌症,而是“癔症”,所谓“癔症”是指招惹了鬼魂或者精怪,这些不干净的东西报复、捉弄人,使这些人得的一种说不清、治不好的怪病。这样的病当然是没法用通常的医术来治愈,只能大仙儿通过仙家的方法来驱除。
第二,是奶奶给人看病的时候,分文不取。有些感恩奶奶的,非要表示心意的,奶奶会勉强收一些香、蜡烛等等,当然这些也是用来供奉给保家仙的。
奶奶供奉的是常三太爷和常三太奶,也就是蛇仙。在我们家西面的一颗百年树龄的大柳树下,修了一个只有半米高的小庙。庙里供奉着用黄纸写的常仙的牌位,以及一些香炉果盘等等贡品。初一十五,奶奶都会斋戒,然后去烧香上贡。
当然这样的行为,在六十年代的新中国,是不被允许的,这是宣扬封建迷信,是要被批斗的。我们家也不例外,也曾被专横跋扈的“红卫兵小将”盯上过,听爸爸说,当时呼呼啦啦的来了一大堆人,要来拆了那座小庙,抓我奶奶去游街。但最后发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就再也没人敢来我们家闹事了。
我小的时候对这个特别好奇,就缠着爸爸给我讲红卫兵到我家“破除封建迷信”的事,爸爸会训斥我说 ,
“小孩子家家的,别打听这些事”,
每次爸爸这样训斥我,我就不敢再言语。不过越是不知道, 好奇心就越强,后来从村子里年纪大一些的叔伯大爷们的口中,零散的知道一些片段,拼凑起来, 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话说当年在下队,有个姓白的年轻后生,是兽医包有才的干儿子。包有才是做驴马生意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驴贩子。年轻的时候走南闯北贩卖驴马。攒了不少的钱,年纪大了,懒得再颠簸,索性在刘家镇买房子置地,利用贩卖驴马那些年学来的给牲口看病的本领,在本地当起了兽医。
这个后生, 就是他在外地做生意的时候,在路边捡到的弃婴。解放前的年月,大道上发现弃婴是在常见不过的事了。穷人家生下孩子,养不起,就扔到路上,或者扔到有钱人家的门口,至于婴儿的生死,就要看造化了。
包有才把这个婴儿带回了家,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大,给他取了名字,叫包书白。这名字取的文雅,也是希望他能做个儒雅的读书人。可这个包书白,只读了几年书就把教书先生气跑了。没办法,包有才只好带着他学兽医,读书不成, 好歹也学一门手艺,将来也能养家糊口。
包书白学兽医的时候,也 是吊儿郎当,包有才也拿他没有办法,谁让自己膝下没有儿女,只有这个捡来的干儿子呢,从小娇惯,现在想管,是管不成了。所幸由他去吧,只要不惹祸就行了。
后来赶上了**********,包有才家里比较富庶,政治成分不好,被打成“混入无产阶级的万恶走资派”,整天被红卫兵小将批斗,五花大绑的游街。包书白这个混混仰仗读过几年书, 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了村公所的门口,措辞严厉的要跟养他成人的干爹包有才划清界线,说包有才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地主老财,这些年打他,骂他,不把他当人看,逼他****喝尿,给他家当童工,受尽了欺凌和剥削。包书白拿着大喇叭 ,对围观的群众声泪俱下的痛数包有才的“累累罪行”。仗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得到了大家的同情。摇身一变,变成了“饱受资本主义地主老财剥削和压迫的无产阶级穷苦同胞”,加入了红卫兵,并很快成了骨干,并抛弃了“资本主义走资派地主老财”包有才的给他取的名字,自己改名叫“白胜利”
他整天带着一群人,东家打砸,西家批斗,那些他嫉妒的,看不上眼的,跟他有过节的无一幸免。而他盯上的最后一个目标,就是我的奶奶,出马了的大仙儿“六姑”。
话说那一天,奶奶起早就跟着爷爷,去地里干活。我家的耕地在村的最西面,离神秘的“柳树沟”不远,因为柳树沟流传着很多吓人的故事,人们都不敢轻易的靠近,这块田地没人愿意耕种。我们家刚搬来的时候 ,就分到了这块地。
白胜利带着一大群红卫兵踹开我们家的大门,气势汹汹的闯进来的时候,家里那时候只有大伯和爸爸两个孩子在家。他们本来是冲着我奶奶来的,见大人不在家,就开始打砸我们家泄愤。大伯上去阻止,被白胜利一脚踢翻。只有七八岁的爸爸身体瘦弱, 吓的躲在角落里哭。
他们砸光了我们家的锅碗瓢盆还不解恨,索性冲到我们家院子西面的那棵大柳树下,三下五除二,就砸烂了那个供奉着常三太爷常三太奶的保家仙的小庙,撕碎了用黄纸写的牌位,踢翻了供奉的香碗。
傍晚的时候奶奶回来后,见家里一片狼藉, 自然就知道发生了什么。爷爷气愤的要去找白胜利算账,被奶奶拦住。奶奶带着大伯和爸爸,一点点的收拾残局,爷爷愤怒的坐在院子里抽烟。
过了好一阵子,终于收拾出一点眉目。突然,大门又当的一声被踹开,白胜利又带着白天的那些人闯了进来,一进院就大声的喊叫;
“姓赵的,你这个宣扬封建迷信的无产阶级敌人,你给我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