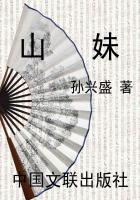那天,我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我打算利用将临的假期到南方的岛上去住几天。于是我忙着安排行程,打点行囊,那夜,我居然因此而激动得热泪盈眶。我想给你写别后的第一封信,一口气我写了四大张纸,然后想想,我又沮丧地捏掉了它们。
卖白茉莉的女孩从窗前轻盈的走过去,叫卖声传得好远,并且满巷都飘满茉莉花香。我蓦然怀念起南方的乡庄来了,夏季里南方的草原上葵花是否都开了?葵花呵葵花……曾写过一首抒情的短诗,沾满着七月葵花的香息,我将它藏匿在旧日记的扉页里。那时还仍是懵懂的少年,梦幻比谁都多,都圆美;懂得忧愁之后,我却沉默得像终年踩着满林凋叶的旅人。葵花不再是少年时代的葵花,梦也定了型,没有变化,没有色彩,梦却成了一首没有音乐的哀歌。
我从海岸归来,带回满怀的盐味,满袖子醺然的海风。你一定又会怪我再到海边去,只因为你怕我触景生愁。如果我说:“我到海岸去,只是纯粹为了看海色霞光。”你可会相信?你必须要相信我所坚守的信念,像一只鸟相信它的柯巢一般;我躺在金色的海岸,像躺在母亲的怀抱,那样的舒适、恬然,并且,我不会有太多的哀愁。
每次读到Wander这个字眼,我总是习惯性地阖上双眸,于是便有一片深邃的阔叶林在我望中。我看见一位身披红色斗篷,足穿芒鞋,手持芦笛的游唱歌者,他会将七孔的芦笛吹得令我为之泫然。泪光中,一个疲乏的老人,拖着沉甸的脚步,步向未知的远方,渐渐消陨在落日深处。深夜里,史蒂芬逊的短诗也回荡在我忧悒的眸色里——
在星光闪烁的夜空下,
请为我掘一个坟墓,
且在墓前遍种玫瑰,
伴我幽然永眠。
七月时,我必然会成为一个Wanderer。我将拾着满掌的落寞,漂流到南方的岛上,但无论到任何地方我还是想你。
我多么盼望能再为你唱一遍“初恋女”。虽然我的初恋已经击碎在海岸的浪花里。有人说:“第一次的感情是枚真珠,第二次的感情是尘土。”我相信这种说法。
你应该在你的发间缀一朵玫瑰,那么所有写诗作画的人便会说你华丽、俏媚。我们曾共舞过几支施特劳斯的G调圆舞曲?我们曾几次相伴走过那片狭长的海岸?那时我们唱歌的声音有多大,我们的舞姿多翩然。沙滩上踩出同样的足印,我们走了好长好长呵,像一世纪那么长。如果海风不将足迹用沙子掩盖,再一次潮涨时,浪花也会将它们轻轻拂灭的,我们的故事也将宣告休止。
我们来自不同的方向,一南一北,相识却是在多雨的北部海岸。有时我真想点着一盏风灯,到那片多雨多雾的海岸去寻觅你藏映在水中的柔情,且幻想:有一天,你会将一封蓝色小笺置于海螺壳里,让我前去俯身拾起。我们来自不同的方向,我们只是两片偶然交叠的云彩,相遇,交融,然后分散,继续我们原本寂寞的旅程。虽然那条熟悉的轨迹早已消逝净尽。而我的心中却扬起风暴,永不能平息的风暴。
我问:“还记得那个爱穿淡黄色毛衣的少年吗?”而你必定会答以万千沉默,白色的沉默。
夏季来了,我反而又想念起冬天,可以拥裘围聚在火旁谈诗的冬天,可以将每一句话哈成一团团奇异烟雾的冬天。有一天,我们会回到那冰雕玉琢的北国,一样会再围坐在暖炉边笑着、谈着。但那时我们已不再年轻了,笑起来时,眼角的鱼尾纹加深了几条,且已白发如霜,那时我会凄凉地忆起某年的一个夏季,我们相识在那多雨的北部海岸,我一定会很感伤的。
夜深时,我的眉心会紧皱,我的眼神郁悒。但天明后,我仍然会愉悦地去面对新来的一天;我会细细地盘算,散课后去看一回幼师中心的艺展,或者到咖啡屋去听琼恩贝丝的歌谣,甚至于有兴致去挤最后一场的午夜电影。说实在的,这些举动并不能带给我些微的欢乐,但这就是生活,谁又能否定了它们?
那天在海岸,临风小立,思绪里蘸满着海色,我的眼眸也深深蓝蓝。
有辉光自你发间悄然亮起,我便分不清是凌晨的星子抑或是夏夜的萤火了。我们隔着多少距离?远吗?远得像亿万光年外的星体那般迢遥。近吗?近得像你我凝视时眸与眸那般窄密。来年的夏季,我将一个人去绿湖轻荡舴艋舟,载一船柠檬色的满月,载一船浓浓郁郁的思念。
197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