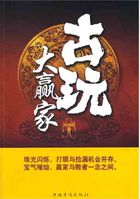这是一座空空如也的城,他来了,他走了,一切尘归尘,土归土...
似乎全世界所有大都市的机场都没什麽两样,有著各种肤色和语言的人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来来往往,熙熙攘攘。杨筝站在首都机场下行的电梯上想著,是有多少年没听到如此嘈杂而纯正的乡音了?B市人讲话,似乎总喜欢把舌头抡圆了,无论男男女女,说话总是那麽理直气壮,骂人更是骂得大义凛然,不像日本人,日语中有著太多冗长而无意义的敬语和拟声拟态词,过了这麽多年,他都没能习惯。
杨筝提前一步跨下电梯,快速向前走了几步,因为他看见闫言在不远处向他拼命招手,将近一米九的大个子使他看起来像只憨态可掬的熊,还怕他没看见似的,喊得脸红脖子粗,刚走近,闫言就一把把他熊抱住,“哎呦喂,兄弟你可回来了!”杨筝笑笑,颇有些无奈地拍拍闫言的背,闫言是他表哥,虽说是哥,但也就比他大几个月,两家又挨得近,於是从幼儿园到初中,他俩都是一个班,直到杨筝去了日本,但两兄弟经常视频聊天,所以倒也没生疏,这次听说杨筝决定回国,闫言高兴坏了,说是他的房租终於有人分摊了。
闫言开的是辆半新不旧的天籁,这时正堵在高架桥上纹丝不动,他像所有坏脾气的司机一样,骂骂咧咧地狂按喇叭,杨筝知道劝也没用,扭头看著窗外,B市的温度和东京差不多,但天空却是淡淡的灰,太阳虽明晃晃地在那挂著,但却像隔了层怎麽也擦不干净的毛玻璃,看来这些年时常看新闻说这里雾霾严重,确是实情。
前面的车终於动了,闫言喜形於色,转头对杨筝说:“对了,今晚老郑生日趴,听说你回来了,非让我把你也带上,你去吧?”
杨筝收回目光,其实他和老郑不熟,老郑是他们的初中同学,但杨筝只读了一年初中就去日本了,闫言和他却是好兄弟,杨筝微微抿了下唇,就看见闫言一脸的不要不要,他好笑地点点头,“但你先送我去一趟疗养院!”
车开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到位於城郊的疗养院,这里位置偏僻,但环境不错,也很安静,杨筝与闫言进去的时候,刚过十一点,小花园里,几个穿著病号服的人随意溜达著,草坪上,一个女人坐在轮椅上,正仰头盯著眼前那棵木樨看得出神,那女人的头发有些灰白,但皮肤很白,瓜子脸,看得出年轻时是个美人,但此刻,她却以一种狐疑的目光看著那颗无辜的木樨,眉头紧皱,嘴里碎碎念叨著什麽。
杨筝走近了,才听清楚,“咦,花呢?花到哪去了?....”此时已是深秋,木樨的花期早就过了,杨筝站在一边,静静地看著那个女人,直到很久,那女人才注意到旁边的青年,却是一脸警惕地看著他,“你是谁?”
那一瞬间,杨筝的表情突然变得有些奇怪,脸上的肌肉不自然地收缩著,像是在极力忍受著什麽,过了半晌,他才挤出一个很勉强的笑容,他单膝跪在那女人面前,拉过她的手:“妈,我是小筝,我回来了!”
那女人痴痴地看他一会儿,眨了几下眼睛,像是努力地去辨识眼前的这张脸孔,“你是小筝?你是,儿子?”
杨筝笑著点点头,抓紧了她的手,谁料那女人却像是被吓到一样,拼命地甩开他的手,大叫起来:“你,你不是小筝,你不是我儿子,我不认识你....”
边说边挣扎,眼看著就要摔下轮椅,杨筝忙扶住她,她却挣得更凶,甚至哭喊起来,不远处的闫言和医生也跑了过来,闫言过去把她扶起来,这次她却没有拒绝,像是看到救星似的,一把扑到闫言怀里,“小筝,小筝,你来了....”
她一边抹眼泪一边小心翼翼地指著杨筝,“他是坏人,我不认识他!”
闫言一时也有些尴尬,但还是先将李洁云抱上轮椅,他抱歉地看向杨筝,拍著李洁云的背安抚道:“妈你不要怕,他是闫言,闫言你都不记得了?是二姑的儿子啊!”
“闫言?”李洁云的脸上还挂著泪水,但立刻就笑了起来,合手一拍:“我想起来了,是闫言啊,妈当年还带你去吃他的满月酒呢!”
闫言顿时无语,“闫言比我大,他是我表哥!”
李洁云却没管他,拉过杨筝的手:“小言啊,你怎麽从来都不来看我的,小筝说我生病了,很快就好...”
杨筝突然有种想立即挣开那双手的冲动,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却只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李洁云很快就觉得这个表情奇怪又不说话的“闫言”太没意思,於是又转头和自己的“儿子”说悄悄话,“小筝啊,你最喜欢吃桂花糖糕了,妈摘了好多花瓣,等你放学了就给你做,但花怎麽没有了.....”
後来到饭点的时候,护工就把李洁云给推走了,回去的路上,杨筝一直没说话,闫言实在憋不住,干笑两声,“小筝你也别难过,舅妈是一时糊涂,你多来几次她就记得你了!”
杨筝看著闫言,却是微微低头,“闫言,谢谢你,这些年替我照顾我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