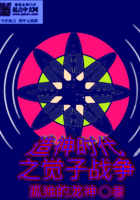我拉起青袖,向红云使了个眼色,起身向外走去,其它姐妹见我们离开,也纷纷跟了出来。
为什么不让我帮小青?在走廊上,青柚不解地问我。无无仗着自己红,伙着她们几个一直压我们的单,你就打算这么忍下去?
靠着墙,听着远处传来的小青委屈的哭声,我淡淡地说:现在出手,就是摆明了跟无无为敌,以你我现在的样子斗得过她吗?还有,就算现在你现在出手帮了她,她也不会领情的,你和敬的事儿,让她打心眼里就看不起你,小青的德性你不是不知道,你要是出手了,没准她就把气撒你身上了。
青袖气愤地说:关她屁事,你以为我怕她吗?我只是想借这个机会打打那几个贱人的气焰,****妈凭什么这么踩我们,夜总会又不是她家开的!
人无百日好,花无百日红,没有人会永远站在金字塔顶端的。我说,接过紫烟递来的女士烟,就着她的烟头点燃,看着眼前慢慢飘散的烟雾,微微一笑,往走廊深处走去,瞄见月月她们几个得意地谈笑着进了包房,青桔踟躅着跟了上去,不禁皱了一下眉头,不过瞬间释然。这个世界,谁都不可能是谁的人,利益驱动下,翻脸不过分分钟!
置身于这个血腥的场所,就得适应这里的规则,别去抱什么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想法,要在这个行当里继续,不管愿不愿意,潜规则就是踩着别人的肩膀让自己更近地靠近阳光才能进行光合作用;所以,脸上扣着热闹的面具,内心永远保持清醒,把本真藏到光年之外!
那晚结束后,阿进特意让我上了他的车。铺天盖地的倾盆大雨,略低的地方积水成渠,车灯如鬼眼呼啸而来,带起水浪铺开如花瞬间又消失。欢场散尽,买欢的也好、卖欢的也罢,都已经消失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做着人之初就会的事儿。我茫然看着雨刷急速上上下下,心里反复思量一会儿如何回答阿进的话。
是的,我知道阿进今晚为何让我推掉客人,我更明白他在送我回去的路上要说什么。
古语形容我这样的女子是“心比玲珑多一窍”,我的心早被生活的利箭射成蜂窝。父亲过世把母亲变得喜怒无常,在家里我得小心翼翼观察母亲的脸色行事,生怕哪里不对她就晴转阴了;在学校,我得时时注意老师同学的脸色,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其实那些用抄写我作业换来的一时笑脸也说不上是友谊吧?要不然,他们的脸为何在记忆里那么模糊!
阿进只说了一句:青桐,你让进哥为难了。
我动了一下僵硬的身体,垂下眼帘,说进哥,我明白,明晚我把多领的钱还给您!
他没接话,过了一会儿拍拍我放在膝盖上的手,说还是你懂事,进哥是真想帮你,但是你看到了,进哥这样做,对其它人不公平。
我嗯了一声,轻声说我明白的进哥,没有关系,就按咱们的规矩来吧,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第二天,我当着所有姐妹的面,把多领的8千多块钱退还给了阿进,眼角余光瞥见圆圆悄悄出去,明白她这是去给她主子打电话报告战果了。
不过半小时,无无一身纯白蕾丝礼服微笑着走了进来,手上拿着两大袋糖炒板粟,亲热地跟每个姐妹打招呼,见到换好衣服出来的我,热络地把板粟递到我面前,说还是热的呢,挺甜的,吃吧!
我伸手取了几个,笑着问她。感冒好了吗?怎么不多休息几天?
好一些了。她说,开心地笑。我得来上班挣钱啊,否则就没钱花了。
这时那个矿老板的一个手下走了进来,看着无无说,何总带了五个朋友来玩,在4个2,请姐姐带几个妹妹过去。
无无笑容如花,媚眼飘飘,说我选的姐妹,你们可不准欺负人家!
放心放心,我们哪敢啊!那人讨好地笑,转身先出去了。
无无点了圆圆、玉儿、如烟、月月,最后瞄了一眼青桔,貌似无心地说你也来吧,便走了出去。
青桔偷偷瞄了我一眼,起身跟了上去。
青袖探身看着青桔的背影消失后,这才回头说道:她什么时候成了无无的人?
红云也探询地看着我。
紫烟嘟着嘴轻轻吹着着烟圈,说这门庭换得可真快啊!
青袖见我不说话,过来扯了扯我。青桐姐,你说青桔这是什么意思?
我面无表情地说:什么意思都没有。你没听见对方要五个人吗?她正好差一个,就让青桔去了。
青袖怀疑地看着我,紫烟挣灭烟扔进嘴里,对我竖了竖拇指,含笑说你果然跟我们这些人不一样,牛B,需要我做什么,甭客气!
我笑着看她,她也正看着我。我们眼里的含笑,不言自明。
这出由无无导演的戏就这么结束了。我损失的不过是几千块钱,却让我摸清了无无的底线。欢场中的明争暗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躲在幕后的冷箭防不胜防,射灯下的对手反而就没那么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