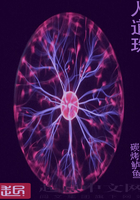当然,要是慧明是个男孩,也许情况不同。
因为如果何宝贵跟别人说起自己家的情况,别人就会问:你家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在听说是女孩之后,大都会说:女孩呀,那就离了再找一个老公啰!
男孩女孩就该有这么大的区别吗?何宝贵很奇怪这样的逻辑。
但是,好像这是实话。
她又不是生不出男孩。
何宝贵想起那个滑掉男胎。要不然也快一岁了。因为就比慧明小一岁。
廖家兄弟都以换老婆为本事。这些倒了血霉的女人过着“饶君修成深红色,也被旁人说是非。”的日子。
刘兰芝是这样,何宝贵也是这样,廖又德的二嫂也是这样。全部过着霉头过的日子。
何宝贵的错,只在于功高盖主,没有“一索而得男”。
这样演绎出来一幕幕稀奇古怪的故事。
在小镇的时候,虽然没有人为他们劝架也没有敢对何宝贵说三道四。
来到这里,就大不相同了。何宝贵什么都是错的,什么事情都有人干涉。尤其田金枝。
何宝贵结婚只在家里呆了五天就出来了,除了生孩子时跟婆婆打过几天交道,其余时间除了受廖又德的制约,别人不敢干涉她。
现在来到这里,田金枝竟然像个旧式的婆婆一样压着她。
比方说,明明是廖又德要在她上吵架的,田金枝却说何宝贵跟他在摊上吵架是打击廖又德的威信。
何宝贵从来不知道廖又德应该有什么特别的威信。任何人只是应该讲道理不是吗?
何宝贵就想,大概他们这帮人在提起廖又德的时候,都是拿他曾经进过号子的经历虾唬人的吧,而这是何宝贵希望最大程度地淡化甚至被所有人遗忘的事情。她不希望人们提到她的老公就像在说一个土匪一样,更加不希望她的孩子被人记住有一个经历不光彩的父亲。
何虾贵有一次来看妹妹。正好何宝贵不在摊上,前一天廖又德当众打了她,她这一天就在家里睡觉。
怎么有动力做生意?这一年眼看快过去了,钱是越来越少了,还要被廖又德当众打。
似乎睡在床上可以暂时麻痹自己。这是何宝贵给自己减压的方式,也就是这样不当的方式,让钱加速地被廖又德控制了。
也许是廖又德知道何宝贵被打后会这样沉睡,所以为了达到目的,经常打她。
何虾贵听到几乎所有人都在说何宝贵的不是。
这在小镇的时候是绝对不会有的。
S市是二级批发的地方,何宝贵们买的鞋也是批发兼零售。
廖又德进货,何宝贵卖货。
由于何宝贵语言功底好,所以他们的生意比别家都要好。
有个顾客赊账进了货,好久不来还帐,廖又德就去讨要,因为赊账的时候是留了地址的。
廖又德回来后就说没有要到帐。何宝贵不信,因为他的戏演的不好,听不出没有要到帐的生气和着急的口气。
再说谁会为了欠货款把自己经常进货的路断了?
廖又德这是明着“打夹帐”,其实,除了他私自卖店后回家那段时间是以何宝贵为主经营着生意,正常地赚了一点钱之外,之前和现在廖又德都在大肆“打夹帐”---大肆鲸吞何宝贵的劳动心血。
这一年,他们的鞋子卖得就剩一双进货回来就是同边的鞋子,比谁家都买的干净。
然而,何宝贵最后看到的钱只有五千!
比上一年那一段时间出来的近万元少了一半。
这一年,廖又德无疑是超满意的一年。
腊月二十八歇业以后他提议两人到外面的澡堂洗了澡。
回家后,家里的煤炉子熄火了,廖又德就说去他大哥家过年。
在去她大哥家的路上,廖又德主动提出来两人去照一张合影照,回家好补办“复婚证”。
关于“复婚”一说,何宝贵第一次听说,是在那次从小镇来看慧明,也就是田金枝提议让廖又德给何宝贵带货的那次。
“离了婚还可以复婚的,这附近有个女人好想复婚,她老公就是不肯,”,那时田金枝怂恿何宝贵复婚。--这之前,何宝贵是不知道有复婚一说的,
廖又德买了一百多元钱的炮仗给自己的侄子,换来的是他大哥大嫂到晚上快十点了才做熟的一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