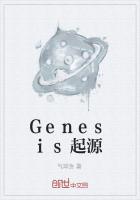公元2013年。盛夏。星期天。国际大都市西京的响水街上。
太阳毒辣,持续的高温让街道的热度己经可以烤熟牛排。但鲜有行人,这条街最热闹的时候还没有开始,通常要到傍晚,南风把清凉的空气输送进来,娲居在房子里的人们才会纷纷走出家门,透口气,散散步,买点东西。
所以通常,别的摊子都是晚上七点才会陆续摆出来。只有一家摊子例外,它从早上出摊就没有收过,一直要坚持到傍晚散场。
它也称不上什么摊子,只有两个马扎几张素描纸而己。一个马扎上坐着摊子的主人,另一个马扎等着顾客上门,但很明显它没等到过几个客人,它的旧和残破不是被人为坐出来的,而是被无情的太阳烤出来的。
那个摊主,如果说他从前是这座城市一流的画家,一定会没人相信。他现在是一个半秃了头发的男人,眼泡浮肿悬垂下来,几乎像两只鹌鹑蛋了,典型的酒糟鼻,红的让人看了会恶心的鼻头。一件白色的圆领纯棉老头衫被汗渍了又渍,几乎是一块脏抹布了。他还无所谓地把他撩到几乎颈下,露出布满了伤痕的凸出的啤酒肚来。
总之,他都把自己糟蹋成那样了,没有人会想坐上另一个马扎,让他给自己画张素描像的。
现在他倚着人行道后一家单位的铁围栏,己经昏昏欲睡了。
路过两个小伙子,相互对视一下,给个眼色,然后一个人坐下了,敲敲栏杆喊醒了摊主。
他揉揉红烂的鼻头,说要画像吗?一张二十。
小伙子说老头,你这样儿,值二十吗?
摊主又眯上了眼,不理他了。
站着的那个赶紧说画,我们画。高手在民间嘛,保不准二十一张,将来拿出去卖二十万一张呢。是不是,叔?
摊主又睁开了眼睛,也不多说,拿起碳笔,也没个画夹之类的固定,就纸撂着纸撑起一个角度,自顾自忙活起来。涂抹了几笔,没看那个小伙子一眼,哗哗就完成了。
他把素描纸往小伙子眼前一扔,好了,给钱,二十。
坐着的小伙子脾气大,嘿,老头,你糊弄我们呀?顺手捡起那张画像,伸手就要撕。可就瞄了一眼,他也有点蒙了,他本来是个连眉,看上去就有点恶,可不知道怎么,被摊主那么几笔勾下来,眉还是那两道眉,感觉却不一样了。他从自己脸上竟然找出点江湖大人物的豪情和悲凉来。
他没撕,递给另一个看,说你瞧瞧,这是我吗?
另一个看一眼画像,再看一眼真人,说了像,又说不像吧!又说这他妈就是你的眉毛啊,不是你是谁!
摊主不耐烦了,要是不要,不要拿来!
坐着的赶紧把画像拿到手里,要,我要。他有点舍不得的意思了。越看,越觉得自己还挺有气势的,还挺好看的。
站着的就付钱,从大短裤的后兜里抽出一张百元钞票,递到摊主手里。
摊主捏到手里,嚓嚓两声,竟然直接给撕成碎片了,随手一扔,小子,我画的都比这个真。
站着的就有点穷凶极恶的意思了,我就这一张,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该找的钱,一分也不能少!他己经逼到摊主身前了,摆明了是要强抢。
摊主的大肚子往前一挺,坐着的那个还在自我陶醉呢,冷不防手里的画像也被撕成两半了,那变好看的眉毛跟碎了的假钞一样,散了一地。然后他把汗衫再撩高一点,直接忽扇到脸上了。
坐着的那个一蹦三尺高,啊,我的画像?那连着的眉毛耷拉下来,瞬间又变回街头衰人了。站起来,一脚踹碎了坐着的马扎,胳膊上鼓起一疙瘩肌腱来,一把掀起了那抹布一样的老头衫,拳头晃到摊主眼睛底下了。再给老子画一张,听见没有?今天不赔老子这张画像,我就把你这摊掀了。
另一个在旁边倒乐了,掀什么掀,就两破马扎,一个还被你踹碎了。
不管,反正得给我重画一张。
咱们是出来弄钱的,你犯贱啊!要什么画像?想看,自个儿回家照镜子得了!
两个人,唾沫飞溅,嗓门大的像锣一样,一个要钱,一个要画。
摊主根本没反应,照旧眯着眼睛一副睡着了的样子,当那两人是嗡嗡嘤嘤的苍蝇了。
终于惹恼了其中一个,呼的一拳,摊主红通通的酒糟算里滩出一股血来,马扎本来就不结实,这么一弄直接就断了。他挨了一拳歪在了地上,再要起来又被另一个踩在了肚子上,再挣扎又挨了一脚。
这时候正是最酷热的时候,没有几个行人经过,也没有谁多管闲事。
倒在地上的摊主干脆不动了,瘫了的泥一样。
于是一个小伙子开始搜他的身,他浑身的口袋干净的像被水冲过,连张毛票也没有。
两个人拿他没招,只能泄恨地再踹他几脚,转身悻悻地走了。
被撕碎了画像的小伙子走了几步,转身又回去了,从一堆碎片里挑出了那张素描纸的残骸,小心翼翼地揣到了裤兜里。另一个说你干吗,拿回去烧纸用啊!
他说哥,我总觉着这老头邪性。我以前从来没觉着自己好看过啊。我得拿回去拼好了它,再找张像框装进去。
就在这个过程中,离那个摊位不远处的拐角,一个穿着牛仔短裤露出小麦色肌肤的女孩子,刚想要冲出去,却被另一个身材矮胖、留着波波头的女人给拉住了。
两个人虽然撕扯着,却都不敢大声说话。
年轻的女孩子把头上的棒球帽拉到了最低,再加上墨镜,基本上就看到不长相了。可猜得出来她应该很漂亮。
被身边的女人拉住了,她呆呆地看着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男人,眼泪己经顺着腮边流了一路。她说芳姐,你让我去看一看他,好不好?
芳姐说怜心,你别做傻事了。你先回去,呆会儿我找人送他去医院,看情形应该不严重的。他这样子也不是头一回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怜心说那芳姐,你快点找人,这么热的天我怕他受不了。
芳姐说好,那你听话,先回公寓等我吧。
怜心有点不情愿地上了出租车,看着芳姐向她招招手,车呼地一声开走了。那个躺在地上的男人的影子,停留在她脑海里,像电影的定格画面一样挥之不去。
回到位于近郊的一座公寓房里,一进门她鞋也没换,扑进客厅的沙发里号啕大哭起来。边哭边喊着,我恨你,我恨你们。不知道她在恨的是谁,可是她的恨里分明掺杂了太多复杂的情绪。
临近傍晚芳姐回来了。进来的时候,怜心换了家常的运动服,披散着一头的乱发,眼圈己经哭得发乌,一副呆呆的样子。看见芳姐,跳起来就问他怎么样了?
芳姐放好包,换好鞋,坐下来,喝两口凉茶,才告诉怜心,他没事了。送去医院就是一点皮外伤,让护士简单消了一下毒,处理了一下。本来要送他回去休息的,可他坚持要回去摆摊,我就送他回去了。
怜心说他那个样子,还去吗?
不去怎么办,谁给他酒喝?
怜心不说话了,她心里某个痛的地方又被刺了一下。
芳姐赶忙补了一句,临走我塞了一点钱给他。你别担心,他饿不着的,就怕他拿了钱又跑去喝酒。
怜心不好意思地看芳姐,总是让你操心,对不起。
芳姐只说没事,一边往厨房走,问怜心晚上想吃什么。系了围裙,打开冰箱的门,却只有牛奶和几个鸡蛋,还有放了很久变硬的面包片而己。不由地皱起了眉头,怜心,最近几天是不是都没好好吃饭啊?看你的冰箱空成什么样子了。
怜心说吃了,就在附近小餐馆吃的。
芳姐默默地摘了围裙,走回怜心身边,替她打散一头纠结的长发。怜心,最近公司给你安排的通告很少,你过的很困难是不是?
怜心还了芳姐一个体谅的笑,没事,芳姐,你也为我争取了一些机会,怪我自己不争气吧。
芳姐说,我明白,那都是一些没人肯去的通告,安排你去塞牙缝而己。
怜心说我一个不知名艺人,有活动己经很开心了。
芳姐就不说话了,从茶几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烟,燃了,静静地坐下来,看着怜心窗外那处正在开发的楼盘。高高的塔吊上,是通明的灯光。
怜心,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机会,可是机会不是人人都能抓得住的?你为什么入这行,我不太明白,可你为什么到现在也红我却清楚。你啊,就是太爱惜自己了。在这一行太爱惜自己的人,意味着你脸皮不够厚,你没办法豁得出去,那你怎么能吸引到众人的关注呢?
怜心亲昵地把头枕到了芳姐的肩上,那肩膀厚实而温暖,她于是忽然就觉得开心起来。这几年除了芳姐,她再没有对谁这么亲昵而孩子气了,芳姐更像是她真正的亲人了。
她像个孩子一样逗起了芳姐,你早知道我是这个样子啦,还要带我入行?怎么不拒绝我?是不是成心的捏?
芳姐拿指尖点了她的额头一下,拿你没办法,要不是不能拒绝你,我怎么会带你这么傻的人进来,还一熬这么几年,眼看着一拨又一拨的人都上来了,你都快成老人家了。
怜心扑地笑了,我要是老人家,那你岂不是千年的妖精了?
芳姐也跟着笑了,我要是修成精了,早把你点拨透了,还让你这么不开窍啊?
怜心说芳姐,你对我最好了。
芳姐站起身,是,我对你最好了。没办法,对你最好的人只有再管你一顿晚饭了,要不然我都不忍心走。起来换身漂亮的衣服,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怜心提提自己的运动服的裤子,转一圈,说芳姐,这样不行啊,我觉着这身挺漂亮的。
芳姐故意眼睛一眯,鼻子皱着,给了她一个无比嫌弃的表情。快去换吧,别撒懒。
怜心听话地回到卧室,再出来,却还是牛仔短裤,跨栏背心,棒球帽。
芳姐拿她没办法,该选你去当运动员才是,把你委屈在演艺圈真是浪费了,就这么喜欢这一身啊,天天穿着。
怜心说芳姐,我就觉得这一身自在,凉快,还超级舒服,再说了,她故意摆一个曲线出来,芳姐,你不觉得我很性感么?
芳姐说哎哟哎哟,你的眼神电着我了,你怎么不拿这眼神去对付那些观众,还有李董他们呀?一麻一个准。
怜心撇嘴,才不呢,不乐意。挽起芳姐的手,蹦蹦跳跳地像个孩子一样。
芳姐再次拿她没办法,只能被她拖着拽着往外走。问怜心要吃什么?懂事的怜心说吃点大餐吧,却还是只带着芳姐去附近一家干净清爽的小餐馆,点了两份最家常的套餐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