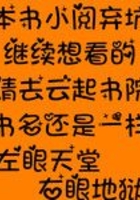赵班长说完,若有所思地注视着远处的神女峰,仿佛成了一座石雕。
男知青玄曜说:“神女峰如一把利剑贯穿天地,南疆部族认为神女峰是连接着天地灵的神锋。历代南疆部族宗女在继承大祭司后都要在血月之夜登上神女峰,替沉睡的‘血阳女巫’守护南疆。”
男知青周浩用手挪了挪厚重的方框眼睛,不可置信的眼神表明他是一个务实的唯物主义者。他分析说:“赵班长描述的这段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土耳其嘉里坡里地区失踪的英军有些相似的地方。在1918年,有800多名英军正向一个山顶充满灰色迷雾的高地进发。当时除了英军头顶的天上有块面包状的白云漂浮外,四周都是晴好少云的状态。当这支拥有800多名英军的部队进入迷雾后,山上的雾气徐徐上升,到山顶的时候组成了一团厚厚的白云,最后与天上的那团面包状的白云合而为一,渐渐飘离开了。这时山上没有一丝雾气,所有植被清晰可见,唯独不见这支步入山顶的英军部队……”
周浩看了看远处的巫山神女峰,接着说“当时英军以为这支部队成了土耳其方面的俘虏。直到战争结束,土耳其方面几次澄清没有俘虏过这支部队中的任何一名士兵,英军经过调查核实了这一情况。在找寻无果的情况下,只能在该军档案上写上失踪二字。我怀疑这支部队可能遭遇到了十分罕见的超强陆地龙卷风,这种龙卷风来的突然,去的也突然,可以轻易把行人卷至万米高空……”
队里一位川区的女知青听着挺玄乎的,问:“啥子龙卷风?还能把几百人卷到天上,我看啊,莫不是让李天王的宝塔给收啰?”其实队里谁也没见过周浩说的龙卷风,周浩解释说龙卷风形状就像一个从天而降的巨大漏斗,呈螺旋上升,它的破坏力能把一俩解放牌大卡车摔成一堆废铁……
另外一位内蒙来的女知青说:“你说那东西俺或许见过,就在俺们那有个湖,一天有个白色的‘巨龙’从天而降,直接把‘龙头’插到湖里,外形就像你说的那个样子。俺们家离湖也就几里地。不一会天上就噼里啪啦开始下雨,我的映像很深,那场雨很奇怪,就像是有人从天上用瓢子一把一把往下淋。最渗人的是,这雨水有股浓浓的腥味,数百条鱼、青蛙、水蛇和那豆大的雨滴子一起落下。不一会的功夫就爬满了屋顶……”
周浩说那是水龙卷,也就是在水域里发生的龙卷风,可能由于湖水被卷到天上连带着水生动物一起被‘搬’到了别处,才出现了‘天降鱼蛇’的离奇现象。
我看这位周浩同志对自己的科学解释十拿九稳,说道:“即使是龙卷风那也会留下蛛丝马迹吧?比如周浩同志说的英国军队失踪,那为什么山上的植被安然无恙,人却被卷到天上,按道理龙卷风把一颗树连根拔起那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对吧?而且把英军失踪的例子套在神女峰上,这血红的宫殿又如何解释,你不会告诉我说这龙卷风能把一座宫殿搬来搬去?”
周浩被我说的哑口无言,其他知青也是满脸疑惑地盯着他看,似乎期待他能自圆其说。我看他一脸尴尬,知道自己刨根问底,不留情面的学术派作风又犯了,道:“周浩同志说的也是一种假设,最后的谜底不也是在无数个假设后经实践得来的么。不过,当人类试图解开自然谜题的时候,这个世界会告诉我们,人类在自然面前永远只是个小学生。”
男知青周浩惊讶地看着我,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漏出了些许激动之色。不知道是因为同为学术派家庭出身有惺惺相惜的感情,还是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感慨。赵班长这时从沉默中缓过神来道:“俺老赵只是个粗人,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的话,俺是听不明白的。不过这巫山确实邪的很,我们如果进去可得有个心理准备。”
……
看到围坐着的年轻人脸上漏出了一丝焦虑和不安,赵班长转移话题问:“组织上跟俺说你们之所以来到这么遥远的地方下乡,是因为家里觉悟不够高,或者犯过大错。这个,都跟俺说说,都犯过啥大错?”
男知青玄曜第一个开口说:“我们玄家祖辈是玉县大户,最繁荣的时候拥有三百多长工,专门架桥修路,兴修水利。玉县众多楼台庙宇都与玄家有关。后来红卫兵说玄家只拜神,不拜马列,是社会主义毒瘤。玄家就这么散了……”
我接着说:“我的父母是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和考古专家。学校把父亲视为墨守成规的老顽固。我父亲对被盗的面目全非的清皇陵研究后,曾在刊文上说过‘可在名誉上保留皇室的身份’。就是这一句话,成为日后史家被批斗的根源。当年组织上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说是对于父亲这样的封建老顽固,道德败类,皇权思想走狗要坚决打击。”
“而父亲为了我不受到牵连,声称与我断绝父子关系。就这样我‘脱离’了史家,组织说我是知错能改的好孩子,问我是否愿意到祖国最遥远的南疆大山。我想了想离开那里也好。”
也许是同病相怜的缘故,我刚说完,对面的女知青“呜呜”地抽泣起来。后来一问才知道这个女知青姓那,是个来自内蒙的满族姑娘,本姓是叶赫那拉氏。可惜现在是新社会了,否者她也不用隔着千山万水来这儿受罪。
赵班长不愧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兵,一看到下属‘士气低落’,又开始转移注意力。
他叹息道:“人啊,哪有不犯错的。”接着从口袋里拿出一小包东西,声音颤抖地说:“你们看这东西,是俺战友留给俺地。在俺最想他们的时候,就吃一口。你们要是伤心也尝尝。”说完赵班长把它递给我们看,这是一块黑色的东西,包装上写着满满的洋文,背面还戳着‘madeinUSA’的字样,我一闻原来是一包美国生产的巧克力。
我问赵班长哪来的这东西?赵班长抬头看了下天说:“是从俺战友死后衣兜里拿的。”
我心中刚想骂赵班长把死人的东西拿给我们吃。可紧接着赵班长情绪有些激动地说:“俺那些战友,死的烈啊。那年朝鲜的冬天零下十几度,俺的战友趴在雪地里伏击敌人,可一等十几个小时过去了,敌人都没什么动静。后来趁天黑,俺过去一看,俺的那些战友全部趴在雪地上冻死了,脸上结满了冰霜。手上还随时准备扣动扳机……”
听到这里就连刚才还在低声抽噎的女知青都安静了下来。赵班长接着说:“俺当时只是个通讯兵,敌人出现的时间比俺接到的电报晚了整整十二个小时。俺一直怀疑是俺听错嘞……”说到这里赵班长停了下来,坚毅的脸庞上有几条淡淡的泪痕。原来这个性格刚毅的老兵居然有这样的故事,他一直在内疚是自己害死了自己的战友。
“整整一个排就剩下俺一个通讯兵。敌人来了,近距离发现俺的战友,先是吓了一跳,凑近一看这些来自中国的志愿军已经全部被冻死了。大雪掩埋了他们大半身子,由于死的时候手里紧紧地握着半自动步枪,无论美国大兵如何拖拽,都无法从俺战友手中拿走任何一支枪械。后来敌人站成一排向死去的中国志愿军脱帽致敬后就离开了……”
“只要看到天上的星星,俺就能看到死去的战友。”说完赵班长再次抬头望向了天空,脸色却阴沉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