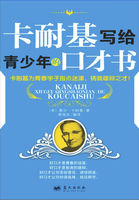眼看子瑜就要跌落台下,去病一个虎步跨上前,伸手接住了子瑜,将一张热脸贴在子瑜那滚烫的泪脸上,那烛火熊熊燃烧的光焰在他那眼中闪动,“子瑜,我们回家……”
琴姑见冠军侯霍去病抢了石岩子,众随从跟着离去,心中大苦:这如花似玉的美人可是毁了!想着石岩子的诅咒,琴姑就浑身打颤,深悔不该让姑娘今日奏琴,如今却是悔之晚矣。
去病抱着子瑜策马回府。到了府上,抱着晕厥的子瑜下马,脸紧紧地贴了子瑜脸,“子瑜,我们到家了。”子瑜脸火烫,去病摸摸身子,更是滚烫,去病那心就沉到海底了。
“快,去宫中请太医!”去病回头吩咐霍祁,他则抱着子瑜快步向曾经的居室而去,到了院门口才想起这里已是芷若房,就转了方向,朝书房而去。
“霍连!抱两床被子来。”去病又吩咐道,“叫仲叔来!”
室内已睡的芷若早被门外杂沓的脚步声惊醒,侧耳细听,就听去病喊太医,又要被子,还唤管家,很是诧异,就披衣下榻,喊了荷花,“你去瞧瞧,公子出了何事?如此慌乱?”荷花打着哈欠,一脸迷糊,随手摸件衣裳穿上就出了门,跟着脚步声而去。
去病一直抱着子瑜,等霍连在卧榻上铺了两床锦被后才将子瑜放下,盖好他日常被子,就挨着子瑜,一屁股坐在榻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子瑜。
子瑜双眼紧闭,泪痕斑斑,赤潮脸颊若朝霞,鼻息柔弱似游丝,看得去病悬着的心紧了又紧。
轻轻擦拭了子瑜泪痕,收了珠串,又摸了摸子瑜额头,去病皱了眉,回头看着霍连,“你去坊间,请那姑姑和日常服侍的人过来,我有话问。”
见大管家霍仲已经进屋,就道:“仲叔,这是我在草原娶的妻室,从今日起就住书房,你安排两个婢女住书房外间,夜里有事好唤。夫人如今病着,你叫他们全都仔细,出了事,我只找你!令厨房多烧点热水,等会儿,我给夫人洗脸擦身子。还有,叫婢女准备洁净衣裙,我给夫人换衣;再就是安排人手熬药,夫人的药好了,端过来,我亲自喂;通知厨娘,马上熬粥,随时备着,夫人醒了,喊吃就必须吃上热粥。以后,等夫人病好了,你好好把这里收拾一下,要像个居室的样!”
去病有条不紊地一一布置,考虑之细致,还自己亲自动手,霍仲从未见过,听得张嘴,一脸惊诧。正踌躇,见去病看着他,赶紧应声安排诸般事项。
很快,张太医就急急进了里屋,见去病一屁股坐在地上,慌忙上前,“冠军侯有病,怎可直接坐地上?”手一伸,就上前欲搭去病手腕。
去病赶紧爬起来,向张太医施礼,“张爷爷,辛苦您了,不是我看病,是这位姑娘看病。”去病转身躬让,请张太医问诊子瑜。
张太医是一老者,白发白须,从小给去病看病,医术好,人也慈祥,去病一直尊称张爷爷。
张太医知不是去病,正了正因急迫而戴歪了的头冠,慈眉眼眸看着卧躺。榻上女子,脸颊赤潮,鼻翼翕动,昏迷不醒,显见高热着身。和善的张太医沉了脸,去病将子瑜手从被中摸出,令人垫了席垫,张太医赶紧坐下,搭了脉,点头抚须看诊。
一盏茶,子瑜两手脉看毕。两人离开里屋去了外间,去病喊茶时,张太医已在绢帛上写了药方,交与霍祁快去抓药。
“这姑娘身子很弱,恐落病根。今日又受了极大刺激,急火攻心,伤了五脏六腑,如今高热缠身,这病恐怕一时半会儿不会好。”张太医本低首抚须自语,立时,抬头看着去病说,“这姑娘不能再受刺激,你要静心一点,不能和她争吵。女子嘛,多让让,消消气儿,自然恢复就快。如再怄气伤心,有反复就不好办,你要有所准备。”
颔首沉吟一会儿,张太医又道:“今日我开了药方,今晚赶紧喝,两个时辰一碗。再令人擦拭身子退热,明日再按时服药,高热近日就能尽出,调养月余,这姑娘的病才会慢慢好起来,不过她身子已是亏虚,须慢慢养才行,你这段时间不能急迫。”
张太医已将子瑜看成去病之妾室,要去病行床榻之礼时有所节制,去病倒不在乎,只疼惜子瑜,诺诺地应了声。
去病将张太医送出府门外,眼见马车渐渐离去,去病正欲进府,却不想,转头就看见街尽头一队火把向霍府策马而来。
到了府门口,策马之人都翻身下马,为首廷尉张汤见去病一人站立门口,握拳施礼道:“叨扰冠军侯!”
“张大人深夜到本府,不知所为何事?”去病负手而立,冷冷问道,没有一点迎客的意思。
“有人来报,霓裳坊乐伎石岩子辱骂大汉官员,我等前来捉拿,请冠军侯放人!”
“这石姑娘在本府上,在下自有处置,不劳烦张大人。”
“按律制,民众犯法,应由官府审讯判别,以律定罪,冠军侯不能私自用刑!”张汤知道去病大胆,且傲气,武帝也偏爱。今夜,一贯眼中无人的冠军侯居然被一伎人大厅之下诅咒,这冠军侯不知会怎样对待这姑娘。张汤一听案报,就及时策马过府而来。张汤也知道今夜这冠军侯府不好进,可也不得不来。听了去病的话,张汤那眉皱得就要挤到一堆了。
去病脸色未变,沉稳地看着张汤,“你担心在下用私刑?”
“这姑娘如此咒骂冠军侯,难免冠军侯气大。不过由本官处置,冠军侯尽可放心,定当秉公处置!”
去病不接话,场面冷了下来。
月夜秋风清冷,那火苗子蹿了两蹿,鬼影晃荡,众人缩了缩肩。
“按律制,这姑娘咒骂在下,当如何处置?”去病昂首问道。
“咒骂是实,重者处极刑;轻者,当琼面腕舌!”张汤虽冷言,但隐含一丝惋惜。
去病缄口不语,负手踱步,突转身子,“这女子是在下所爱,她骂在下,乃是与我起了争执,因此怨恨,实乃在下之家务事,廷尉不必担心在下用私刑,我爱之还来不及,怎会用私刑?”
情势一个急转,就是断案无数的张汤也一时楞住,眼直直地望着去病。府门前的火光随风晃动,一时明亮一时混暗,那去病的脸色根本就看不清楚。
张汤脸色一冷,道:“冠军侯此语乃玩笑话?”
“非也。”
“即使是冠军侯所爱,但在大庭广众之下,诅咒大汉君侯,已触犯大汉律令,应按汉律处置,不能按家务事处置,请冠军侯交人吧!”张汤不为所动,仍然铁面坚持。
清幽的街上马蹄“得,得”响,一匹马伴着一辆摇晃的马车从街头缓步而至,马车棚顶翘檐角上挂的迎风灯不停摇晃,仿似要跌落般颤抖不止。
马车里的琴姑、珠儿和兰儿正一声一声地数着静谧夜下一直就很清晰的车轱辘声前行。
珠儿一边哭泣一边回想早间的事。
自己今夜本要陪着姑娘去奏乐间,可姑娘坚决不许。看着姑娘穿了那大红草原稠服,梳了自己从未见过的草原小辫,用玉儿大婚日留下的梳妆盒,描了眉,抹了胭脂,自己那不安的心就直跳。
姑娘白日听了噩耗,本就大病卧床,自己一直哭泣担心,不想,到了傍晚,姑娘硬是起了床,还呆坐院中很久,之后才进屋收拾准备。姑娘走的时候,那眼神也很怪异,还吩咐自己,明日去魏府看看玉儿,这是为何?自己不懂。自己只知道那猛跳的心更是狂跳,在院中就一直不安,哭泣的兰儿更是脚不离身地跟着自己,不知该怎么办。后来,听说姑娘在大堂咒冠军侯,自己更是抱着惶惶不安的兰儿大哭……
“珠儿姐姐,那冠军侯会杀了姑娘……还有我们吗?”兰儿抬着泪花花的脸问道。
“不知道。”珠儿收回了心思,用手揩了揩泪痕,一脸坚毅,毫不犹豫道:“反正,姑娘死,他就是不杀我,我也死!”
“我也跟你去……”兰儿哭泣道。
“那不一定。”琴姑上了车,听着珠儿和兰儿的哭声,一直就在想问题,为何那冠军侯府的人用了“请”字。明明,冠军侯抢走了姑娘,姑娘肯定被辱,自己也罪责难逃,肯定被罚,可侯府来人却躬身作揖,请自己过府去,琴姑想不通,心中一犹豫,冲口就说出了此话。
珠儿抬着泪眼不信地望了望黑黝黝的琴姑脸。
“吁——”马车夫的声气儿一晃过来,马车还未停稳,惨淡的夜灯下,琴姑、珠儿和兰儿就急急忙忙地下了车,三人互相搀扶着,缩着身子跟在已下马的霍连身后,快步走向门前。
看见去病正站在大门口,霍连回话:“禀公子,坊间琴姑,还有服侍石姑娘的珠儿、兰儿都来了。”
看着夜灯下站着的去病,那模模糊糊的魁伟身材在恍恍惚惚的烛火下来回变身,琴姑打了一个冷颤,珠儿却恨恨地看了一眼,兰儿根本不敢看,紧握着珠儿手不放。
“请他们进去。”去病让了道,三人慌忙低着头依序进门。
“这不是坊间琴姑吗,她们来干何事?”
琴姑心中一沉,这不是张大人吗,他来捉拿石岩子?琴姑回了头,望了望同样模糊的张汤,才还犹豫的心现在又恐惧起来,但脚还是急急地碎步向前,继续往里面走。
“这石姑娘病重,我请她们来问问。张大人如没其他事,就请回吧!”去病向张汤下了逐客令,欲转身进府。
“石姑娘病重?她才高声辱骂冠军侯,就已经病了?能否容在下进府看看?”张汤听到病重,就怀疑石姑娘已被辱没,既担心,又不信。
“张大人不信?认为在下用了私刑?”
“不是不信,只是罪犯在府上出事,我等担待不起!”
去病心中挂着子瑜,没心思跟张汤耗着,他根本就不怕张汤执法,就朗声道:“好,你随我进府!”
一贯六亲不认,铁面执法的张汤忖度了一下,就吩咐众人门外等候,他一人跟着去病进府。
听到张汤那一贯冷酷的声音,越往里走,琴姑那心就越慌。这石岩子究竟如何?这冠军侯为何请自己?进到一个庭院中,那错落有致的树木在两旁黑魆魆地静默无语,廊下有几个人影在晃动,眼前,那高大的大屋豁然入目,敞开的大门内,明亮的灯火像那针线般直直地透光到了室外,石岩子在这里?在大屋内?看这步程,这像前院,难道是书房?这冠军侯要审自己?琴姑越来越猜不出究竟来了。
跟着来人,进了大门。室内,多盏烛灯亮着,白煞煞地照着。琴姑抬眼看了看,室内装饰精致,各色罐子、漆器错落有致地摆放着,迎面处,书简一大墙,才看见一副盔甲,琴姑一眼就瞄见那华丽幔帐后的床榻上,有人躺着,一床大花锦缎被子正盖在长长的身上。难道是石岩子?
来人伸了手,琴姑疑惑地走进卧榻之室。看到石岩子闭着眼卧在那花团锦簇的卧榻上,琴姑稳住了那一直忐忑的心,开始真心实意地哭了起来。紧跟进屋的珠儿和兰儿围着姑娘掉眼泪。兰儿拉着姑娘的手,哭喊道:“姑娘,醒醒……醒醒……”喊了又哭,哭了又喊。
两三个服侍的婢女也在室内,都站立着,看着三人哭泣,见公子进屋,就低了头退到一边候着。
门外霍连回道:“公子要的干净衣裙和热水都已备好。”
去病挥挥手,“等会儿。”
琴姑虽哭着,可一直在看这房间,心中很是异样,不懂冠军侯为何将石岩子安置在书房卧榻上,难道,这姑娘今夜露了真容,这冠军侯也被迷住了?
琴姑一眼就看见张汤进屋,慌忙过来施礼,悲切道:“请侯爷和张大人高抬贵手,我家姑娘今日受了刺激,不该咒骂侯爷,姑娘如今这样,请放条生路吧!”说着就一跪不起。
去病示意,琴姑擦了脸上悔恨的泪站了起来,
张汤看里屋榻上姑娘睡着,放了心,冷面冷语道:“这石姑娘犯了事,该怎么处置就会怎么处置,没人能幸免!”
“张大人真要抓捕石姑娘?”去病扬眉道。
“冠军侯,大汉律令,卑贱之人以下犯上就应依律处置!”
“她是在下夫人,夫人犯事,在下这当家人更应被处置!既如此,在下替夫人上你廷尉府服刑!”
琴姑心中一动,抬了不信的眼望着烛火下去病那黑脸,这冠军侯真被迷住了,不追究诅咒之语,还欲娶这石岩子为妻室,不是妾室?琴姑不信。
正哭泣的珠儿、兰儿都蒙了,恍若梦中一般,互相望望,更是不懂。
“她是妻,更不能辱骂自己的夫君!”张汤气极,大声应答道。
张汤正气着,突生疑惑,愁眉道:“那姑娘有面疾,你这朗朗冠军侯会不在意?”不等去病回答,也不顾礼制,张汤急趋步子,走到里屋卧榻旁,去病紧跟而至。只见榻上睡卧之人,美丽娇艳,何来丑容?
去病笑看张汤,“这姑娘故意丑容,就是在等在下!”
想到这姑娘丑容面君一事,张汤那断案心思转了一转:自己对此事可是知道得一清二楚,但在皇帝哪里,断不能让他知道自己知晓此事;又看看去病,此人虽傲慢无礼,但一贯重义守诺,难道真是其妻室,不是妾室?这皇帝最偏爱此人,谁知道皇帝会如何对待此事?如像那匕首一样,自己岂不为难?张汤那眼才跳过一抹惊异,脸色瞬间又回复正常,看看昏睡的姑娘,回头看着去病,沉稳地问道:“她是你妻室?”
“正是!”
张汤又问:“没听说你冠军侯娶妻,你何时娶妻?”那眉眼一个跳动,就不信地问:“那日在坊间,你曾当着陛下说,大漠娶妻,难道就是这乐伎?”
“张大人不在廷尉府就审犯人了?”去病不屑回答,“张大人硬要夫人服刑,在下陪同,不过,必须等夫人病好才行!”
霍祁进屋,禀道:“回公子,药已抓好,隔壁春儿正熬着。”去病挥手,霍祁退下。
张汤又仔细打量了一下去病,这冠军侯是出了名的胆大妄为之人,娶妻匈奴女子,也只有这冠军侯才会干这种事。看他那沉稳的样子,不像是被这石岩子的貌所迷惑之人。既然敢当着皇帝面说大漠娶妻,他肯定娶了匈奴女子为妻室。
张汤又看看榻上的石岩子,这石岩子入坊就一直遮面,丑容拒君,应该在等人,在等冠军侯?真是其妻?他俩为何失散?为何就一直没见面?张汤又转个身子,狐疑地看看屋内婢女手上托着的干净衣裙,看看也同样疑惑的坊间女子,再看了看一直很稳重的去病,思虑良久,一直不说话。
“你倒底想怎样?我此时可没空!”去病不耐烦起来,再下逐客令。
“既是你夫人,在下暂不叨扰了,只是,你那夫人可不简单!等冠军侯他日有空,能否给在下一个交代?陛下过问,也好回禀。”张汤终于做了决断,退了步。
“陛下会问这个?”去病不解,也没在意张汤所说,巴不得张汤快走,就说道:“好,他日定给张大人一个交代!”
张汤前脚一走,去病就令人将热水端进屋,洗了帕子,上前为子瑜试脸,头未回就吩咐道:“留下热水和衣裙,你们都在外面等着。”
听了去病的话,珠儿大骇,一跪到地,哭道:“小女子一直服侍姑娘,请侯爷外出,我给姑娘换衣。”
去病回了头,温言道:“我给子瑜换,你们都去廊下等着。”
“子瑜?”珠儿不解,仍叩头哭泣道,“姑娘是匈奴女子,一直未嫁,请侯爷不要坏了姑娘清誉。”
“你倒是忠心,”去病停了手,回转身体,上下仔细打量着眼前的珠儿,“她名子瑜,是我草原结发之妻,失散四年余,今日才得相见,你明白吗?我是她夫君!”去病看着珠儿,语音很温暖:“你们都出去,我给子瑜擦拭身子换衣。”
“冠军侯年下不是才娶亲吗?怎又在草原娶了姑娘?”珠儿眼中尽是糊涂之意。
“子瑜知道我娶亲?”去病嘴角一抽,话音明显有点紧张,那脸色也有了变化。
“那日,姑娘她们出城放鸢,见陈府送亲,就听街上的人说冠军侯娶妻,当时姑娘也在车上,听得清清楚楚的。此事,兰儿也在场。”珠儿不信去病娶妻姑娘,一脸的不放心,看了看呆立的兰儿,示意兰儿说话。
此时,兰儿正挂着一脸的泪珠子,茫然地呆立着。兰儿也记得冠军侯曾娶妻,她还和玉儿争论过。兰儿懵懂间,觉得姑娘可能就是冠军侯的妻子,因为娶亲当日,兰儿就觉得那冠军侯不高兴,也许他就是那人……兰儿不知该如何说话,一张泪脸呆呆地望着去病。
去病看着珠儿,那眼色已变坦然:“我娶妻子瑜,你们遇着的那日是取妾。”
眼见面前这忠心的小姑娘还在怀疑,去病就问珠儿:“你们姑娘是不是在寻人?”
“不见姑娘寻人。只是……姑娘身子一直就不好,自玉儿嫁人后心情更不好,好像在等什么人。”珠儿迟疑的眼看了看去病,她一点都不相信他就是姑娘心中那人。
“她在等我,但也在恨我!”去病眼中满是自悔,“她有个朋友叫莫措,你们知不知道?”
“是姑娘的妹妹,去年来过,六月就回去了。”珠儿心动了动。
“那你还不相信我?”
珠儿无法对答了,只有无助地望着琴姑,琴姑半信半疑:他住着华丽的侯府,这石岩子却卖身做了倡伎!石岩子所有古怪言行一一迎刃而解:她那石岩子的名字就是指的他?她丑容拒天子,也是在等他?可为何两人一直没相见?为何?想着,琴姑疑惑地点了点头,珠儿只有跟着众人外出。
外间廊下站立良久的荷花将屋内的一切听得一清二楚,见众人一一退出,荷花惊骇下赶紧溜了。
那边,去病已褪去子瑜身上草原华服,擦拭了子瑜火烫身子,换了日常干净衣裙。不想,子瑜刚换了衣裤,被放入被窝中,就一手拉了去病手握在胸前,眉紧皱,口中喃喃大喊:“父王……不要离开我……”然后一手伸向空中,闭着的双眼有泪滴出,低泣道:“母亲……不要……”拉着去病的手力气巨大,指甲深深陷入去病手心。
子瑜那头翻过来舞过去,一头发辫被弄得一团糟,又猛地闭眼转头,哭喊道:“莫措……你在哪里……莫纳……你在哪里……我跟你走……”去病心中一沉,伏在耳边低语:“子瑜,我在这儿,别怕!”子瑜脸似倾听,哭声低了下来:“陈霍……你在哪里……你不要我了……”然后苦痛低泣。去病脸一热,眼中微光闪动,喉头一动,被去病咽回肚中,不停地喊:“子瑜,我要你,我要你!”子瑜脸色渐渐放松,拉着去病手,渐渐睡沉,不再言语。
外面的人听到子瑜胡言,都心急,但没人敢进屋。
小半个时辰后,霍连在外轻声喊道:“公子,药好了。”
“端进来。”
去病将子瑜头垫高后,用勺子舀了一勺汤药,就向子瑜嘴边送,子瑜嘴半闭着,去病就用手轻轻掰开,将药罐了下去,药流了少许,去病就用春儿盘中的湿巾擦了子瑜嘴角。
春儿偷偷看着去病那不慌不忙的身躯,嘘了一口气:幸亏在盘中放了擦脸的湿巾,否则,今日又要被管家骂!一直在熬药的春儿很奇怪,从未见公子服侍他人,这公子为何如此细心地服侍一女子?
子瑜喝了药,已经安静下来,一刻钟后,汗水开始一汪一汪地出。去病又令外面候着的菊儿拿了干布垫了子瑜后背,令她守在榻前,他自己则轻车熟路地擦拭子瑜额头、脖颈和后背的汗水,又吩咐菊儿:“你仔细点,守在这里,出了汗,就一点一点擦拭干净,要干爽帕子,不能伤风!”
见子瑜在退热,去病放下幔帐,就踱出外间坐下,喊了声:“进来吧。”
琴姑等人低着腰身一一进了屋。
婢女端了茶水,去病喝了一大盏,抹抹大嘴,开始问话:“今日,子瑜因何事受了刺激?”一双厉眼看着坊间琴姑、珠儿、兰儿。
“这姑娘来时名木朵,不唤子瑜。”琴姑小心道。
“我说是子瑜就是子瑜!”
房内静了下来。去病看着琴姑,琴姑低首,战战兢兢道:“姑娘草原家乡传来信息,说……姑娘的父兄在上年的汉匈大战中战死,母亲因此跳河自杀。而且……而且……说姑娘父兄是侯爷您所杀。”
去病沉了脸,“还有呢?”
琴姑侧脸想了想,“姑娘的妹妹和弟弟都失踪了,姑娘因此伤心,白日闻听噩耗,姑娘还吐了一口血。”抬眼瞧着去病,见去病脸阴着,就硬着头皮继续说,“今日姑娘滴水未沾,颗米未进,姑娘伤心透顶。”
“那条白犬呢?”
“你说汤圆?在院中!”琴姑还没回答,珠儿已经应声。珠儿听到去病说姑娘是他妻室,虽不信他就是那人,可他知道莫措,珠儿犹豫了。忐忑间,见去病问汤圆,珠儿心中才有了安稳,半信半疑间,就急急地答了话。
“霍祁,你和这位姑娘一起去坊间,把汤圆接过来。”霍祁应声,带着珠儿外出离去。
去病又饮一大盅茶,擦了嘴角,“子瑜何时到的坊?”
琴姑壮胆施礼,“姑娘是前年冬日进的坊,当日姑娘在长安城外大道上卖乐为生,”去病脸抽动了一下,姑姑一眼瞥见,胆颤心惊道,“被我家李琴师遇见,就引荐姑娘到了我们坊间,作了……作了……乐伎。”将姑娘流落长安郊外,自杀一事暂隐去不提。
“卖了身?”去病端着茶,黑着脸,咬牙蹦出三字。
“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坊间规矩,女子进坊必须卖身。只是,侯爷放心,这个卖身不是服侍其他男子,就奏乐卖身。”琴姑现在已经相信这石岩子就是去病之妻,已吓得惶然,赶紧解释。好在去病听到只是奏乐卖身,脸上墨色才隐,琴姑瞥见才大大地舒了一口气。
室内没了声音,去病那脸色青一阵黑一阵的,一直变幻莫测,场面甚是诡秘。
“公子,今日且歇歇吧,此时已是寅时,眼看就天明了,公子还要上朝。既然夫人已在府中,来日方长,以后再慢慢细问不迟。”霍仲见公子脸色甚是冷峻,就打了圆场,加之一晚已过多半,人人俱是一夜未睡,公子马上就要更衣入宫,就斗胆劝了去病一句。
庭院外响起了狗吠声,去病一笑:“亲人来了!”果然,那汤圆急蹿进屋,一纵就扑上了去病身子,长舌一舔,去病左边脸上全是汤圆口水,还不停地摆着尾巴,与去病甚是亲热,在去病周围不停地撒欢。
珠儿一见,瞬息明白了那夜姑娘为何大哭。珠儿心中嘀咕:难道,他真是那人?
去病抱着汤圆,拍拍汤圆大头,苦笑道:“只有你认我,你那主子如此咒我,还不知道认不认我呢。”眼神忧郁了一下,随即恢复如初,问珠儿:“你还怀疑我吗?”
“小女子向侯爷赔礼。不过,也不能怪我,姑娘从不说以前的事。我们不知道姑娘叫子瑜,也确实不知道你和姑娘是怎回事,是什么关系。”
此时,珠儿正细细地打量去病。如是他,那夜,他为何又走了?看今日情形,他认得汤圆,肯定不会离开,难道不是他?可汤圆那动作跟今日如此相似,不是他,会是谁?珠儿摇头,肯定是他,他为何直到今夜姑娘发了咒语,他才现身?那夜,姑娘抱着汤圆痛哭,姑娘认定他走了不会来了,因此痛哭,他去了哪里?
一想到这些,珠儿心中就有了气,咕哝道,“你杀了姑娘的亲人,还娶了亲,姑娘恨绝了你,看你咋办!”此话说得去病那黑脸更是黑沉如锅灰。
一见去病那黑脸,琴姑慌忙道:“小姑娘的话,侯爷不要见怪。不过,姑娘性子很烈,侯爷要有所防备。”
去病沉吟起来。
一屋的人都小心等着,只听室内烛火“啪啪”的报喜声。
“好吧,今夜到此为止,你们都退下歇息吧。”
珠儿不肯离去,坚持要服侍姑娘。琴姑叹气摇头,欲带着一直哭泣的兰儿回坊间。兰儿听说她一人回石院,更是惶然,惊恐的眼望着珠儿,珠儿慌忙跪地请去病留下兰儿。最后,珠儿、兰儿和春儿一起住进了书房外室。
等众人走尽,去病和衣挨着子瑜半躺下。去病心中思绪翻腾,根本就睡不着。子瑜因自己食言,已成彻底的匈奴女子,历经四年的艰苦,今日差点死去!其中,有两年居然在长安卖乐卖身为倡伎!想到此,去病不能原谅他自己。
去病抱回子瑜,就让人点了多盏油灯,室内明晃晃的。四年未见,去病巴不得房间越亮越好,双眸分分秒秒地看着子瑜,何在乎那一碗油灯?去病低头看着仍昏睡的子瑜,房中明亮光影下的子瑜,一脸惨白,那历经千百沧桑的脸也正默默无言地望着去病。去病伸手轻抚子瑜脸颊,眼中全是揪心的痛。
去病一脸痛苦地看着子瑜,恨恨地捶打他自己的胸口,仿佛要把心口捶碎。
去病在屋内狠狠捶胸,那边大管家在左右为难。
今晚之事太过离奇,霍仲根本就没离开。在庭院内左思量右思量,最后来到门外,轻喊道:“公子,老仆有事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