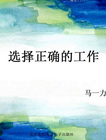雨仍在下。暮色更浓。小女孩仍然呆木地立在那里。在远古时代创造出来的口,是用雨的言词与风的音调讲出第一句话的。亿万年过去了,那被忘记的昔日话语,今天又用雨声来呼唤这个女孩呢。那呼声唤语,越过一切樊篱,在外面徐徐消逝。
有过多少伟大的时代,有过多少伟大的人世!又有多少生灵在世界的多少个时代中欢快地繁衍生息!何等久远,何等辽阔!透过云影和雨声,在这个不驯服的小姑娘的脸上,我们看到了这一切。
她合上那双大眼睛,静静地立着,宛如无限时代的楷模。
生命与爱
托尔斯泰
众所周知,爱的感情之中有一种特有的解决生命所有矛盾的能力。它给人以巨大的幸福,而对这种幸福的向往构成了人的生命本身。然而,那些不懂生命的人叫嚷着:“但是要知道,这种爱是偶尔才发生的,是不能持久的,它的后果常常是更大的苦难。”
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爱情不是理性意识所认为的那样——生命中唯一合乎规律的现象,而不过是一生中常常出现的各种数不清的偶然现象中的一种,人的一生中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人有时会夸耀,有时会迷上科学或艺术,有时热衷于工作、虚荣、收藏,有时会爱着某个人。
对于没有理性的人们来说,爱的情绪不是人类生命的本质,是一种偶然的情绪,一种独立于意志之外的情绪,同人的一生中会产生的其他情绪一样。更有甚者,我们还能常常听到或谈到这样的推论:爱情是某种不正确的破坏生命正常进行的折磨人的情绪。这种议论很像太阳升起来的时候,猫头鹰所产生的眩晕感觉。
尽管如此,在爱的状态中,这些人也感觉到了一种特别的、比起所有别的情绪来都更重要的东西。但是,不理解生命,人们也就不会理解爱情。而对于这些不懂生命的人来说,爱的状态和其他所有情绪一样,充满苦难,充满欺骗。
“去爱,可是去爱谁呢?
暂时爱一下不值得,
而永远爱又不可能……”
这些话准确地表现了人们的模糊不清的认识:爱情之中有着摆脱生命苦难的东西,有某种类似真正幸福的东西。与此同时,人们也承认,对于不理解生命的人来说,爱情也不可能是灵魂得救之方。
既然无人可爱,任何爱情也就都自然流逝。因此只有当有人可以爱的时候,只有当有人可以永远爱着的时候,爱情才成为幸福。而由于没有这个人,那么爱情之中也就没有拯救之方,爱情也是骗局,也是苦难,同所有别的东西一样。这些人只能如此理解爱情,而不会有别的理解。
不懂生命的人认为,生命不是别的,只是动物性存在的人。他们不但自己跟别人学会了这一点,而且也以此教导着他人。
在这些人的眼中,爱情简直不能有我们大家通常赋予这个概念的内涵。它不是给爱的人和被爱的人带来了幸福的好的活动。在认为生命在于动物性的人们的观念中,爱情常常是这样的感情。由于这种感情,一个父亲尽管感到良心的折磨,却仍然会从饥饿的人那里抢来最后一块面包来喂养自己的孩子;由于这种感情,一个母亲会为了自己孩子的幸福,而从别的饥饿的孩子那里夺走他母亲的奶;由于这种感情,爱着一个女人的男人会为这爱情而痛苦,并迫使这个女人也痛苦,或者出于忌妒而毁灭自己和她;由于这种感情,经常发生人们为了爱情而残害妇女;由于这种感情,一个集团为维护自己而损害另一个集团;由于这种感情,人们在所爱的事业上——这个事业只能给周围人带来灾难和痛苦——自己折磨自己;由于这种感情,人们不能忍受对自己祖国的侮辱,而让死尸和伤兵铺满荒野。
不仅如此,对于那些承认生命在于动物性躯体的人来说,爱情活动是如此困难,以致它的表现不只是痛苦的,并且常常是不可能的。不理解生命的人们常说,不应当去讨论爱情,而应当沉入在那种真正的爱情中——你所感觉到的对人们直接喜欢和偏爱的感情。
他们说得没错,不应当去讨论爱情,因为任何对爱情的讨论都是在毁灭爱情。但是问题在于能不讨论爱情的只有那种已经把理智用于对生命理解的人,只有那种抛弃了个人生命幸福的人;而对于那种不理解生命、只为了动物性躯体幸福而生存的人来说,是不能不去讨论爱情的。他们必然要讨论,以便能沉浸于那种被他们称之为爱情的感情。对于他们来说,不讨论、不解决那些不能解决的问题,这种感情就不可能出现。
事实上,人们喜欢自己的小孩、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妻子、自己的祖国远胜于别的任何孩子、妻子、朋友、国家。人们把这种感情称之为爱情。
一般来说,爱意味着希望,渴望行善。我们只能这样理解爱情而不能有别的理解。换句话说,我爱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妻子、自己的祖国,也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妻子、祖国比别的孩子、妻子、祖国更幸福。任何时候没有过,也不可能有这种情况,我爱的只是我的孩子,或者只爱我的妻子,或者只爱我的祖国。任何人都是在同时爱着孩子、妻子、祖国和人们,同时人们出于爱情而希望他所爱的各个对象能获得幸福,其条件是相互联系的。
因而,人为了所爱的生命中的一个所进行的爱的活动,不仅妨碍为其他人而进行的活动,而且常常是有害于其他人。
对祖国的爱,对选中的职业的爱,对所有人的爱,也完全如此。如果一个人为了以后的最大的爱而拒绝眼前最小的爱,那么十分清楚,这个人,尽管他全心地希望,却永远也不能权衡,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了将来的要求而拒绝眼前的要求,因而他也就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总是挑选那些会给他带来愉快的爱的表现,也就是说,他的行动不是为了爱,而只是为了他个人。如果一个人打定主意,为了未来另一个较大的爱,他最好放弃眼前最小的爱,那么他这是在欺骗自己,或者欺骗别人,他是谁都不爱,而只爱他自己。
对未来的爱是不存在的,爱只能是现实的。一个人,如果在现实中没有表现出爱,他就根本没有爱。
那种被不理解生命的人称作爱情的东西,只是对自己个人幸福的某一些条件的偏爱;当不理解生命的人说他爱自己的妻子、或者孩子、或者朋友的时候,他说的只是由于他妻子、孩子、朋友的存在增添了他个人生命的幸福。
这种偏爱同真正爱的关系就像存在同生命的关系,那些不理解生命的人总把存在当做生命。同样,这些人也总把对个人生存的某些条件的偏心叫做爱。
这种感情——对某些存在的偏心,例如,对自己的孩子,甚至对某些职业,再比如对科学、对艺术的偏爱等,我们也都把这些叫做爱,但是这种偏心感情各不相同,无穷无尽,它汇集了人的动物生命所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复杂性,不能称之为爱,因为它们不具备爱的主要特征——即以幸福为目的和后果的活动。
这些偏心的热烈表现只能煽起动物性躯体的热情之火。热烈地偏重一些人而不去重视另一些人,这被人错误地称作爱,其实,它不过是未嫁接的小果树,在它上面有可能嫁接上真正的爱之枝,可以结出爱之果。但是作为未嫁接的小果树,它毕竟不是成熟的果树,它不能结出苹果,或者它只能结出苦果来代替甜果。
偏爱、嗜好同样不是爱,不能给人带来善,只会给人带来更大的恶。正因为如此,世界上发生的那些最大的恶行都是因为这个被充分赞美的爱,对女人的爱,对孩子、对朋友的爱引起的,当然更不必说对科学、对艺术、对祖国的爱了。它们只不过是把动物性生命的某些条件暂时看得比另外一些更重而已。
幸福是一位少女
纪伯伦
我爱过自由。越是看到人们受奴役、受蹂躏,我对自由就爱得越深;越是认识到人们服从的只是些吓唬人的偶像,我对自由的热爱就愈加增长。雕塑那些偶像的是黑暗的年代,是持续的愚昧把它们树立起来,是奴隶的嘴唇把它们磨出了光彩。不过像热爱自由一样,我也爱这些奴隶,并怜悯他们。因为他们是一群盲人,他们看不见自己是同虎狼的血盆大口亲吻,他们并没感到自己是把毒蛇的毒液吸吮。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亲手为自己挖墓掘坟。我爱自由曾胜过一切,因为我觉得自由好像一位孤女,形影相吊,无依无靠,她心力交瘁,形销骨立,以至于变得好似一个透明的幻影,穿过千家万户,又在街头巷尾踯躅,她向行人打招呼,他们却置之不理。
我像所有的人一样,爱过幸福。每天醒来,我同人们一道把幸福寻找,但在他们的路上,我从未把她找到。在人们宫殿周围的沙漠上,我未能看见幸福的脚印;从寺院的窗户外,我也不曾听到里面传出幸福的回音。当我独自一人去寻找幸福时,我听到自己的心灵在耳语:“幸福是一位少女,生活在心的深处,那里是那样深,你只能望而却步。”我剖开自己的心,要把幸福追寻。我在那里看到了她的镜子、她的床、她的衣裙,却没有发现幸福本身。
我爱过人们,非常热爱他们。这些人在我的心目中,可分三种:一种人诅咒人生坏,一种人祝福人生好,还有一种人则对人生深深地思考。我爱第一种人,因为他们日子过得太糟糕;我爱第二种人,因为他们宽容、厚道;我更爱第三种人,因为他们有头脑。
自由与生命
索尔·贝洛
正值八月,在一个充满暖意的下午,一群孩子在十分卖力地捕捉那些色彩斑斓的蝴蝶,我不由自主地想起童年时代发生的一件印象很深的事情。那时我还是个十二岁的少年,住在南卡罗来纳州,常常把野生的活物抓来放到笼子里,而自从发生那件事后,我这种兴致就被抛得无影无踪了。
我家的旁边是一片树林,每当傍晚都有一群美洲画眉鸟来到林间歇息和歌唱。那歌声美妙绝伦,没有一件人间的乐器能奏出那么优美的曲调来。
我下定决心捕获一只小画眉,放到我的笼子里,独享它那婉转的旋律。果然,我成功了。它先是拍打着翅膀,在笼中飞来扑去,十分恐惧。但后来它渐渐平息、安稳下来,承认了这个新家。站在笼子前,聆听我的小歌唱家美妙的演唱,我感到万分高兴,真是欣喜若狂。
鸟笼就挂在我家后院,第二日清晨,我看到小画眉的妈妈口含食物飞到了笼子跟前。它让小画眉把食物一口一口地吞咽下去。当然,画眉妈妈知道这样比我来喂它的孩子要好得多。看来,这是件皆大欢喜的好事情。
又过了一天,我再次去看望我的歌唱家,可这次我没有听到它的歌唱,我发现它无声无息地躺在笼子底层,已经死了。我对此迷惑不解,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自问已经给了它最细心的照料。
那时,正逢著名的鸟类学家阿瑟·威利来探望家父,在我家小住,我把我小可怜儿那可怕的厄运告诉了他,听后,他作了精辟的解释:当一只母美洲画眉发现它的孩子被关进笼子后,就一定要喂小画眉足以致死的毒葡萄,它似乎坚信孩子死了总比活着失去自由好些。”
从那以后,我摔碎笼子,不再捕捉任何活物。因为任何生物都有对自由生活的追求,而这种追求无疑是值得尊敬的。
禽鸟
霍桑
在春天的赏心乐事之中,我们是不能忘记禽鸟的。就连乌鸦也会受人欢迎,因为它们正是更多美丽可爱的羽族的鸟衣信使。白雪还没有融化时,它们便已经前来看望我们了,虽然它们一般喜欢隐居树荫深处,以消暑夏。我常去拜访它们,但见到它们高栖树端的那副如作礼拜的虔敬神情,我又感到自己的拜访来得唐突。它们偶然引颈一鸣,那叫声倒也与夏日午后的岑寂无比相合,其声大而且宏亮,且又响自头顶高处,非但不致破坏周遭的神圣穆肃,反会使那宗教气氛有所增加。然而乌鸦虽然有一副道貌和一身法衣,其实却并无多大信仰;不仅素有拦路抢劫之嫌,甚至不无渎神之讥。
相比之下,在道德方面,鸥鸟的名声倒是更好听些。这些海滨岩穴中的住户与滩头上的客人正是赶趁这个时节飞来我们内陆水面,而且总是那么轩轩飘举,奋其广翼于晴光之上。在禽鸟中,它们是最值得观看的;当其翔驰天际,那浮游止息几乎与周遭景物凝之一处,化为一体。人的想象不愁从容去熟悉它们,它们不会转瞬即逝,你简直可以高升入云,亲去致候,然后万无一失地与它们一道逍遥浮游于汗漫的九霄之上。至于鸭类,它们的去处则是河上幽僻之所,另外也常成群翔集于河水淹没的草原广阔腹地。它们的飞行往往过于疾迅和过于目标明确,因而看起来并无多大兴味,不过它们倒是大有竞技者们的那副死而无悔的拼命精神。现在它们早已远去北方,但入秋以后还会回到我们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