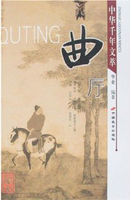一天的劳乏,到了晚上,大家都睡得正浓,我因为想着你不能安睡,窗外的明月又在纱窗上映着逗我,便一个就走到院子里去,只见一片白色,照得梧桐树的叶子在地下来回地飘动。这时候我也不怕朝露里受寒,也不管夜风吹得身上发抖,一直跑出了庙门,一群小雀儿让我吓得一起就向林子里飞,我睁开眼睛一看,原来庙前就是一大片杏树林子。这时候我鼻子里闻着一阵芳香,不像玫瑰,不像白兰,只薰得我好像酒醉一般。慢慢我不觉耽不下来,一条腿软得站都站不住了。晕沉沉的耳边送过来清呖呖的夜莺声,好似唱着歌,在嘲笑我孤单的形影;醉人的花香,轻含着鲜洁的清气,又阵阵地送进我的鼻管。忽隐忽现的月华,在云隙里探出头来从雪白的花瓣里偷看着我,好像笑我为什么不带着爱人来。这恼人的春色,更引起我想你的真挚,逗得我阵阵心酸,不由得就睡在蔓草上,闭着眼轻轻地叫着你的名字(你听见没有?)。我似梦非梦地睡了也不知有多久,心里只是想着你——忽然好像听得你那活泼的笑声,象珠子似的在我耳边滚,“曼,我来,”又觉得你那伟大的手,紧紧握着我的手往嘴边送,又好象你那顽皮的笑脸,偷偷的偎到我的颊边送了一个吻去。这一下我吓得连气都不敢喘,难道你真回来了么?急急地睁眼一看,哪有你半点影子?身旁一无所有,再低头一看,原来才发现,自己的右手不知在什么时候握住了我的左手,身上多了几朵落花,花瓣儿飘在我的颊边好似你在偷吻似的。真可笑!迷梦的幻影竟当了真,自己便不觉无味得很,站起来,只好把花枝儿泄气,用力一拉,花瓣儿纷纷落地,打得我一身;林内的宿鸟以为起了狂风,一声叫就往四处乱飞。一个美丽的宁静的月夜叫我一阵无味的恼怒给破坏了。我心里也再不要看眼前的美景,一边走一边想着。你,为什么不留下你,为什么让你走。
1925年5月1日
神牵梦系
王映霞
(一)
文:
沅江及长沙发的两片都于昨日送来,欣慰之至。
你行后我已有两快函寄闽省府托蒋秘书转交。
不知能于你到闽省前寄到否?今日天气放晴,忙着洗了一天衣服,警报又来了,传说敌机已到长沙,想来你廿四、至迟廿五总可以离长去南昌的,不然又将为你添愁添虑,此时出门真靠不住,所以我总梦想着什么地方都能与你同行来得好些,并非我能防止空袭,与其老远在为你担心,倒不如大家在一起受惊来得痛快,复仇过后心境依然是澄清的,只教你能明白自己的弱点,好好地爱护她,则得着一颗女人的心亦不难也。衡山设委会会计处寄来一张须盖章的收条,我已为你盖章后用挂号信寄去,信一张,便附一阅。愿珍重!
映霞九廿七
(二)
文:
各片均悉,连上之函,谅均收到。前夜得自浦城来电,计今日已可到达福州矣;到闽后各情颇急于想知道,可惜信又慢,而事情又偏不能详电报中。此间已设立湖南省银行驻汉寿办事处,地址是在从前的中央旅馆旧址,招牌已挂,以后汇款,或可直寄此,当较为便利。望舒有来函,附上一阅,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根本人不知谋,而天欲成亦不能也,人到了中年,依然得过且过,没有一上进取之心,专赖他人催促,又何补于事实?奈何奈何?
大小均安,勿念。
映霞九卅日
(三)
文:
六日的快信反而到在七日所寄的以后,邮件之颠倒无常,这正象征了我的命运,在十几年前,我何曾会得遥想到有今日,有今日受着丈夫恶意的欺凌?这的确与怀瑜向我说的“红丝牵错了,误了前因”一样,倘若当初你与别人“结识”了(这两字是照七日来信中所写,你的用字似欠妥当,我是上等人家小姐,似与别人不可比也。你一开口便下流,难怪从前的人的婚姻须门户相当!)
马马虎虎亦会得过半生,而我,又可以做一个很贤惠,很能干的大家庭中的媳妇,让翁姑喜欢,丈夫宠爱的和平空气中以终其身,如今是一切都成过去,所有的希望都只能希冀于来世,自古聪明人的遭遇偏不寻常,我又何能例外?徒靠你现在的每一次来信中都述说着“不愿援用强权”是无益的,你的用不用强权,与需否用强权,这都已在过去的十年你的行为中为你证明,一个己婚的男子在第二次的结婚后,精神肉体可以再重返“故乡”,在那初婚的少女尚且能宽宏大量,能以绝大的牺牲心在万难中忍耐了过去,这才可以说并未“援用强权”,以夺取你的自尊心,但当初我的报复的心,每时每刻我都在牢记着,从未因为暂时的欢娱而衰落过,正与据你所说的你对我的爱一样。现在只教你来信中一提及往事,那即刻就会使我把过去的仇恨一齐复燃起来,你若希望我不再回想你过去的罪恶时,只有你先向我一字不提,引导我向新的生命途中走。大家再重新地来生活下去,至于你的没有爱过旁的女人和对我的爱从未衰落过的那些话,我读了,只会感到你的罪深而刑罚太浅,这如病重而药轻一样的无济于事。能不能使我把你的旧恶尽行忘去是在你,请你记住。近来杂志读得很多,很有些想写文章写自传的冲动,但第一次的尝试,似乎总不敢下手。匆匆复你六日的快信,孩子我都照顾周到,无须你挂心。
映霞十月十八日午后与爱相约
依丝·纪修尔
中央火车站服务台上面的大圆钟指着差六分六点钟,高大的年轻中尉从月台上走来,抬起黝黑的脸,正看时间,他的心砰然跳动得让自己都很吃惊,因为自己已无法控制。再过六分钟,他就要见到一个特别的女人了。他从未见过她,但她在过去的十三个月里,一直在他生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她从未间断的信,一直都与他同在。
他让自己尽量靠近服务台,站在包围服务人员的一圈人外。
布兰福中尉记得战争最紧张时那个特别的晚上,他的飞机被一群敌机包围,他甚至还看到某敌机上驾驶员狞笑的脸。
在他的信中,他曾提到自己时常感到害怕,就在战斗前几天,他收到她的回信:“你当然会害怕……所有勇敢的人都会害怕,大卫王不是也怕过吗?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写诗篇二十三篇了。我希望下次你再怀疑自己时,能听到我的声音为你朗诵:‘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到伤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他记住了,也仿佛听见她的声音,使他重新充满体力和作战的勇气。
现在他就要听到她真正的声音了。差四分六点,他不安地四处张望。
巨大的屋顶下,过往的行人忙碌地穿梭来去,像彩色的线被织进一张灰色的网。一个女孩经过他身边,布兰福中尉盯着她看,她的上衣口袋里有一朵红花,但是朵红色甜豆花,不是他们约好的红玫瑰。此外,这个女孩也太年轻了,大约十八岁而已,而霍莉丝梅内尔却坦白告诉他,她三十岁了。“那又怎样呢?”他回信说,“我三十二岁。”其实他才二十几岁。
他的心思又跳回到那本书。那本书是大众捐献,送往佛罗里达州训练营军中图书馆的书,上帝自几百本书中挑出这本放在他手中,这本书是《人性枷锁》,从头到尾写满了一位女性的摘记,他一向痛恨在书上东写西写的习惯,不过这本书上写的评论很不同。他从不敢相信一个女人能这么体贴,这么透彻地理解一个男人的心,她的名字写在书的封页内:霍莉丝梅内尔。他找到纽约市的电话簿,然后找到她的地址,写信给她,她也回信了。第二天他就随军队启航离开,不过仍继续与她通信。
十三个月来,她一直忠实地回信,而且她不只回信,有时他的信没到,她还是照写,所以他相信两人彼此相爱。
尽管他不断要求她寄照片给他,她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拒绝,那当然令他感觉不太好,不过她解释:“如果你对我的感情是真的、诚实的,我长得如何并不重要。假使我长得漂亮,我会一直以为你因外貌而爱我,那样的爱会让我讨厌。假使我姿色平平(你必须承认这点比较有可能),我会害怕你只是因为寂寞孤单,别无选择才继续跟我通信,不要要求看我的照片,你到纽约来就可看到我,到时你可自己决定。记住,见面之后,我们都可自由选择要不要继续下去……”
还有一分钟六点,他紧张地点起一根烟。
这时布兰福中尉的心脏跳得比他曾驾驶的飞机还高。
一个年轻女子向他走来,身材修长,金发成鬈梳在小巧的耳后,她的蓝眼明亮如花朵,唇和下巴温柔中带着坚定,身穿浅绿套装,像春天乍现。
他开始向她走去,完全忘记去注意她根本没戴红玫瑰。女子看到他,嘴角弯起一抹挑逗的微笑。
“同路吗?阿兵哥?”她低声地说。
他无法自制地再靠近她一步,然后他看到了霍莉丝梅内尔。
她站在女孩后面,少说也四十开外了,灰发隐藏在一顶老旧的帽子下,她不仅丰腴,两根粗脚踝还重重地踩在低跟的鞋里,不过,她绉折的褐外套口袋却戴着一朵红玫瑰。
穿绿套装的女孩迅速走开。
布兰福觉得自己已分裂为二,一来多么希望能跟随那绿衣女孩,但却又深深渴望跟这个女人见面。她的灵魂一直陪伴他、鼓舞他,而现在,她就在眼前。苍白而丰满的脸温柔而敏锐,现在他看出来了,她灰色的眼充满温暖及慈爱的光。
布兰福中尉没有迟疑,他的手指抓着《人性枷锁》老旧的蓝皮书,让她能认出他来。这可能不是爱,而是比爱更珍贵、更稀有的友情,他一直很感激,而且会永远感激。
他挺起宽阔的胸膛,打了招呼,把书拿给女人。虽然他鼓起勇气说话,但内心仍被失望的苦涩所苦恼。
“我是约翰·布兰福中尉,而你……你是梅内尔小姐吧?很高兴见到你,我……我可以请你去吃晚餐吗?”
女人的脸宽容地笑了开来:“孩子,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她回答,“那个穿绿套装的年轻女孩,就是刚刚走过的那位,请我把红玫瑰戴在外套上,她说如果你要我跟你出去,我就告诉你,她在对街的大餐厅等你。她说这是某种测验。我自己也有两个儿子在当兵,所以帮个小忙是应该的。”
只要有爱
聂鲁达
我在许久以前曾受祖国发祥地的召唤顺着朗科湖往内地走,在那里找到了既受大自然攻击又受大自然爱护的诗歌的天生摇篮。
高高的柏树密密成林,空气飘逸着密林的芳香,一切都有响声,又都寂静无声。隐匿的鸟儿在低低交谈,果实和树枝落下时擦响树叶,在神秘而又庄严的瞬间一切都停止了,大森林里的一切似乎都在期待着什么。那时候有一条河流就要诞生了。我不知道这条河叫什么,但是它最初涌出的纯洁的、暗色的水流几乎令人察觉不出,涓细而且悄然无声,正在枯死的大树干和巨石之间寻觅出路。
枯藤老叶堆满了它的源头,过去的一切都要阻挡它的去路,却只能使它的道路溢满芳香。新生的河流把烂根朽叶一路冲刷,满载着新鲜的养分在自己行进的路上散发。
在我看来,诗歌的产生与此大同小异。它来自目力所不及的高处,它的源头神秘而又模糊,荒凉而又芳香,像河流那样把流入的小溪纳入自己的怀抱,在群山中间寻觅出路,在草原上发出悦耳的歌声。
它使干枯的田野受到滋润,为挨饿的人解决粮食。它在谷穗里寻路前进。赶路的人靠它解渴;当人们战斗或休息的时候,它就来歌唱。
它把人们联结起来,而且在他们中建立起村庄。它带着繁衍生命的根穿过山谷。
歌唱和繁殖就是诗。
它从地下喷薄而出,不断壮大,热情洋溢。它以不断增长的运动产生出能量,去磨粉、锯木,给城市以光明。黎明时岸边彩旗飞扬,总要在会唱歌的河边欢庆节日。
我曾在佛罗伦萨一家工厂参观过,并当场给一些工人朗诵我的诗。朗诵时我极其羞怯,这是任何一个来自年轻大陆的人在仍然活在那里的神圣幽灵近旁说话时都会有的心情。随后,该厂工人送我一件纪念品,那是一本彼特拉克诗集,1484版的,我会一直珍藏。
诗已随河水流过,在那家工厂里歌唱过,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伴随着工人们。我心目中的那位永远穿着修士罩袍的彼特拉克,是那些纯朴的意大利人中的一员,而我满怀敬意捧在手里、对我具有一种新的意义的那本书,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只是一件绝妙工具。
我知道前来参加这个庆祝会的有我的许多同胞,还有一些别国的男女知名人士,他们绝不是来祝贺我个人的,而是来赞扬诗人们的责任和诗的普遍发展。
这类聚会使我非常激动,也非常自豪,我感到我的诗还是有一定社会价值的。确保全体人类相互认识和了解,是人道主义者的首要责任和知识界的基本任务。只要有爱就值得去战斗和歌唱;就值得活在世上。
我很清楚在我们这个被大海和茫茫雪山隔绝的国度里,你们不是在为我,而是在为人类的胜利而举行庆祝。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假如说这些海拔几百米、几千米的高山和波澜起伏、神秘莫测的太平洋曾经想把我们祖国的心声摒弃在全世界之外,曾经企图阻止我们的祖国向全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曾经反对各国人民的斗争和世界文化的统一,现在这些高山被征服了,大洋也被战胜了。
在我们这个地处偏远的国家里,我的人民和我的诗歌为增进交往和友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战斗。
这所大学履行其学术职责,接待我们大家,从而确立了人类社会的胜利和智利这颗星辰的荣耀。
我们不曾孤单,来自美洲热带地区的鲁文·达里奥支援我们来了。他大概是在一个跟今天一样的天空澄碧、白雪皑皑的冬日来到瓦尔帕莱索的,来重建西班牙语的诗歌。
今天,我把我最诚挚的敬意和最深沉的思念奉献给他那星星般的壮丽。
昨夜,我收到了劳拉·罗迪格等人送给我的礼物。我十分激动地把 劳拉·罗迪格带给我的礼物打开。这是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十四行诗》的手稿,是用铅笔写的,而且通篇是修改的字迹。这份手稿写于1914年,但依然可以领略到她那笔力雄健的书法特色。
在我看来这些十四行诗意境有如永恒雪山一样高远,而且具有克维多那样的潜在的震撼力。
此刻,我把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和鲁文·达里奥都当作智利诗人来怀念,在我年满五十周岁之际,我非常想对他们表达我内心的敬意与感激。
真的,我对他们充满了敬意,是对所有在我之前用各种文字从事笔耕的人。他们的名字举不胜举,他们有如繁星布满整个天空。
远方的女子
巴勃罗·聂鲁达
远方的女子,这女子刚好装满我的手。她皮肤白皙,金发,我会用手捧起她,如同捧起一篮木兰花。
这女子刚好装满我的眼睛。我的目光拥抱她,我的目光拥抱她的时候就什么都看不见。
这女子刚好装满我的欲望。在我的生命的烈火前面,她赤裸着身体,而我的欲望把她像活炭一样燃烧。
可是,远方的女子呀,我的双手、我的眼睛和我的欲望的爱抚,都是留给你的,因为只有你,远方的女子,只有你刚好装满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