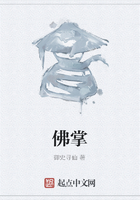她会意,轻脚下床,去到外间,一脸煞白。“我需要你帮个忙,小师娘现在西边耳房内,水我已经打好了,你给她擦洗一遍,替她换上一身她平日里喜欢穿的干净衣裳。”锦瑟顿时双泪坠落,拿手捂住嘴,点点头。江楚寒哑着声音,“身子还撑得住吗?会怕吗?”继而唇角一动,冒出来个类似于笑的表情,“好,手脚快点。”自己抗着一座结冰的、散发着童尿腥臊的背,到床头坐下。被窝中的小人儿一手抓着木头剑,怀里搂着个旧偶人,眼睛依旧红肿。江楚寒感到了一阵胸肋的急缩,直戳肺腑。眼底这张稚气的脸,分明拓着师父:上挑的眉、薄嘴唇、已具雏形的直挺挺的瘦鼻子——如同一场错位,师父忽变得这般幼小、不经世,需要他保护一样坐守在旁。依稀却又如坐在师父当年的座位上,所守的,是幼年的自己。爬树时折下来,摔掉了半颗牙,发高烧,嘴上逞能着不用陪,夜里睡不实,老偷偷地张眼窥。每次将眼睛开出条缝,师父都在,冲他笑,“你个臭小子,再不睡我可真揪你起来练功啊!”练功的辰光是真狠,高了、低了、动作不对了,立刻连踢带打,可到了吃饭时就对他笑,“臭小子,你可真是块好料子,我从没见过比你还聪明的孩子!多吃点!瞧你这长手大脚的,长大个子!”教他写字,眉头皱起来笑,“偏你就跟人不一样!得了,左手就左手吧,这么着执笔,诶,对了。”蘸饱墨,暖暖的大手包住他的手,一笔一画地“上、大、人”。集市的玩具摊子前,垂下手罩在他头顶,揉一揉,“哪个爷们儿家像你这么里唆的,又不是挑婆娘!”扔过一串钱,这些都要了。他向来没搞懂过师父为什么挑中他,从那么多的流浪儿里,不嫌弃他又臭又脏,脏得伤口生蛆的身体、抿死了嘴一个字也不吐的阴郁,于土墙根抱起他,给他治伤,带他吃饭、洗澡,逗他讲话,认真听他讲话,爱他,教导他,给他足够暖和的被子、体面的衣裳、爱吃的东西、自尊、一脸笑,孩子该有的笑。而他晓得这有多难:是在暗光中眯缝着眼,修补一尊早摔得烂碎的土陶罐,费神地弥缝、画彩、上釉,往里面填东西,玛瑙子、珍珠,哪怕水,哪怕一颗心——多沉重,也是颗像模像样的心。
黑寒雪天里的一盏温灯下,他坐着,盯着墨儿,迷失在时间的雾翳中。身上的雪一消融,又空又冷,仿佛一件陶器失却它的匠人、一部完书失却作者。江楚寒静默地承受着搁在他身上、曾一刀一泥塑造他的那双手撤走的温度,甚至不是体体面面地轻盈抬起,如一双充满技巧、理应受到敬重的手一样,而是叫把刀给嘭地生剁掉了。
天明前,后院,浓烈的烟雾与烤肉的焦臭味中,江楚寒独自一人,送别师父师娘。纷扬的雪,他跪着磕头,一个一个又一个。头发湿了,眸子是干的,手齐着手腕摁在冰雪里,一脸麻木不仁,低低念诵着单只有他自个儿能听见的话。
傍晚前后,正准备着过年的忠伯、陈小小祖孙俩出乎意料地迎来了少爷,还拖着位从未听说过的奶奶和一位小爷。墨儿一路消沉,马车上就抱膝埋脸,死抓着木头剑不放,与平日屁叨起来没完的活泼劲大相径庭。倒是江楚寒话多得吓人,一早上都没停过,起床吃饭直到上车,打从去年养的一只小鸡你还记不记得讲起,一句一句,告诉墨儿,没人能从死亡带回人来,大哥也不行,死了就是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说话、不能吃东西你爹娘死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就像那天咱们看县太爷出大殡一样,送走了,就回不来了。但他们不疼、不冷,一点也不,他们高高兴兴的,很快乐。不,不是你的错,好孩子,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你是这世上最乖的孩子,所以你也不能生你爹娘的气,他们绝不是抛下墨儿不管。但有些事情由不得人,一旦发生了,就没办法更改,你爹娘虽然不能再亲你、抱你,可他们没离开你,他们会一直爱你,在天上看着你一天天长大。你心里有什么话,都悄悄地说与他们听,能,他们能听见的,好墨儿真乖,什么?哦,不会,大哥绝不会离开墨儿的,绝不会墨儿问几个字,哭一阵,锦瑟也缩在角落里哭。唯独江楚寒,半滴泪也不掉,一手搂着墨儿,一手搂着只骨灰瓮。
墨儿累了一整天,晚上又哭过一场,蔫惨惨地再不惦记守岁放炮仗,早早就睡下。睡熟后,江楚寒才悄然起身,自将锦瑟带去上房。丫鬟陈小小留下来看顾,听从吩咐,不敢离开眠床半步。
锦瑟头回来江楚寒这边的宅子,上房并不曾隔断,而且一应玩器全无,雪洞一般。除了桌椅茶具必需之物,只在角落里设有一张大得没谱的拔步床,后檐下一张楠木炕。炕沿坐下,哈了哈手,“到底发生了什么?”
江楚寒在她对面长桌边的一张椅上坐着,嘴唇干得起了燎泡,一脸脏。“江湖上,最大的两个帮派就是龙会与丐帮,几十年前他们就结下了仇,近年来又因为抢地盘、运私货之流的事情冲突不断。师父早些年替龙会刺杀了丐帮帮主贺冲天,本来已经完事了,却不知谁走漏了风声,让丐帮的四大长老晓得了是师父干的,找上门来,设陷阱暗算师父。可没料到,他们四个人加起来都不是师父的对手,全送了命。虽然师父自己也因此成了个废人,可说起来,毕竟丐帮的五个首脑人物全死在他手上。我当时小,很害怕,一直带着师父不停地搬家,只敢在小地方住,怕丐帮还要上门寻仇。这么些年过去了,十四年了,出了多少人和事,所以我总想,也许他们早忘了那个美阎罗,或以为他死了,这件事,就能这么过去了。”说着说着搓起手来,笑,极骇人的笑,“锦瑟,都是我的错。你晓得吗?我早知道要出事了,可我一点都没往这上头想,头几天还有群乞丐在咱们门口讨东西,我都没想到。我早该带师父师娘搬走了,为什么拖到这会子?还有昨儿,昨儿我要是坚持让师父师娘与咱们同去,也就没事了,哪怕我能早一步进门,我、我怎么就跟瞎了眼似的,总以为该死的是我?可,该死的明明就是我。这一点道理都没有,完全没道理,锦瑟,这不对,真的是该我去死的。”
锦瑟泪流满面,急步上前将他搂住,“不关你的事,关你什么事,小楚,不怪你。”江楚寒把头顶在女人突出的小腹上,缄口不语。须臾再抬脸,死气沉沉地眨一下眼皮,“锦瑟,我对你不住。答应你的事情,我做不到了。过了这段,过了年,等墨儿好些,我就去找龙会,开香堂入会。我要替师父师娘报仇。”
“你,你——”
“就是说,我一辈子,再不可能从这圈子里拔脚了。”锦瑟短暂地失语一刻,腹部出现下坠的痛感。末后,硬生生一笑,“我晓得你要为师父他们报仇,但,为什么非加入龙会不可呢?”江楚寒也笑,“你怎么倒笨起来了?虽说我没和丐帮的人打过照面,可既然他们能查出师父的行踪,没准也知道我这号人。就算我能秘密地刺杀掉他们帮主,他们猜也能猜出来是谁干的。过了十四年,他们都不肯放过师父,今儿能放过我?我再傻,也不至于一个人去和整个丐帮为敌。唯一的法子就是投靠丐帮的敌人,在龙会往上爬。我要有自己的兄弟和堂口,借帮会的力量来办事。不管丐帮究竟知不知道我是美阎罗的徒弟,反正我对他们做出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把这笔账算在我一个人头上,至少也得让他们有所顾忌。而且就算事情真出了岔子,你们的后半生也能有人照管。”
“你、你要,你也要去杀丐帮的帮主?”“师父身上的伤是丐帮的铁头棍打出来的,小师娘也是。这棍子,在他们帮主贺健翔手里,就是师父所杀的贺冲天的儿子。况且昨儿晚上来的还不止他一个,总有十一二人,我会把他们一个个都揪出来。”
“小楚,我不想,我、我不想你去报仇。我很怕,我忘不了昨儿小师娘的样子,万一你也你才说他们有十好几个人,丐帮又这么厉害,我,我求求你了,你别去,好不好?”
“你放心,我有分寸,不会乱来的。你昨儿没见着师父,那帮人,把他的头割下来带走了。我本想、本想连夜就追上去跟他们拼命,好歹也为师父留副全尸。可我想了又想,就算我不要命,还有墨儿,还有你,还有咱们的孩儿。”默然过后,低声接续,“我江楚寒这条烂命现下可值钱了,我得长命百岁地活着,好好照顾你们。只是我做徒弟的,居然袖手旁观由他们把师父的这会子,还不知他们怎样我连这个都能忍下,自不会急在一时。我会一步步慢慢来的,哪怕三年、五年、十年,但一个也不会放过。昨儿踏进过咱们家门口的人,谁都甭想跑。”
语调森寒,似一线由半掩门后透出来的阴光。锦瑟直觉到,这扇门不能开,绝不能。故尔才蛮横地,两手一起扳起他的下颌,“小楚,你别去,我不准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