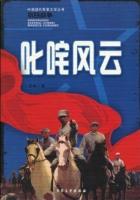民国36年(1947年)。
1月。
清晨的阳光打在王克飞脸上,他不情愿地睁开眼睛。今天的光线好像有些异样,他边想边打了个哈欠坐起来,这才发现窗外正在下雪,白茫茫的鹅毛大雪从窗前飘过。
他兴奋地坐了起来。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啊!
那个炎热的夏天已经很遥远了,好像是上一辈子的事。
今天是几月几号了?自从来到这里后,时间已不再有意义,不再有见面、等待、离别的切分。他已经习惯了长时间的独处,自己和自己交谈、辩论、争吵,又妥协。他甚至开始有点喜欢在这里的日子了。
这几天,王克飞在思考一个问题:他这一辈子到底错过了什么?他错过了战场上一个战友的遗言,错过了萧梦的一次流产,错过了一次发财的机会……去年夏天,他错过了和一个女孩温柔地道别……人生之河无法倒流。
最近,他在她的笔记本里读到了一段话,是她从《呼啸山庄》里翻译的句子。
如果你仍然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那无论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对我而言,都是有意义的;如果你已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那无论这个世界多么美好,我的心,也像无处可去的孤魂野鬼。
而你已经不在了……
他坐在床上,愣愣地瞪着眼前的墙壁。他的记忆里好像有一件事和下雪有关,可他又不太记得清了。
“508号!有人来看你了!”护工突然站在门口喊了一声。
谁会来看自己呢?王克飞没有转过身,内心有些烦躁,他讨厌被人打断思绪。
这时,他听到了轻盈的高跟鞋落地的声音。
一个略带笑意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我回来了。”
他吃惊地说不出话。多像她的声音啊!可是……不,不可能!他的肩膀僵硬着,一动不动。他真怕这只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美梦,一转身,梦便醒了。
访客又往前走了两步,娇滴滴地对着他的后背说道:“怎么了,王探长?您不想看见我吗?”
王克飞这才慢慢转过身。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逆光的剪影:窈窕的身形,披肩的卷发,右手上挽着一件大衣。
他惊讶得不知说什么好了。难道真的是自己错了吗?难道自己疯了吗?一切都是妄想吗?这甜蜜是真实的吗?他开始觉得眩晕。
“你还活着。”他嘀咕了一句。
她咯咯咯地笑了:“我当然还活着。”
黄君梅在他身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笑道:“您不再认为是我杀了陈海默吗?”
王克飞摇摇头。他注视着她,依然不相信这一刻是真实的。
“我怎么会在乎什么凤冠啊,王探长。那个夏天,我只是太爱他了,并以为他也一样爱着我。是他为我出的主意,也是他提出要去铁轨边为我取回凤冠。可8月2号那天晚上,他回来后告诉我,他到达铁轨边时火车已经撞人了。他猜测陈海默手上并没有凤冠,被逼得走投无路才卧轨自杀的。我确实深深内疚过,但谁会想到……”
“你离开的那天晚上呢?到底发生了什么?”王克飞愣愣地问。
“我带了一把父亲藏在书房地板里的手枪,里面总是上满子弹……他们看到枪,拿我没有办法。我带了行李,逃出了医院,最终赶在‘梅吉斯’号发船前到了码头。”
“可你怎么会想到带枪?”王可飞皱着眉头问。
“其实啊,在那晚以前,我已经预感到可能会发生的事。”她苦笑了一下,说道,“还记得那封勒索信吗?有一点您猜对了,为了提前拿到凤冠,我在熊正林的怂恿下向福根提出代笔写信。可我怕海默认出我的字迹,索性让熊正林写好信后寄给她。之后的一个下午,我发现那封信躺在陈海默的化妆桌上。我看到它的那一秒,直觉感到哪儿不对劲,却又说不出来。直到某一天我自己写信时,我才终于想明白了--那封信没有折痕!一封寄过来的信怎么可能没有折痕?所以,这封信只能是陈海默写给她自己的。”
原来如此啊!谁会想到去比对信和收信人的笔迹呢?哪怕再给自己一百次机会,王克飞也不会拿陈海默的笔迹去和那封信比对。
黄君梅走到窗边,手指在窗玻璃的雾气上随意涂抹着,说道:“这个发现一度让我无比困惑。一定是哪儿出了错,可我却想不明白错在哪儿。有一天,当我们经过一张选美海报时,我留意到他的目光首先是落在陈海默身上的。他看她的眼神……怎么说呢?他从来没有这么看过我。但我依然不敢想、也不愿想究竟发生了什么,只因为那个念头太疯狂。离家的那个晚上,我依然抱着一线希望: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胡思乱想。所以,我才上了熊正林的车。可当我发现他没带行李,而是把车开回医院时,我彻底绝望了。”
王克飞看着黄君梅的背影。她的声音听起来是那么平静,只有瘦弱的肩膀微微颤抖。
“直到在隔离病房里见到了活着的陈海默,回想起熊正林指导我做的一切,我才明白了他们想要什么。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把我打造成完美的躯壳,以便有一天让她钻进我的身体。无论多夸张的念头,也可能是真的,永远别低估人心的疯狂……可我为他付出的一切,丝毫没有让他犹豫和心软吗?他从来都只把我当作一件定制的衣服吗?她比我好在哪儿呢?爱情真让人不解啊!”
“可是……”王克飞感觉自己的思维有些迟钝。问道,“在你走后的第二天,熊正林火化的那具尸体是谁的?”
黄君梅沉默不语。
过了一会儿,她才吁了一口气,回答:“我真不愿意回忆起那个晚上。在我离开病房时,海默已经变得歇斯底里。我一旦逃走,她的出口就被堵上了,她被困在了两个身份中间。她无法回到过去,成为陈海默,也没有出口可以成为另一个人。她曾经是多么心高气傲,又志向远大。我无法想象,成为一个没有身份的影子,对她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黄君梅眉心微蹙地摇了摇头:“但我也并不知道,在我离开后,发生了什么……”
王克飞低下头,坐直了背,轻轻吐出一口气。有一些答案,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了。它或许将永远深埋在熊正林一个人的心底,伴随他度过余生的每一天。
黄君梅对着窗外的景色,自言自语道:“今年的第一场雪可真大呵。”
坐在床沿上的王克飞也抬起头,把目光投向明晃晃的窗外。洁白大雪漫天飞舞,纷纷扬扬,以轻柔无声的力量覆盖大地,似乎想要掩盖世间的一切痛苦和丑陋。
黄君梅转过身,看着王克飞,说:“谢谢您为我的‘死’难过。他们都告诉我了,您为了坚持他们是凶手,才被关在这里。”
她走近王克飞身边,缓缓摊开掌心,里面是一根细小的银色的别针。
“我依然记得您跪下来为我戴别针的晚上呢,”她把别针放在他手心中,带着几分讨好和俏皮,眯起眼睛说,“我知道您一定会保护我的。”
王克飞仰起头,两人的目光接触,黄君梅的面颊上泛起了红晕。
他觉得她比夏天更加美丽成熟了。
“王探长,我带您离开这里吧。”
王克飞站了起来。黄君梅把手伸入了他的臂弯:“让我们一起向世人证明我们无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