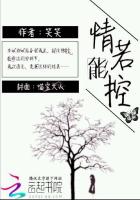回家的路上,我独自走着。
从东南走向西北,五六分钟光景,就快到马路南侧了。圩场,就在我脚下西北百来米处。望着尘土飞扬的马路,望着马路两侧的房屋,望着自东向西或是自西向东的车子,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也就是在这时候,只觉得后颈一痛,像是给什么东西猛捶了一下!回头一看,只见袁雄义咧着嘴,狞笑着跑开了;那只右拳,依然是紧握着的!“唉,这世上居然有这样不要脸的人,竟然从背后打黑拳——”我这样想着,脚下就慢了半拍。也就是利用我这一楞之间,袁雄义一矮身,从我左侧偷逃走了。
向西北方向仓皇逃窜的,就是这暗算我的打黑拳的家伙。
左脚想向西北方向追出一步,右脚却纹丝不动:撵他?就算撵上了,又有什么意思呢?打他一拳出一口气吗?像他这样的人,半点规矩都不懂,值得我这样做吗?算了吧,打这种人,只会弄脏我的手!一个连正面放马过来都做不到的人,实在没必要跟他一般见识。俗话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又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就放他一马吧?这种人——“哦,时间也不早了,该做点什么呢?”这样想着,梁晓刚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气来。的确,在客厅里,他已经坐了好一阵子。
坐在竹椅上,望着虚掩着的木门,梁晓刚一时也没站起身来:看来,今天真的不走运啊!没来由的跟同学打了一架,回到家后又吃不上饭,这真有点屋漏偏遭连夜雨了。哦,如果就像我同桌所说的,忍一点退一步,或许就不会——“吱——”的一声,虚掩着的大门被推开了。
走到客厅里来的,是袁雄义的父亲!
梁晓刚从竹椅上起身,静静地看着这不速之客。
静静地盯了梁晓刚几眼后,袁雄义的父亲发现对方没有让座的意思,就先开口了:“吃过饭了?”
“嗯——”梁晓刚这样回答。
“就你一个人在家?”袁父接着问道。
“是啊,在家里坐一下。”
大概是觉得这两句寒暄也差不多了,袁父板着脸,脸上像是刚落过一层寒霜,只听她这样说道:“今天上午,你打了我袁雄义——”
梁晓刚心里暗自发笑,于是这样说道:“我,我怎么敢打他?!”
袁父皱了皱眉头:“你们,你们打架了?”
“是他,是他先动手的!”梁晓刚这样回答。
“他,他先动手?你,你打伤他了——”
梁晓刚心头一怔:打伤他了?怎么可能呢?这家伙,就会恶人先告状!背后打黑拳也就罢了,回到家还要再咬我一口,要他老爹帮他出头。这,这未免太过分了吧?而这位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子,到我家来,连门都不敲一声!这样想着,梁晓刚也来了气,冷冷的说道:“他,是他先动手的!”
袁父皱了皱眉头,缓缓说道:“谁先动手,我先不管;现在,我是以伤论——”
以伤论?这三个字就像一声惊雷,霎时在梁晓刚脑里炸开了:“以伤论”?照这样说,我还真的打伤了袁雄义?!是啊,要不然,怎么会引来这位“不速之客”呢?或许,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前几天,我跟一位同学你追我赶的,还拿着几小截黄麻杆砸来砸去的,结果一不小心,那位同学的左眼角被我砸中了。好几天过去了,那位同学的眼角,还留着一个水泡大小的痕迹。不过,跟袁雄义打架这件事相比,到底是两码事!于是,梁晓刚并不松口,只是淡淡地说:“我,我怎么可能打伤他呢?”
袁父狠狠的瞪了他一眼,紧接着,咬了咬上下两排牙齿。
寂静,客厅里,凝滞的空气中,近乎窒息的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