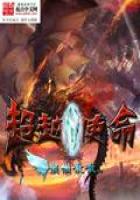石燕对这次聚会场景的想象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屋子里,一群人正弓腰驼背地造着土炸弹;另一种就是在一个豪华的大厅里,很多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在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到了E市郑教授家,她发现真实场景跟她想象的不一样,既不是阴暗潮湿的屋子,也不是豪华的大厅,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房子,不在E大里面,是郑教授自己的私房,如果不是有很多人在那里聚会,可能会有点阴森的感觉,不过老房子都是这样的。
她听卓越说过,郑教授是他在K大时的导师,挺有名气的,后来因为受排挤,调到了E大。卓越本来也想进E大的,但没进成,再加上要照顾他妈妈,就回到D市,进了C省师院,这样就离E市比较近,方便他跟导师来往。虽然师院名气不大,但卓越也没准备在那里干一辈子,所以学校好坏还没离导师远近重要。
她不太明白为什么卓越已经毕业了,还跟导师保持这么密切的联系,她想可能研究生就是这样的吧,或者名校的学生就是这样的吧,人离校了,心没离校,跟导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是跟名校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一般来说,导师都是留在名校的。不像他们破校的本科生,一毕业就像刑满释放了一样,恨不得跑八丈远,才不想跟母校扯上什么关系呢。被人问起来,都要支支吾吾,不说“C省师院”,而说“师大”,让别人误以为是“C师大”。
与会者大多数是男的,只有几个女的,看上去都不年轻了,只有一个女孩年轻一点,也比她大,可能至少有二十五岁左右,卓越介绍说那女孩姓朱,叫朱琳,是他的师妹。
卓越的表现还挺令她满意的,因为他把她介绍给这个,介绍给那个,而且都是说:“这是我夫人石燕——”让她听着很舒服。
但她很快就有了自惭形秽的感觉,因为那些人全都是名校毕业的,最低的都是C师大的,而且都是教授、研究生什么的。幸好她事先就跟卓越打过招呼,叫他别提她是哪里毕业的,所以卓越介绍的时候没提,那些人也没问,不知道是对她不感兴趣,还是早就听卓越说过了。
她这人就是有这么一个毛病,一旦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就只想躲避,她既不能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比名校生差,也不能闭着眼睛说自己绝对不比名校生差,进大学之前你还可以说大家都一样,只不过你运气好考进了名校。但四年过去了,名校生肯定学到了更多的东西,因为他们的老师更好,学校设备更好,不然谁还会去名校?
有了这种自愧不如的心情,她就死也不肯参加他们的活动了,等到他们开会的时候,她就坚决不去,卓越没办法,只好给她找了个房间,让她自己在那里玩。
那是郑教授的一个小书房,里面除了书,就没什么别的东西。卓越指着桌上的电话说:“你想看书就看书,要是觉得没事干,就跟你那些亲朋好友打电话玩,公费的——”
这个让她挺感兴趣的,平时给家里打个电话都要跑学校外头的电话服务点去打,因为学校的电话都不能打长途。她问:“真的不要钱?”
“不是不要钱,是不要你的钱,只要公家的钱。你自己玩吧,我开会去了——”
等他走了,她就真的开始打电话,但一时想不起打给谁好了。她父母家里没电话,平时都是等到父母上班的时候打到单位去的。她想给黄海打个电话,给他说说书的事。自从他那次从她家走后,就没再跟她联系过,她也因为把书都给了姚小萍,而姚小萍说会付钱给黄海的,她也就没费心思去跟他联系。潜意识里,她觉得自己不该再跟黄海有联系,不知道是怕卓越知道了不高兴,还是觉得那样做有脚踏两只船的嫌疑。
以前都是黄海把电话打到她寝室来的,用的是他朋友单位的电话,所以她从来没问过他的电话号码,他也没说过。
最后她决定给姚小萍打电话,因为姚住在集体宿舍里,是她唯一能找到的人。她拨通了电话,让门房去叫姚小萍。
不一会儿,姚小萍来接电话了:“怎么?又跟卓越吵架了?”
“没有啊,我跟他到E市来玩,现在他开会去了,我没事干,给你打电话玩——”
姚小萍很郑重其事地问:“你是怎么搞到生育指标的?”
她不懂:“什么生——育指标?”
“就是生孩子的指标——”
“生孩子的指标?我不知道啊。”
“你没拿到生育指标?那你怎么生孩子?你没到学校去要指标?”
她还没把怀孕的事告诉任何人,想等到在C市办了婚礼再说,除了家里人,外人当中就姚小萍一个人知道,她一直掩藏得挺好的,因为她只在吃过饭后想吐,而她一日三餐都是在家吃,所以单位上还没人知道。她不解地问:“生孩子还要到学校去要指标?到哪里去要?”
“应该是学校计生办吧。”
“我跟卓越都——从来没生过,难道我们——生一个都不行?”
“生一个当然没问题,但是学校有指标限制的,每个单位一年能生多少都是有规定的,所以各单位都会制定一些政策,从年龄上婚龄上限制一下,不然的话,由着你们乱生,那还不该单位吃罚款?”
她吓坏了:“如果我拿不到指标,那怎么办?”
“那就打掉,还能怎么办?”
“那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师院是什么规定?”
“我也搞不清楚,不过我知道我弟媳单位的规定是这样的:女方二十五岁以上结婚的,一结婚就有指标,二十五岁以下的要结婚三年才有指标,他们两口子商量结婚时间的时候,我听他们说过,那时我弟媳二十四岁,他们想干脆等一年再结婚,那就马上有指标——”
她更慌了:“啊?二十五岁以下的要结婚三年才能生孩子?那我——怎么办?”
姚小萍安慰她说:“我说的是我弟媳单位的政策,谁知道师院是什么政策?我生孩子的时候,我们单位就没这些政策。再说你们家卓越这么神通广大,弄个指标还不容易?既然他同意你生,那肯定是有办法了——”
她挂了电话,就满屋子找卓越,最后在一间大屋子里找到了他,但他坐得很靠里面,脸又不是朝着她这边的,她也不敢喊,只好跑回书房写了个小字条,让门边的那个人传到卓越那里去。那些人都很配合,一个传一个,像击鼓传花一样。
花传到了卓越旁边那个人手里,而卓越还浑然不觉,正在聚精会神地听发言人说话,他身边那个人碰了碰他,把字条给了他。他看了字条,朝她这边望过来,看见了她,顿时脸红了,表情很尴尬,使她想起读书时候的事,班上那些同学在城里混了几年,从穿着打扮到言谈举止,都有点脱离土气了,但他们的乡下亲戚仍然是土得那么正宗,又不懂事,最爱上课时跑到教室来找人,把那些被找的人窘得满脸通红。
她发现自己做了一回乡下亲戚,有点后悔,但在心里给自己鼓劲说:我这不是有要紧事吗?如果没要紧事,我会跑来找你吗?
卓越走出来,压低声音问:“没看见我在开会吗?什么事这么急?等我把会开完不行吗?”
她嘀咕道说:“不急我会跑来找你?”她把他带到刚才打电话的那屋,小声问:“我们有没有生育指标?”
他摸不着头脑地说:“什么生育指标?”
“师院教职工生孩子是需要生育指标的,你知道不知道?”
“我没听说过,你听谁说的?”
“听姚小萍说的。”
“她又没在师院生过孩子,怎么知道?”
她也不知道姚小萍到底算不算得上搞清楚了,只提醒说:“我就是想问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事——”
“那你不能等我开完会?”
“到底是孩子的事重要,还是你的会重要?”
“孩子的事重要你现在问了也不能做什么,反而把我开会耽误了,你把我叫出来,我就不知道别人在讲什么——”
她有点语塞,但她不服气,嘴硬地说:“你会上那点事,就算你错过了,你不会问问其他人?”
“那你不会问问其他人?”
“我问谁?”现在她已经是相当生气了,她觉得作为一个即将做父亲的人,听到自己孩子的出生权有了问题,难道不应该条件反射地着起急来,慌忙地跑去打听或者想办法吗?把他叫出来了,他还这么不高兴,到底有没有一点爱心?
她赌气说:“你去开你的会吧,我回D市去了——”
他瞪着她,生气地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专门拣我忙的时候耍这种小脾气,我跟你说,你要回去你回去,但是如果你在路上出了什么事,把我的孩子——弄怎么样了,我跟你没完!”
她被他唬住了,又觉得他还是很爱孩子的,可能现在逼着他去打听生育指标的事真的有点过分。她不敢再提回去的事,只绷着个脸,表示没有屈服。
他生了一阵儿气,说:“你别给我添乱,你给我好好待在这里,等我开完了会,我会找人打听的。你懂个什么?就知道瞎操心。”
他说完就返回去开会了,她气晕了头,真恨不得马上跑回D市去,但她现在两眼一抹黑,去哪里坐车都不知道,而且身上一分钱也没带,想跑回D市都不可能,只好又给姚小萍打电话。
两人七扯八扯地聊了一通,她问:“上次我转让给你的那些书,你——后来跟黄海——联系过了吗?”
“联系过了,我说把书钱寄给他,他叫我别寄,说那些书他是送给你的,你想怎么处置都行,但他绝对不会收钱,我寄钱过去了他也会给我退回来的,别搞得两人寄来寄去,白白浪费人力财力——”
她很惭愧,书是黄海送给她的,而她转让给姚小萍了,这让她觉得很对不起黄海,她下意识地为自己开脱说:“你有没有告诉他,我把书转让给你,不是因为我对他——有——意见而是因为我想考出国?”
“我告诉过他了,我说其实不是你想考出国,是卓越叫你考出国——”
看来在开脱罪责上,她还需要向姚小萍学习。她问:“那他怎么说?”
“他说他会去帮你搞出国考试的复习资料,不过他听说本科生出国不太容易拿到全额奖学金,怕不好签证,但是也有很多人办成了。我叫他别搞资料了,你们家卓越路子那么广,肯定能搞到复习资料。但他说没关系,资料多没坏处,可以互补,就算两人搞的资料一模一样,也不用喂饭给它们吃——”
她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家卓越路子是广,但到现在为止还没给她搞来什么出国考试的复习资料,她这段时间忙着结婚怀孕做家务,也没心思催他去搞复习资料。但听了黄海的话,特别是看到今天来开会的人个个比她学历高,再加上跟卓越闹了点矛盾,她心里那点事业心学业心又蠢蠢欲动起来。
她冲动地问:“你——有没有——黄海的电话号码?”
“我有,你想给他打电话?那我上楼去拿我的电话本,你过十分钟再给我打。”
她等着姚小萍找电话号码,不由得想起那时侯黄海为了弄清卓越是不是故意支开他,竟然冒险跑到传染病院去核实,那时黄海就说是卓越在搞鬼,而她不相信,结果后来卓越自己亲口承认了。她听见卓越承认的那一刻,并没觉得这事坏到哪里去,只当做卓越爱她的一种表现,但现在却触目惊心地摆在那里,仿佛在嘲笑她的智商一样。
她现在觉得卓越有很多事都是可以一分为二地看待的,关键看你把他当什么人。如果你把他当好人,那些事都可以解释成好事;如果你把他当坏人,那些事都可以解释成坏事。他撒谎说钢厂要抓黄海,以此调虎离山,把黄海赶走,可以说这是他爱她的表现,也可以说这是卑鄙的做法;他为她安排留校的事,可以说这是为她前途着想,也可以说是为他自己的婚姻着想。
也就是说,卓越这个人做事,要么动机不好,要么手段不好,要么动机手段都不好,似乎没哪件事是动机手段都好的。调虎离山那件事,是手段不好;帮她办留校这件事,是动机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