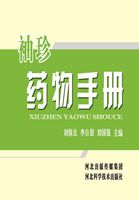“砰”——
一声枪响,一群鸽子飞上天空的声音,四面散去。
我看见大量颜色的弧线在逃窜,在逃亡。夜空里的突围,绽放出突然的礼花,永久地留在我的视线里,
夜深人静,我布满血丝的视网膜,总是出现一颗、五颗、无数密集的子弹,犹如雪地上的青草,穿透冬天僵硬的肌肉,瞬时吐出烈焰般的火舌,温柔地舔着周围。我仍然在大地上行走,麻木,或者微笑,因为我无法回避。
冬天,铁丝网附近。那对二战时期的恋人,相互凝视,他们拥抱,坐在残缺不堪的木制炮弹箱上,一直接吻,一只鸽子仍旧站在铁丝网的上方,眺望。远处,烟尘滚滚,不断闪射出黑色和红色的光晕。是哪一场狂轰滥炸,主人带花园的小院,尖顶阁楼上的鸽笼,在一群鸽子飞起不久,也学着鸽子的样子飞了起来……那只鸽子再也没有发现其他的同伴,更没发现飞上半空的自己的巢穴。它注视着远方,从那对恋人的身影看过去,突然发现一颗金属光泽的飞行物向这里飞来。这次,鸽子没有惊动他们,轰——火光中,他们飞远了,鸽子仍旧站在原地,无法第二次飞翔……
我闭上眼睛都能看见一切。
床头上,我慢慢打开保罗?策兰的诗集,黑暗的房间发出鸽子撞击墙壁的声音,自来水在锈蚀的铁管里吼叫,在书页打幵的余音里面,一直缭绕。
有一天,我突然听到他的诗行里传来翅膀拍打的声音,越来越强烈,我立即拨通一位流浪诗人的手机,信号穿过无数陌生城市和乡村的上空,一直漫游。他说,他正在去海南的路上。他说,他正在穿过一片墓地,正准备穿越琼州海峡,浪涛声打湿了我的右耳……海鸥在大海和我的右侧翱翔。
时间交织、纠缠,电脑屏幕,无限地虚拟。在满天的雪片和纸屑飘舞中,我看见他,在蓝色集中营。他亲眼看见纳粹用长枪击中了母亲的颈部,血流了出来,如刚刚出生的乳鸽,兴奋颤抖……他在这一刻飞了起来,从没写过关于鸽子的诗歌,他写黑色牛奶,写白色草丛和树,写银色的教堂和血色的声音。
清晨的黑色牛奶我们在傍晚喝它
我们在正午喝在早晨喝我们在夜里喝
我们喝呀我们喝
……
他无比憎恨自己的母语,静悄悄地躲藏在房间、壁橱外面、地窖里面,把德语撕成碎片,红色蓝黑的墨水,脑浆和矿砂,汞和水晶反复地掺和、蹂躏在一起。然后,他把鸽子的羽毛,从夜空中,从飞翔中翅膀的咕咕地鸣叫里,连血拔下!
我看过世界上最多鸽子的地方,是不是上海的人民广场?它们像雪片一般扑来,甚至飞到我的肩膀上,头发上。它们咕咕低唤和其他鸽子没什么不同,全部盯住我手中的鸽食,仿佛所有的天空都低垂下来,无限地机械地坠落,以一颗玉米为圆心。
瞬间,龙卷风向我头顶狂卷袭来,我被刮向任何远方,是我永远不想去的地方。
现在,我又在深夜的房间,打开书籍,打开音乐……听到远方的你和鸽子,使长江以南的江岸突然转向。天空,张开覆盖一切光线和阴霾的巨大翅膀,使大地疾驶地向南,一直向南……我知道,我不是一只鸽子,今生今世不能拥有——片羽毛。
疲倦了,我蜷伏在窗台上的姿势,很可能就像另一只鸽子,或者是一片刚刚坠落的羽毛……把那片世界上最轻的最洁白的我,夹进保罗?策兰的诗集的倒数第六十九页,让它们和《死亡赋格》,和离我最近的枕巾、圆珠笔、茶杯以及我最喜爱的一些荷兰诗人的诗集,当然还有你正在消逝的名字,小心慎重地叠放在一起。
接着,在迷迷糊糊的睡眠中,断断续续响起鸽子的声音,我和彻夜的礼花、铁丝网,还有那只仍然在不断长大的乳鸽同时地飞,飞越银色山川、月亮和河流,那些诗歌的碎片和弹片一直围绕在我的身边……
我真的飞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