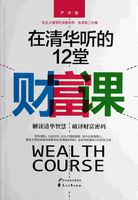慧能看到法性寺(今光孝寺)高高的旗杆上幢幡高挂,迎风招展,心中一阵兴奋。他知道,寺院里幢幡升起,五色彩带飘扬,表示有重大法事活动。今天单升幡旗,则表示寺里有高僧讲经。
慧能跟随着络绎不绝的人流,缓缓走进法性寺。
这法性寺,是南国规模最大的寺庙,尤其是寺中的戒坛,可以说是天下闻名。在僧众中,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
早在南北朝时期,印度高僧求那跋陀罗建造了这座戒坛,并预言,二百五十年后,将有肉身菩萨在坛上受戒。在他建坛八十年以后,另一位圣僧专程从印度带来一株菩提树,栽种在戒坛旁,他还立碑刻文:一百七十年后,当有肉身菩萨在菩提树下大开法席,普度众生。
二百五十岁的戒坛依旧庄严,一百七十年的菩提高大参天,枝繁叶茂,树荫匝地。它们在企盼着肉身菩萨的到来吗?
慧能嘴角泛起一缕神秘的微笑。大殿里,僧俗四众井然有序地盘坐在蒲团上,等待着印宗法师开讲《涅经》。这时,大殿内一片宁静,大殿外五彩缤纷的幡旗在阳光照耀下,在春风的吹拂中,自由地招展,煞是好看:蔚蓝的天空,因它绚丽的色彩而生机勃勃;古老的寺庙,因它的曼妙飘扬而意趣盎然。许多人都被这奇妙的景象所吸引,扭头观望。一位青年僧人大概过分投入、过分陶醉了,不知不觉喃喃道:“春风吹得幢幡动,赤橙尽染艳阳天……”
一个老年和尚不客气地打断他的沉吟,呵斥道:“年轻人!一天到晚心随境转,只知吟诗作赋,禅机却一窍不通。什么风吹幡动,应该说是幡自己在动。”青年僧人倒吸了一口凉气,一脸的茫然:“你,你是说,幡自己在动。”“那当然。因为幢幡高挂,就有了飘动的可能性,所以……”这时,恰恰风停了,漫天飘舞的幡旗静静地悬垂下来,一动不动。青年僧人急忙打断老和尚的话,说道:“不动了,不动了!你看,你看,幢幡真的一动不动啦!因为眼下没有风!有风则动,无风则停。可见,是风吹幡动。”
老和尚漫不经心地望了望高高的旗杆之上死蛇一样纹丝不动的幢幡,不慌不忙说:“照你这样说,动性在风而不在幡了?”
“那当然,你自己不是都看见了吗!”“那好,我来问你,刚才那阵风,是不是也吹拂了白云山?”白云山,是南海城外的一座风景秀丽的高山。在法性寺里,抬头就可以看见它的直插天际的峰峦。青年僧人说:“白云山离这里不远,吹动幢幡的风,应该也能吹到它。”“那么,白云山刚才是不是也像幢幡那样摇摆不止呢?”老和尚咄咄逼人的目光紧紧盯着青年僧人,“说呀,你倒是说呀!风是不是能吹动白云山?”“这……”青年僧人虽然张口结舌,无法回答,但他从心里不服,总感到老和尚的理论有些似是而非。然而,面对人家的问难,他又无言以对。正在他上不来又下不去,处境十分尴尬之时,一个清晰且坚定的声音从大殿东南角传了出来:
“我看,既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两位师父的心在动。”宛若巨石落入深潭,一时惊了寺院内的众人,他们几乎同时向那声音传来处望过去。
一直闭目倾听二僧辩论的印宗法师也眼睛倏地睁得老大,于是,他敏锐的目光将一个四十来岁、衣衫褴褛的汉子捕捉在了眸子中。印宗是亲见过五祖弘忍的高僧,道眼明白,单单听这一句话,他就知道,眼前这位说话的男居士非同一般。
所谓风动、幡动,本质上是心与境的关系。风是境,幡是客尘,所以释迦牟尼说:“有因有缘世间生,有因有缘世间灭。”佛法是缘起法,它的最高明处,就在于揭示了宇宙人生的真谛--缘起性空。佛陀还说过,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是因缘所生,并且互为缘起,互为依存,互为条件,互为前提,也就是互为因果。
例如风与幡,如果只有风,或者只有幡,就不会有风幡舞动的现象;或者幡虽然有,但它没有高高挂在旗杆上,无论再大的风,也无法将它吹动;或者幡升了起来,但风没有吹在这里,而是刮在了其他地方,这样都不会有风幡飘动的景象出现。
为什么是心在动呢?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动静、善恶、美丑、好坏……世界上的一切矛盾对立,都是我们这些人各自依据自己的好恶、利害……强行分别而产生的。所有争端的升起,一切矛盾的产生,也都是源自我们以不同的价值、取此舍彼的结果呀!谁对,谁错?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慧能早就说过,境由心造,法从心生,一切都是我们的心在动。当时,印宗大师的心也在动--他早就听说禅宗衣钵南来了,莫非这个出口不凡的居士就是五祖的法脉传人?于是,离座相问--果然是六祖出山了!
当时,慧能还是居士之身。于是,印宗就作为他的剃度师,为他在二百五十年前求那跋陀罗所建的戒坛上落发出家。也就是说,印宗是慧能的师父。但是,当慧能正式受戒之后,印宗立刻舍弃了自己的剃度师身份,反而拜在慧能座下,以慧能为师。
佛门无贵贱,达者为上首;禅法皆平等,悟道自为尊。六祖慧能就在那株神奇的菩提树下,大开禅法,广度众生。一年后,他应韶州百姓所请,离开南海,回到曹溪宝林寺(今韶关南华寺)。从此,曹溪成了天下禅宗的乳源。时至今日,世界禅宗僧俗,都是六祖的儿孙。
景深
“入此门来学此宗,切须仔细要推究。清虚体寂理犹在,忖度心忘境自空。树挂残云成片白,山衔落日半边红。是风动也是幡动?不是幡兮不是风。”这首《山居诗》是宋代曹洞宗高僧石屋体会到“风动幡动”的境界后有感而写的。
六祖慧能并不否定风吹幡动,关键是我们的心不能被外在的东西所干扰。清晨,一群人站立在河边,等待着渡河。河边野渡,没有码头。为了方便船上的人们上下不湿脚,船夫总是尽力将船头推上河滩。河边上觅食的小鱼、小虾以及藏在沙子里的小螃蟹,因为渡船的往来,有一些被船压死了。一个禅僧路过这里,恰巧一位散步的秀才也同时走来。两个人都看到了渡船压死鱼虾的情景。
秀才问禅僧:“禅师,你看,船夫将船推上、推下的时候,很多无辜的小鱼、小虾、小螃蟹被压死。你说,这是船夫的罪过呢,还是乘船渡河人的罪过?你们佛教讲究因果。将来这个杀生的罪过,是归船夫,还是乘船之人?”
禅师指着秀才的鼻子说:“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的罪过!”秀才当然十分生气,理直气壮地反驳道:“你是不是神经病?怎么说是我的罪过呢?第一,我不是乘船之人;其二,我更不是船夫。那些死去的鱼虾、螃蟹,根本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你多管闲事!”禅僧呵斥道。船夫为了渡人到彼岸,心中没有杀死那些鱼虾的意念;乘船之人只是要过河,更无伤害那些小生灵的想法。他们的无心状态,就像不动的幽潭之水,天上风起云涌尽映其中,却不妨碍它的平静;空中浮云消长,影响不到它的澄清。而秀才心中妄生分别,自己平添了许多烦恼。因为,他在评论他人长短善恶时,必然添加进了自己的是非判断,为了说服别人同意自己的观点,必须费尽心机,让自己的身心不能放松,不得自在。其实,谁的罪过都不干他的事,何必平地起风波,让自己的心随之转动,朝也寒风,暮也热浪,一刻也不得安宁清静?
宋代临济宗高僧龙门清远禅师在法堂上给弟子们讲了一则故事:有一位禅师持戒极为精严,平生连一只蚊子都没有伤害过。人们都说,他已经是功德圆满的得道高僧了。一天半夜,禅师内急,只穿着内衣急急忙忙向厕所跑去。深秋的夜晚,天气很是寒冷,所以,禅师来去匆匆。忽然,他感到脚下踩到了什么东西,而且还发出“叽呱”的声响。
黑夜中看不真切,但从声音判断,禅师认为自己踩到的是一只蛤蟆。并且,他感觉到那蛤蟆肚子里无数的卵都被他踩出来了!
天哪,这是杀生啊!而且是多得不计其数的小生命!禅师战战兢兢,跌跌撞撞回到寮房,失魂落魄地一头栽倒在了床上……虽说是无意的,但毕竟破了戒,数十年的修为付之东流。他自怨自艾,长吁短叹,不知在床上折腾了多长时间,才迷迷糊糊起来……这时候,禅师看到有好多蛤蟆从四面八方蹦蹦跳跳而来,将他团团围住,异口同声向他叫喊:“还我命来!还我命来!”原来,是那些在他脚下丧生的蛤蟆卵冤魂不散,向他来讨还命债……禅师惊叫一声,从梦中醒来。他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像是泡在水里一样。他再也无法入睡,坐在床上发呆。若是一命还一命,他何时才能偿还完那无数的命债?天亮后,他尽管不愿意去看那惨不忍睹的场面,但还是顺着原路找去。他要去超度那蛤蟆的亡灵,忏悔自己的罪孽。可是,当他回到原地一看,哪里有什么蛤蟆?路上躺着的,分明是一只老茄子!
宛若突然间卸下千钧重担,禅师心中的疑惑之情顿然消失,豁然开悟了:三界之中并无实物,一切唯心所造!
讲完故事,清远禅师问众人:“那僧人夜间踩到的究竟是蛤蟆还是老茄子?如果说是蛤蟆,天亮看到的分明是老茄子;若说是老茄子,天不亮时又有许多的蛤蟆来讨还性命。诸位能断定吗?”
清远禅师锐利的目光从大众脸上掠过,停顿片刻,一拍禅板说道:“让山僧来为诸位断断看吧。蛤蟆的疑情虽然消失了,茄子的见解却未去除;若想得到无茄的见解,那就中午敲打黄昏时的钟鼓吧!”
唔?一切尽在细细的品味中。
心语
佛祖拈花,迦叶微笑。禅的精髓,在于心的感应和体悟,语言、文字往往是难以表达的。唯有心有灵犀,以心传心,才能心领神会,心心相印。因此,禅宗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为宗旨,即心即佛,是心作佛,直承佛之心印。
其实,说起来,莫说成佛做祖,就是人世间穿衣吃饭,也莫不在于心的妙用。钱锺书曾经说:“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因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食物符合你的口味,主要是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轻松的灵魂可以专注肉体的感觉,以此来欣赏,来审定。”
人生之惬意,正是如此。所以,要善待心,善用心,保持一颗明澈不昧的真心,不但能洞悉幽微,激发想象,更容易感悟日常生活中的美好。
3.找到真我了吗
六祖慧能第三次来到韶州曹溪,正式住持宝林寺。禅宗六祖在岭南出山的消息很快传遍佛门,许多僧衲闻风来投。
正是春暖花开、春光明媚的大好时节,行脚云游的禅僧,禅杖为马越千山,草鞋为船渡万水,在大江南北的丛林之间参禅问道。这一天,曹溪路上风尘仆仆行进着一位青年僧人。他叫法达,别看年纪不大,僧腊(出家的年月)却很长--年仅七岁便出家了。他听说六祖显身了,便不远千里,从洪州(今江西南昌)赶来拜谒。然而,当他走进宝林寺,真的见到六祖慧能时,很是有些失望呢:难道,这个又矮又丑、又黑又瘦的人,就是禅宗第六代祖师吗?难道这个一字不识的村夫,真的精通神奇而又玄奥的禅法吗?
不过,既然来了,法达就不得不按出家人拜山的规矩,向堂头大和尚顶礼三拜。当然,他的礼拜很是有些敷衍了事,连脑门都未曾触到地面。六祖见状,呵责他说:“僧人顶礼,应该五体投地。而你这样头不着地,还不如不叩头!你这样做,心里必定藏着什么自负的东西!”
“我法达,修持《法华经》十几年,已经念诵了三千多遍。”说着,法达的头下意识地仰了起来。
六祖说:“你叫法达,何曾达法?僧人顶礼,不仅仅是为了表达对他人的尊重,更是为了折服自己的‘我慢’之心。因为,出家人心中一旦存留傲慢的习气,便无法体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理。你只是口头上念诵佛经,而不明了经典的意义。你要晓得,只有明心见性,才能称得上菩萨。”
法达面红耳赤,尴尬地站在那里。六祖轻轻叹了口气,缓缓说:“唉,你今天远道来见我,也算有缘分,我现在告诉你佛法的妙义。”六祖递给法达一杯茶水,等他一饮而尽后,问:“法达,请你准确地描述一下,这杯茶水是什么滋味?它与你以前喝过的茶有何区别?”“这、这、这……”法达吭哧半天,也无法精确表述出茶水的味道。
六祖一笑,说:“禅,不可言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佛法的奥妙,也无法用文字来表达。一切经书,包括《法华经》,都是佛陀教导我们开悟的工具。它如同指向月亮的手指,目的是让我们顺利、快捷地找到月亮。而手指本身并非明月。你若是仅仅研究手指的粗细、长短、颜色,永远都找不到天空中的月亮。
所以,学佛之人要直接探求佛法的本意,而不是执着于经典。你如果用这样的心态持诵《法华经》,那么,一切妙法就会像莲花一样,自然而然地从你的口中生出来。”
法达听后,豁然有醒,不过,心中仍然存有一缕疑惑,犹犹豫豫地询问道:“这么说来,只要理解了经义,就不必劳神费力地读诵经文了吗?”
六祖说:“你这种‘非此即彼’的机械理解,又陷入另一种教条。经典有什么过错,岂能妨碍你持诵?若是口中持诵经文,心中也能实践修行,就是‘转经’;若口里念着经文,而心中另有所念,那就是被经所转。”
六祖对法达吟诵了一首偈子:“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诵经久不明,与义做仇家。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无俱不计,长御白牛车。”
《法华经》中,白牛车代表着人类自性的本源。法达闻偈,恍然大悟。从此,他一生追随六祖,成为慧能的十大弟子之一。
六祖慧能大师在曹溪扩建寺庙,接引学僧,忙得不可开交。一日,他发现,祖传的袈裟皱皱巴巴,沾染了一些尘土。于是,他便忙里偷闲,拿着袈裟出了山门,计划到曹溪之畔浣洗。
曹溪之水弯弯曲曲,漂着烂漫山花,映着蓝天白云,在宝林寺前潇洒地画出一条弧线,然后撒着欢儿奔向远方。溪水边,有几个小沙弥正在洗衣服。他们也太勤快了,甚至连穿在身上的衣服都洗了--你撩一下,我泼一盆,结果大家浑身上下都湿淋淋的。他们无忧无虑,似乎比清凌凌的曹溪水还要欢乐,还要活泼,河滩上大大小小的鹅卵石也仿佛都是他们咯咯的笑声凝结而成的。
六祖悄然离开了。一则,他不想因为自己的到来而使得弟子们的欢声笑语戛然而止;二来,他想,这袈裟是由达摩祖师从印度带来的神圣之物,万一溪水上游也有人浣衣洗物,污垢顺流而下,岂不将袈裟亵渎了?
慧能转身,手持禅杖,向寺院后面的深山走去。行行复停停,寻寻且觅觅,边走边观察,不知不觉已经走了四五里路,来到了一片茂密、幽静的山林中。
这里古木参天,芳草茵茵,瑞气缭绕。不知为什么,六祖嘴角泛起一丝淡淡的笑意。他神色庄重,站在一块空地中央,闭目沉静片刻,然后,将手中的禅杖一振,往地上戳去。他并未用力,但禅杖竟扎入大地深处。更不可思议的是,随着禅杖的拔出,一股清泉汩汩喷涌,片刻之间便汇聚成清澈的水潭,这就是著名的“卓锡泉”。几百年后,北宋大文学家苏轼两次来参拜六祖真身。在卓锡泉畔,他的文思如同这不竭的泉涌,挥毫写下了《卓锡泉铭》。
六祖掬一捧泉水尝尝,其甘醇清洌,令人精神为之一振。他蹲了下来,仔细漂洗着袈裟……“阿弥陀佛。”身后忽然传来了一声佛号。六祖回转身,一位年轻和尚合十鞠躬,问道:“请问法师,到宝林寺怎么走?”
六祖看他风尘仆仆、一副长途跋涉的样子,手里提着湿漉漉的袈裟,站立起来问:“你从哪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