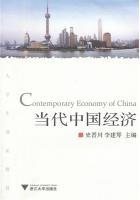“废物,尽是废物!”淡客居内,苏灵儿正怒不可遏地砸着东西,地下跪了一地的婢子,皆悬玉牌,除谷雨、小满、霜降,另有寒露、小雪、大雪诸名,约摸十六七人。
苏灵儿将一个哥窑青瓷双耳瓶狠狠掼在地上,犹觉不解气,又接连砸了几个梅花盏,方指着悬玉使女们道:“十五个人,竟杀不了一个上官清,一个个铩羽而归,且还将白露与小寒折在三峡,好是为我长脸!”
人人瑟瑟缩缩,低头顺眉,大气也不敢出一口。偏苏灵儿还不肯放过她们,指着个婢子道:“寒露,你说,究竟是怎生回事?”
被唤作“寒露”的婢子眼尾上翘,颇有媚色,现下暗自叫苦不迭,却也只得硬着头皮拜道:“姑娘,请恕婢子无能,那上官清实在厉害。白露与小寒最先发难,不想三招之内,被他一掌打入江中。婢子与小雪、大雪出手皆是杀招,却也被一招封了穴道,他实在是……实在是……”寒露越说越愧,越说越怕,竟不敢抬头看苏灵儿。
“三招?”苏灵儿冷笑,森森道:“江湖中,你们哪个没有威名,哪个不是横着走的人物?如今就这点本事,我养你们有何用?”
众婢子听出苏灵儿言外之意,面上皆没有了血色。苏灵儿道:“你们大概忘了,失手的下场!”谷雨面色一变,便要求情,苏灵儿又道:“没能杀了上官清,你们就该自杀在三峡,活着回来,是想去天香楼么?”
自杀尤可,只那“天香楼”三字,寒露诸人听了,入耳若有雷鸣,几有晕眩之感,险险便要把持不住。
天香楼是扬州最负盛名的青楼。它原本不叫天香楼,苏灵儿梳弄之前在此卖艺,因着绝俗姿容,一度艳名远播,仰慕者多如过江之鲫,差点便要踏破门槛。那老鸨借着苏灵儿盛名,便改作了“天香楼”,越发地名声大噪了,只苏灵儿将之视作毕生奇耻大辱。
得势之后,苏灵儿头一个就是杀了天香楼老鸨子,将她扔去了“坟场”,派了个悬玉使女名唤清明的去接管。原来苏灵儿宅中婢子,多是良家子,官家家眷尤其多。良家女子最在意的,便是清白,厕身苏宅,便能免于教坊之遭。是以苏宅女子,上至悬玉使女,下至粗使仆妇,为苏灵儿办事无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毕竟一旦不得力,下场多是发配天香楼,做那些迎来送往的营生,前番那个因着开门晚了一步,引得苏灵儿勃然大怒的观文便是一例。
天香楼的老鸨子清明,对外唤作秦端端,极是声名狼藉:据说她与官府勾结,据说她逼良为娼,据说她常克扣姑娘银钱……只是既为悬玉使女,清明干下的恶事,远远超出世人对老鸨子的想象。苏灵儿“江南王”一半的恶名,由她成全,是以深苏灵儿赏识信任。任着悬玉使女更迭频繁,她自巍然不动。如今清明前四位悬空多年,她俨然是廿四悬玉使女之首。
清明也是长袖善舞之人,经营天香楼许多年,竟有了如今的气象。天香楼枕河而居,白天虽冷清,一到夜里便灯火通明,河上画舫往来不绝,混着桨声灯影和着楼里楼外的咿呀弹唱声,女子娇嗔的谑笑声,直是扬州城,甚至是整个江南最热闹的去处。
风月几多数,天香楼自高。丝竹凝歌,霓裳掠影,软语娇笑,暖风熏香,人间天上。千种娇媚、万般风情,直教多少世人忘忧忘愁忘痛忘悲,多少英雄忘壮志忘报负忘雄心。
时近黄昏,天香楼楼门缓缓打开,早有欢客相候。
“啊哟哟,您来了!”一群艳裳女子簇拥着一女人。看她年纪,不过三十出头,并不十分美丽,却有万种风情。最令人着迷之处,是她偶而一现纯净如孩童的笑容。那一瞬间,好似芙蓉洗污秽,珠玉出瓦砾,让略显粗糙的五官,有了窒人心魂的美丽,妖媚得惑人,总是勾得许多欢客情迷意荡,似醒还如醉。
她便是清明,整个江南恶名昭著的青楼老鸨子。
飞花里,飘絮间,施施然走来两人。一人蓬发虬须,掀鼻阔面,脸生横肉,体形高大壮硕如黑塔,一身的煞气,直是恶鬼一般的形容,令人望之生畏。另一人截然反之,两相映照,有瓦石与珠玉之别。
那人眉稍横溢风流,眼角蕴藉烟霞,顾盼本无心,转眸若有情,而身姿如临风玉树,如挺拔青竹,如淡烟流水,萧萧肃肃而清逸绝尘,正是神仙一流的人物。奇的是,此人姿仪既美,乍看如弱冠少年,再看又似不惑丈夫,只因鬓角发间染上风霜而有了岁月的痕迹。那整丽容颜,也就是添了这抹沧桑,反更有清致。饶是见惯了南来北往人的扬州人,也被他所惑,是以一路走来,谁撞了谁,谁踩了谁,谁挤了谁,都无从去计较。
这二人径向天香楼而来。清明不经意一回头,瞧见了他们,眼中有着讶然之色。他们逆着光,夕阳洒在那郎君身上,映出一圈绚丽的光晕,仿若踏着霞光而来。清明眨了眨眼,终于瞧分明了,眼中绽出绚目的光芒来。
自那群痴缠的男子中摆脱出来,清明一手搭在那郎君肩上,整个身子趁势贴了上去,便有欢客吃味道:“此人是谁?”清明媚笑道:“前度刘郎!”又向那人道:“你……”眼珠转了转又道:“这位相公不知该当如何称呼?”她一径说着,一径向身侧心腹递了个眼色。
她这厢风流快活着,却不知自己姐妹们,正在淡客居内度日如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