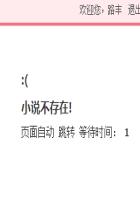2013年年初上市就带来了一时反响的作品,作者柴静的散文作品同样入选2012年中国散文排行榜。我把它放在5本书的第一位来写。这部以随笔笔法完成的纪实作品,与之前的个人性作品有太多不同。并不想以高下立判,而是它有一种鲜明的时代感,这种感觉是民国到建国时期的杂文著作没法比的,更是古代社会的议论性著作望尘莫及的。所以这个文学观的更新在这里就体现得比较明显了。
何况她的主业是播音主持和新闻报道。不是说任何一个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都要具备较强的文学能力,在新闻出版的职业种类越来越多的今天,职业的分化首先在时间性上就要强过一百年前的太多。然后细分到细节职业要求,对文字需求的多少、寡众直接影响了从业者对此的专注。因此既能以这种纪实性散文作品勾勒自己的职业背景,又能表现文学观的独到的,《看见》一书自然第一时间进入我的选择范围了。在这里也还要题外话似地向柴静姐姐本人表示赞佩,年初因此书的出版传出的“央视最穷主持人”的说法,她给以的从容自信的回答愈发让人亲近。
恐怕一百年前的周作人、朱自清加上五四那一批闯将要革新的写风到了今天都会自叹不如了。那个时代太重要了,其实在之前的几个章节都提到了。在时间上承上启后给了后来的中国新的历史生命力,又以中国的复苏影响了世界的发展格局。那一批人在文学上的自信直接给予了破败不堪的中国旧社会以精神上的巨大刺激,他们一定也认为自己要革新的文学观比古代中国文人强无数倍。而到了2000年,你会发现他们死得悄悄的,一点生气都没有了。当然我不是说这部作品的问世比2000年以来的任何一部文学类作品都要突出,水平都要高,然它所展现的自信已经完全不只有文字上,也与当下文艺青年只停留在仰望前辈、今天的著名作家的写作成就时都在喟叹的“我什么时候能够达到那样的文学高度啊”上完全不同。《看见》一书所透出的是对技术进入社会操作中的复杂性,是文字背后不只是蕴藏的思想,更有人与人间模糊、陌生的关系,而具体技术在社会单一机体中起到的随机与计划性作用更加深、递进或消退了这种关系。21世纪的人口基数激增的全球社群,其生产能力、世界观与所掌握的技术都完全是20世纪初那会儿没得比的了,由此构造的一圈又一圈人与周边、生命共同体相处的网络纵横交错,与虽然整体格局混乱、文化从废墟中拾起然人际关系仍处于封建习俗当中对比今天一定落后但在其中表现出简单的一面相比,就真的复杂太多了。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技术层面的复杂性,人际关系对周边的几层影响同样为技术系统的更迭提供了主动或被动的实现空间。一个无从否认的前提是,无论你谈不谈技术使用,实际操作技术还是思想技术,在个体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其实都无法避开它们。而只缠绵在文字的技术到文学技术层面的五四人,与五四一个时代但并不从事五四写作的文化人,他们所从事的文字事业想来在当时的新思潮鼓励中一定高于19世纪。但到今天文学能力其实已经进入了各个阶段、社会部门的全民使用大潮里,你也能看出文学观的急速更迭了。
在这里当然提得出一个悖论,需要为大家理清一个思路。在政治与军事主导的古代中国历史当中,文学从来都是副业。在不同时期文学的主要体现都是文字,而文字以不同形式出现使当时的人获得信息上的便利,就成为了到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各种体裁、作品风格了。这个时候,因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资源分配的多少,也自然出现了当时生产条件下的部门区别。为了获得生产发展上的便利,从业者都会使用文字利于生产条件上的满足,文学能力就进入了各个阶段、社会部门了。这就是我要理清的一个思路:古代社会不管是大的行业分工,还是具体领域内的分工,都达不到今天的高度一体化;生产条件的限制使文学能力即使进入了各个部门,也只是以陪衬的状态出现,烘托生产对象。而今天无论是文化共同还是技术使用认同,都已经使文学的实际社会生产能力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文学生产再也不是社会生产的副业,而早已能具有极强的社会独立号召能力了。于是,我们从文学观的更新来到文学的历史地位变迁之后,这里迅即进入了接近于今天的主要社会性讨论“文学的边缘、死亡还是主导”的时髦辩题了。而这三个层次的快速推进,哪里是白话文推广以前的文化习惯里能够想象的。
我不能说《看见》一书更新了文学观,也不会就按照这个时代被普遍教育了的文学使用,就是直接放大到与它同期的作品里去看,这些作品合在一起就更新了从上世纪过来人的文学观;也不是反过来说,因为文学观随社会、历史变迁的更新而推出了《看见》,推出了与《看见》同一时期的其它作品,它们比上世纪同一时期的作品都更具魅力与时代感。因为这一逻辑根本无从成立,也没有任何可比性。你无法想象《红楼梦》是公元前8世纪的作品,你也无法将它挪到新世纪以来,今天有哪一个作家能够写出一部《红楼梦》的?你更难预测在22世纪的这个时间段又会问世什么新作了,会不会出现一个曹雪芹级别的作家。所以我希望以此提出的在文学观更新上的建议是,《看见》一书同作者在20世纪末以来的职业背景为我们生活年代的文学提供了新思路。这个思路并不算特别大,然却同旧社会的文学使用完全不同。新闻工作随时间和技术条件的推进有了极大变化,技术上使用的简捷高效同人思维和方法的急速提升让文字处理在其中也变得明快。而总有极端的文化批评者喜欢拿一个新鲜出来的东西就比作什么新思潮革命的标志了,认为这是“以小见大”,是远见卓识。完全不必如此,就连作者本人也不应会有这一想法。越是从微小中所见才越体现真知灼见,越是自然所为才越展现伟大潜力。在这里更不是提倡平庸,而是诚心进入生活细节、见习细节,以己之独立思考理性自我,才能去赢得所有。
作者所做便是如此,《看见》所写亦是如此。其实我觉得在明白了这一道理后才是真正的文学观的更新啊。前文有述,简单的文字技术使用已经被时尚大潮大幅赶超的时代里,即使再提出什么体裁上的创新都显得价值不大。而我所提出“足球文学”即使希望实现一种体例上的创造,也会对此所保有的信心产生质疑。首先是拿不拿文学行为与时尚行为作比较的问题,在这里还要分时尚文学和严肃文学;然后是文学行为与时尚行为各自的内里,它们同时发生且并行不悖,其实都无义做跨界的比较的。内中无论信心几分,都在自行生产。在这里我就看到了那个真正更新了的文学观了。自然而然的文学行为,不受约束的文学行为,不被审查的文学行为,为时代而作的文学行为,为人而作的文学行为。以上的文学观说明了除了写作,文学的发生方式在今天已经极为多样。在交叉的、同行的社会各个部门里都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而在民智未开、国家破败、主权沦丧、弱国无外交的旧社会,这样的看法在半文半白的表达里都显得含糊其辞,最有信心的那几大文化伟人在文字里充满生机,其实已经表现了以上文学观的自信,但现实里却只能使自己从国运衰败的体悟中感受迟暮。因此,这一文学观所要表达的时代信息就是真正得到更替的。即使时代已经趋向了声像的感知世界,文学的从事者仍然在这里拥有极大信心,并受时代热捧。
与《看见》类似的新闻工作者的传记式、纪实类作品还有不少,比如前文中提到过的芮成钢,还有近年连出两部传记作品的白岩松。他们在工作领域的杰出才能就已经起到了文学观的更新了,在旧社会乃至建国初20年你无法想象今天的新闻工作中发达的技术条件与人智。而这几部作品的出版不过是一个亮点的收尾,以他们为代表的这一人群还将继续在新闻传播领域发光发热,达到他们的职业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