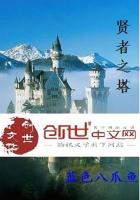原来这雁荡门是浙江的一个小小门派,祖师俞石极原是一个道童,成年之后不能忍受道家的清心寡欲,便私自下山,前往大同府投军而来,在军中一过就是十数年,因为他为人义气深重,又有武艺在身,上阵奋勇杀敌,着实立了不小的功劳,慢慢的便也做了个小小的武官。
正当俞石极打算一展抱负,大展宏图之时,不成想,朝廷腐败,人心不古。俞石极终于看破,留下一封书信,仿效关云长之举,挂印而去。从此游历江湖,最终在浙江雁荡山定居了下来,创立了雁荡门。
俞石极总共收了五个弟子,三男二女,都是俞石极闯荡江湖的时候收养的孤儿,大弟子俞天锡,从军多年,一刀一枪,立了不少功劳,被授了泉州府一个千户的官职,以定东海海贼,俞天锡本来也想如同师父一般退出官场,可石极老人反而劝说徒弟,该出力时应出力,恰安乐时却安乐,现在海贼猖獗,经常打劫过往船只,俞天锡正应为民除害。所以俞天锡便一直留在泉州,他的夫人便是自己的师妹许银珠,赵长河所说的俞师兄就是俞天锡和许银珠的独生儿子俞定波,从小跟随父亲效力军中,现在已经接任俞天锡的千总职务,每日忙着围剿海贼。俞石极的二弟子田明镜,性如烈火,嫉恶如仇,武功在师兄弟中最为高绝,在浙江武林界也是颇有侠名。他的夫人一样是石极老人的弟子姚宝钗,夫妇两人生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田雪冰,嫁给了俞定波,小的名叫田秋雪,却是和赵长河订了亲。田明镜和姚宝钗一直在跟随师傅左右,这些年来石极老人不问世事,门中大小事体都是田明镜处理。最小的徒弟便是刘沅君的父亲刘子钊,学成不久就下山经商,积累下一份大大的产业。这师兄妹五人虽然不在一处,但经常书信往来,关系融洽,像亲生手足一样。
三人默然不语,满桌的苏杭名吃一下子失去了吸引力,足足过了一盏茶的时间,刘沅君耐不住这沉默的气氛,开口问道:“赵师哥,你这次回山是为了什么事呢?莫不是为了师祖的大寿吗?我记得是在下旬的。”
赵长河应道:“师妹你有所不知,今年是师祖七十大寿,古人说,人到七十古来稀,师祖已经在雁荡山整整居住了六年未曾下过山了,所以师傅的意思,要趁这个机会请师祖到苏州来小住几时,因为怕大师伯和二师伯另有安排,彼此冲撞,所以命我先去拜见师祖和二师伯,咱们先定下来再说,本来打算回过山上再去趟泉州的,不成想在山上遇到了俞师兄,他也是奉大师伯之命前来拜寿的,大师伯竟和师傅想到一起去了。不过后来师祖说道大师伯那里事务繁忙,便定了来咱们这里。俞师兄无计可施,只好回去禀报大师伯了。”
刘沅君听了又惊又喜,“这么说来,这几日,师祖,大师伯,二师伯和大林,小林,田姐姐他们都会来咱们家里了?”
“那是当然,你当我们哥两没事老在这里混着干嘛?就是觉得日期差不多了,在这里等着接人。”
刘沅君欢呼一声,重又食欲满满,夹起了一块扁豆糕,几口便下了肚,又忙着夹起一只馄饨,刚要放进嘴里,忽然看见赵长河手里拿着一只灰汤粽,却只剥了一半便停在手里,双眼望向窗外,仿佛被什么事情吸引住了,再看曾江,也是一样,筷子里夹着一只馄饨,却忘了放进嘴中。刘沅君好奇心大起,向外看去,偏偏她坐在里边,视线被窗台挡住了,刘沅君一着急,看口问道:“你们看什么啊?”伸手就拍向两人。
曾江和赵长河被他一拍,如梦初醒,回过神来,彼此看了一眼,曾江吐了口长气,对赵长河说:“你看怎样?”
赵长河也长吐了一口气,方才说道:“好功夫。”
刘沅君自幼爱武,听得曾赵两人说话,似乎外边倒有什么蹊跷,她性子急躁,早已站起身来站到窗前,向外看去,嘴里不迭声的问道:“哪里哪里?”
曾江未曾言语,只是凝神观看,赵长河轻轻一拉刘沅君的衣袖,示意她小声一点,刘沅君只得坐下,向外仔细观瞧,却没有看到什么奇人奇事,心里又急躁起来,问过头去正待询问,赵长河用嘴努了一下,伸出一个手指指向前方,刘沅君顺着他的手指看了过去。只见离开茶楼不远的运河之中,正驶来一只客船,眼看就要靠在码头之上,乘客们纷纷手提行囊,挤出船舱,立在船头之上准备抢先上岸,一眼看去。乱哄哄的,未见有何奇异之处。刘沅君疑惑丛生,她心里知道自己这两位师兄为人精明,曾江固然是爱开开玩笑,赵长河却是绵里藏针,面憨心亮。两人如此作态,必有缘故,于是便更加仔细看去。
忽然,刘沅君心中一动,只见船舱之外坐着一个年轻人,身穿黑衣,手里举着一本书正在仔细观看,周围人众从他身边经过,他竟似毫无感觉,乱糟糟的事情仿佛与他毫无关系一般,乍一看不甚打眼,仔细一瞧却又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显得卓尔不群。刘沅君回头看向赵长河,赵长河看到他眼中的迷惑之意,开口说道:“沅妹你看出什么古怪没有?”
刘沅君又仔细看了一会儿,实在看不出这青年除去行为乖僻还有什么,便摇摇头,赵长河也不多言,站起身来,向桌边走了过来,这桌子本身离窗户很近,赵长河靠了过来,与刘沅君并排坐在一处,不一下说话之间,手中的筷子就碰到了刘沅君的衣袖,刘沅君不解其意,尚自奇怪,忽的脑子一闪,明白了过来,忙看下去,果然,在那船舱之外,即使乘客急忙奔出,那少年却仿佛无影之人,没有一个乘客碰到了他的身体。
眼看船已靠岸,乘客们蜂涌而下,那黑衣青年看看四周无人,方才站起身来,将所看的书仔细收好到包袱里,背起包裹,走向搭班,这下刘沅君留上了心,只见这青年踏上搭板,搭板竟然毫无动静,竟如同上面没有分量一样。刘沅君暗自称奇,江南水乡搭板多用毛竹湿板,取得就是它柔韧之意。长期在水里浸泡,大木虽然结实,却往往糟透断裂。毛竹湿板虽然踏上去忽忽悠悠,嘎嘎作响,却是坚实异常。这青年踏将上去,虽然听不见是否有声,但搭板竟无甚晃动,可见这少年轻功之佳。曾江和赵长河不由自主又叫了一声好。
那少年下的船来,慢慢向这边走了过来,只见他脸色白净,眉清目秀,身材修长,一点有武功的摸样也看不出来,反而倒是像一个赶考的秀才。
刘沅君听的师兄不断称赞这青年,心中不服,又看那青年这般读书人打扮,顽皮之心油然而生,手指一弹,一颗花生已是弹了出去,直奔青年人头顶而去,曾赵两人喝止已是不及。两人心说不妙,这青年人虽说年纪不大,但是内外兼修,功力已臻上乘,刘沅君故意挑衅,对方万一生气,便是一场不小的争执,而且错在己方,不好分辨。不过再埋怨刘沅君已是无用,只好静观其变。刘沅君弹出的虽然只是一粒花生,但是她自幼习武,手上劲力十足,这下全力弹出,这花生去势甚快,打在身上,无亚于一块石头。
眼看花生就要击中这青年,这青年恍若不知,神色丝毫未变,轻轻巧巧,一步迈出,正好躲过了花生。然后,那青年仿佛不经意一般,抬头向茶楼这边看了过来,曾江,赵长河和刘沅君正在向下观望,这下四个人眼光对了个正着。曾江和赵长河赶忙站起,向这青年拱手表示歉意,刘沅君看着这青年人,只见他五官俊秀,不过脸色苍白,仿佛很少见着阳光的样子,一双眸子又黑又亮,看向自己的时候就好像小刀一样,不知怎地,心中便有些慌乱起来,不由自主低下头去,偷偷看这黑衣青年。黑衣青年看到曾江和赵长河拱手,一转眼又看到了刘沅君的样子,已明其意,他生性恬淡,这点小事也不放在心上,嘴角一动,似笑非笑了一下,算是回应,便继续前行。
眼见这青年人拐过街口,身影看不到了,曾江扭过头来“沅妹,你这惹是生非的性子真的好好改改了,幸好对方不甚理会,要不又是一场无端的麻烦事。”刘沅君心中尚自慌乱,闻言只嘟囔了几句,也就不再强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