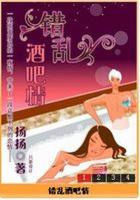话说关远领兵直逼官军大营,这里有着大军粮草并武器盔甲,当然也还有左龙骧军使的行头。由于后队逃散的是步兵,所以溃兵还没有回营,其实他们也不敢回去,都是四散而逃,各自回了自己的老家。
当关远赶到的时候,由于故意没有扯军旗,守营官兵见了还以为是自家军队,看盔甲应该是地方援军,那守营的副将并没有多少防备,关远也放慢了速度。
那副将来到栅栏前高声问道:“前方来的是哪一路援军,可是将军打了胜仗,要移营入城?”
关远听了暗喜,也装着就是官军的样子道:“本将汝州行军指挥使李远,奉王将军将令前来接应粮草入城,还望将军安排弟兄们尽早收拾好草料,日落之前要赶到濮城。”
“既然如此,将军肯定带了大将军将令来,非是末将啰嗦,只是大军草料事关重大,末将必须小心行事。”那副将说着带了十几个人往栅栏这边靠近,只是望着关远,示意他拿出凭信。
关远装模作样的在身后掏出一块令牌,快步走上前就递给了那副将,那副将接过令牌,一个“唐”字映入眼帘,看下方还有一行字,正疑惑间,感觉脖子有一丝寒气,冰凉凉的让人毛骨悚然,身边的军士都是大惊失色,急忙后退了几步,那副将抬起头,一柄寒光短剑出现在他眼里,握着手柄的正是这自称汝州指挥使的李远,利剑就搭在自己脖子上。
这副将大惊,双手举起:“将军,这是为何,末将没有什么错啊!”
其实他这些都是多余的话,当他看到了那块令牌的时候就知道上当了,此时此刻只是为了自己性命,只好与关远说了这废话。
“少罗嗦,你家将军已经全军覆没,识相的就赶紧交出粮草,某饶你不死,否则骑兵冲营,定当片甲不留。”关远说着逼着副将命人开了栅栏门,众兵士见主将被擒,都是手足无措,骑兵已经冲了进来,副将大惊失色,无奈只好命众人投降。
“你们听着,本将并不会滥杀无辜,你们大将军已经全军覆没,现正在我们元帅那里做客,你们是去是留都是自愿,只是要趁早。”关远说着加重了语气。
众人听了都是把目光投向了被关远制住的副将,副将眼睛一闭:“兄弟们,大势已去,按他说的做吧,想走的就走吧,一路珍重。”说完重重的叹了口气。
一时间营里众人都是心乱如麻,一部分只是僵持着,另一部分人却是纷纷逃往营外。
一盏茶的功夫过后,留下的人在三百左右,一问才知原来这后方守营军士只有三百人是王彦章带来的,而那七百人都是各州府分拨的援兵,看来这差别这不是一点点呀。
收拾了一番,三百降兵被关远安排押送着粮草往濮城而去,五百骑兵分两边“护送”,看到大大小小的江州车上全是军粮,怕不有八千旦上下,关远笑得合不拢嘴,一路意气风发的赶回濮城。
县衙公堂上,李祚正襟危坐,堂下全是孟郊山大小将领,当然也还有濮城的知县和兵马指挥。看着被五花大绑跪在堂下的二人,李祚满脸的厌恶之色。
对于这样的文武官员,李祚恨之入骨,历史上就是因为这样的人存在,才让百姓过得生不如死,有冤难申,有家难全,若是异族攻下城池,那遭殃的还不是百姓,身为一方父母官,弃民而逃,身为地方武官,弃城弃兵,在李祚这里犯了必死之罪,如是这二人当时能奋起反抗,死战不退,那么他们活下来在李祚这里就被高看了一眼。
“王松、张崇,你二人可知罪,身为父母官,平日不知为百姓谋福,临战时不能坚守城池,平时还仗着官身欺压良善,搜刮民脂民膏,随意糟蹋百姓,制造多少冤假错案,尔等这样的蛀虫,有何面目活在人世?”李祚气愤填膺的说道。
“小人知罪,小人知罪,只是小人等搜刮百姓钱财非是为了自己,而是前线战事不断,物资匮乏,我等都是奉了朝廷命令筹集军粮,还望大王明察。”王松信誓旦旦的说道。
“哼,朝廷,朱温也配,尔等无需狡辩,你们二人作恶多端,今日落在我的手里,还有何话说。”李祚气愤道。
“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小人们再也不敢了。”两人都是哀嚎求饶,李祚生平最是厌烦这样的软骨头,当下也不想多浪费时间,直递了个眼色给站在旁边的郭开平,郭开平会意,当即叫道:“来人啊,将这两个祸国殃民的腌臜货拖下去砍了。”
说完四个亲兵进来拉着鬼哭狼嚎的二人出门而去,不多时听得两声惨叫,亲兵回禀二人已经伏诛。
处理完了这两个蛀虫,李祚命带上败阵的众将。
不多时,几个被困得严严实实的军将被带了上来,当先一人身长八尺,肩宽背阔,虎目不怒自威,方脸色如古铜,长眉倒竖,当下虽是狼狈,然而难掩英气。
李祚看着被绑着的王彦章还有这等气势,当下也是非常欣赏,看来忠义公死节将果然名不虚传。看众人都在打量自己,王彦章无所畏惧:”豹死留皮,人死留名,阁下可否通个姓名,也好让某安心就死。“
李祚听了暗喜,起身来到堂下,亲释其缚,命人搬来椅子给他坐下。关远等人见了也急忙把其他副将的绳索解开,招呼坐下。
命人摆上酒肉,李祚端了一碗酒来到王彦章对面:”将军神勇威震天下,忠义直追关公,实乃当世良将,小子自不量力请将军做客,还望将军给在下一点薄面,喝了这碗酒再议。“
王彦章见这人虽是年纪轻轻,举止却是大家风范,哪里还是山大王的见识,见了这人又如此礼遇自己,搞得他倒是不知该怎么说,本来打算大发雷霆誓死不受侮辱的他已经做好了慷慨赴义的准备,却没想到人家不是这样的人,只好举起面前的酒碗,一口干了个干净,然后坐下来不说话,想看看这人要搞什么名堂。
将军可能不知,在下仰慕将军久矣,只是无缘得见,如今见将军虎威,却不得不在这样尴尬的情况下,天下纷乱,男儿多是身不由己,但是今天我们不谈其他,只管喝酒。
说完李祚连敬了王彦章三碗,王彦章也不好说什么,只好喝了,众将见李祚这样的举动,一开始不解,最后都反应过来,拉着众人劝酒,一时间,县衙里只听撞碗声、劝酒声此起彼落,这些败将一开始还很拘谨,可怎么经得住热情的众人的攻势,不多久就完全放开了,王彦章也是满脸通红,活跃了不少。
…………
一连闹了几日,李祚只是不提如何处理王彦章等人,又不放他们走,王彦章实在是忍不住了,亲自来找李祚。李祚很客气的接待了他,王彦章也不啰嗦,直接了当问:”寨主,连日来蒙寨主盛情款待,只是俗话说‘无功不受禄’,不知寨主是何打算,还望寨主明言。“
经过几日的相处,王彦章知道了大部分人的名字,当然也包括李祚,只是不知道他的来历,李祚也不好说,是以拖到现在。王彦章又是典型的忠臣,而且在唐朝并未出仕,算是地道的梁人,要是劝降,还真不知道从何处开口。而且他明确的知道此人是宁死不降的典型,这让李祚很为难。
“将军既然问了,在下也不隐瞒,想将军虽然前朝并未入仕,却是实实在在的唐人,虽然将军现在效命大梁皇帝,但是说起来世人皆知这大梁并非天下归心,在下之所以要占山为王,起兵攻城,非是犯上作乱,而是为了我自己的使命,不得不为。”
“寨主这话,王彦章却是听不明白,还望寨主明言。”
“话说道这个份上,我也不瞒你,你知道我叫李祚,却是不知道我的身份是大唐最后一位傀儡皇帝,朱温剽窃我李唐江山,造反登基,才导致天下大乱,战争连绵不绝,我想将军应该知道。”
“什么,你是昭宣帝,你尽然还活着,你......”王彦章显得无比惊讶,身为亲军将领,他怎么会不知道朱温曾经做的事情,所以一时间激动的说不出所以然。
“没错,是我命大,不过现在,命越来越大了,所以,荡平朱温是我的使命,将军神勇,我很是钦佩,所以想请将军相助,只是苦于不知如何开口。”
“可是自古以来,忠臣不事二主,某却不是朝三暮四之人,寨主却是为难我了。”王彦章很是坚定。
“将军,忠不只是对一个人的忠诚,君不见普天之下皆无太平之日,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是所有人应当忠于的对象,若是你忠诚的人是胸怀天下的真英雄,那无可厚非,但若是只为了自己的权力而置天下于不顾,只为了一己好恶而使天下受累,这样的人是天下人的敌人,若是帮扶这样的人显忠心,那不是真正意义的忠,而是迂腐,而是助纣为虐,若将军只是追求权力之人,我也不愿多说,但是将军却是高尚的忠义之士,自当心系天下,所以,我在这里劝将军忠于天下,名流千古。我李祚所求,只是还天下一个太平,早日结束战乱,是希望能够有一天百废俱兴,重回盛世。”李祚滔滔不绝说着,王彦章听得很是入神。
是啊,自己常以忠勇而自居,所信奉无非“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但是留什么样的名,忠于个人还是天下,自己都没有想过。
在王彦章心里,一直以为这个世界强者为尊,只要追随强者,建功立业那才是自己追求的本分,他以为那就是对世界最好的奉献,可是如今听了李祚的话,他才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忠于自己,忠于天下,才是真正的忠义,才是人生最大的价值,那么自己这几十年都算是没有做过有意义的事情吗?王彦章心里很乱,他不知道如何回答李祚,只是深深的沉思。
自己作为亲军将领,自己的皇帝是什么品行他怎会不知,名为皇帝,实为盗贼。只是当时天下已经离乱,李唐早就残破不堪,强者为尊的理念占据了他的身心,所以才会一路随朱温走到今天,若不是李祚出现把这番道理说出来,可能到死,他都不会怀疑自己做的事情。
“话我也就说这么多,不知将军是何想法?”李祚问道。
“寨主,王彦章本是兵败被擒之人,本不该提要求,只是我厚着脸皮恳求寨主,王彦章已死,绝不对梁作战,若寨主允许,自当随寨主为天下而战。”王彦章根深蒂固的想法还是没有被磨灭,李祚也不计较,见得王彦章点头答应,比什么事情都使他高兴,当下都一一答应,至此,并列五代十国第一名枪的两人都被自己挖到。
做好了王彦章的思想工作,其他的就变得简单了,三下五除二处理好了副将、降兵,整顿军队,留下关远、黄兴、马立带两营龙威军并降兵镇守濮城,整顿军务。
李祚领着剩下全部龙威军直扑济阴,此行他也特意带上王彦章,目的是为了让他亲眼见证自己不是为了权力而随意起兵,祸害百姓之人。
大军在路上行了五日,骑兵先锋营再一次抵达济阴,氏叔权在得知李祚等人动向后,早在城上部好一切守城武器,同时城门紧闭,防御做的水泄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