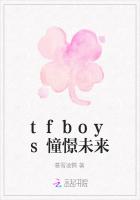“皇上,臣有一言。”奕?道:“若皇上欲与外夷开战,不若笼络这个黄仁仁,臣听说他有一支二千来人的火枪队。不如封他个上京道台的实缺,让英人起疑,到时就算他想不忠于皇上 也不能投奔英人,而我们一个小小的道台则可换个师夷的人才,英人虽是蛮夷,火炮却着实厉害,我们何不让他铸造夷人火器,以夷制夷?”
“老六之言甚善,此谋国之策也。”咸丰点了点头笑道,他慢慢的躺在塌上,似乎有些倦了:“拟旨,封黄仁仁为上京道台,总督上京事物,包括挖矿权利,着他整顿军务,替朕辅佐江 浙巡抚杨文定,剿灭发匪,亦监视洋人动静。”
“喳!”四位辅臣打了个马蹄,齐声道。
“你们先退下吧,朕有些倦了。”咸丰招了招手,不远处的太监小毛子,连忙找来一张金丝毛毯盖在他身上。
“皇上,臣还是有些不妥,这黄仁仁是忠是奸还未可知,况且这上京本是个县城,若是将他封为道台恐怕与理不合。”肃顺本不想开口,但是终于忍不住说了出来,其实一个小小的道台 跟他没多大的关系,只是他一向与看不惯恭亲王一力主和的政见,恭亲王既然奏请封黄仁仁为上京道台,自己何不给他泼些冷水。
恭亲王心中暗怒,突然拜倒在地:“皇上,臣闻,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此时正是国家多事之秋,用人之际,皇上应广纳天下贤才,为我大清所用,这才是大清之福。难道皇上忘了前朝 崇祯杀袁崇涣的故事吗?”
肃顺心中一惊,恭亲王拿袁崇涣做比方,不是比喻自己是那两名诬陷袁崇焕的前明太监么?他连忙跪下,磕头道:“臣对皇上忠心耿耿,天日可见,臣绝没有诬陷忠良之意,请皇上圣裁 。”说完将头埋在地下,呜呜的轻声低泣,他心中恨透了奕?,又道:“臣原本只是镶蓝旗副都统,默默无闻,托皇上眷顾,委与国家重任,皇上待臣恩重如山,若臣有任何不忠之念,臣愿 千刀万剐。”他一边轻轻的低泣,又偷偷的将脸别向站在身边的兄长端华。
怡亲王端华会意,肃顺本是他的同父义母弟弟,这恭亲王暗指肃顺不忠,岂不是指自己家族怀有不诡之心,他连忙上前:“恭亲王与皇上是亲生兄弟,关系自然近些,臣不敢指载恭亲王 的不是,但这个比方却有不妥之处,臣愿全家为肃顺做保。”
咸丰听在耳里,表面上心情不爽,其实正中下怀,他虽然只有三十多岁,但是近来体弱多病,恐怕时日无多,若自己死了,最有希望即位的便是自己的儿子和恭亲王,此时见端华两兄弟 与恭亲王反目,自是求之不得。他故作恼怒道:“这和你们忠心没有什么关系,大家都起来,下去歇息去罢。”
众人唯唯诺诺退了出去,肃顺擦开眼角的泪水,恶狠狠的盯了恭亲王一眼,在其兄端华的搀扶下,慢慢的跟随其后。
恭亲王奕?回到王府径直来到书房,他随手拿起桌上一本宋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翻了翻,又将它合上,他的脑子里仍想着南书房的情景,今天和肃顺翻脸的有些莫名其妙,平时虽然与他 政见不和,最多也不过不相往来罢了,可是现在不同了,斗争已经到了台面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他猛的站起声大声吼道:“叫王先生来,本王有事相商。”
京城仍是繁华如夕,酒肆茶楼中王公贵族们、文人骚客的欢叫声不输往日,朝堂上的政治格局悄然着发生着巨变,几道身穿蓝色长衫的飞骑骤然穿过永定门,数人分散开南方飞驰而去。
“黄队长,黄队长,这可是我王家祖传的砚台,当不了几个钱啊,您手下留情”上京县令王福荣衣裳不整的从衙门里追到门口,跟黄仁仁身后带着哭腔道,双手猛的扑住黄仁仁向前移动 的左脚。
“没王法了?”黄仁仁一脚将王福荣踢翻在地:“兄弟手里有些紧,只不过先借来用用,等我将来有了钱会帮你把这些东西当回来,你怕什么?”
“黄队长,你可怜可怜下官吧,下官十年苦读,上有老,下有小,还不容易熬到今日,您把砚台还我,这是我王家传家之物啊”王福荣又扑在黄仁仁脚上,死死的拽住。
这县令在街上撒泼打滚可是件希奇事,可过往的行人见到这场景竟无动于衷,显然最近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已经麻木了。
黄仁仁将包袱打了个结,背在身上道:“你若是再追上来,别怪老子不客气。”说完吐了口唾液转身便走。最近他手头紧巴巴的,虽然贷了浪漫国人二十万钱早被后勤长官和委托建厂的 赵本善分的精光,章士杰那老狐狸出人出枪劲头十足,一听到要钱便躲在浣月没有了回音。而叶卡娜每日消费的帐单非但没有减少,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黄仁仁只好三天两头带着李天右到 衙门里转一转,县令黄仁仁被他敲诈差点连官服都要卖了,于是黄仁仁便拿着几个大包袱,直接冲进去见东西就往里装,先搬回营中再找几个军士拿去当了换成银子,虽然麻烦,可是收入也 还可以,每天总有几百两银子的收入,今天黄仁仁又来王福荣所住的衙门后堂扫荡,不小心发现了个古色古香的砚台,便塞入包袱,没想到王福荣拿这个家伙当宝一样看待,一直从衙门后堂 追到门口。
此时已日上三竿,因天气炎热,路上行人稀少,黄仁仁背着大包袱越渐沉重,他换了个肩膀,继续在街道上做着匀速机械运动,他有些后悔早知道应该多叫几个士兵过来帮忙,这个念头 很快被打破,自己出去打劫也就算了,再拉上一票人,不知多少清纯的年青人要被教坏。
经过一个服饰店,骤然听见里面有人争吵,只听有人道:“鬼婆子,这四十两银子可便宜了你,你若不买,便将衣服脱下,老子还要做生意。
接着又是一阵女声水东语,黄仁仁听的清晰:“这衣服多少钱?您说什么?多少?”
“这洋鬼子说话怎么那么傻?”黄仁仁嘀咕着心想:“不懂华夏话不在租界老实呆着,硬要跑到上京来挨人宰。”黄仁仁会心一笑,突然又觉得这女声有些耳熟,于是换了换肩上的包袱 ,走入店内。只见一个店小伙不停的伸出四只指头口中念着:“四十两,四十两。”而站在他对面的竟是叶卡娜,她一脸莫名其妙的样子,不停的用英文重复着:“四两么?还是四十两?这 是丝绸质地么?”
黄仁仁心中升起一股怒火:“难怪叶卡娜每日寄来的帐单都要几百两银子,敢情天天单身跑来上京挨宰来了,穿在叶卡娜身上的旗袍最多也不过值四两银子,卖衣服的王八蛋竟开口要四 十两。”不及多想,一脚将仍不停伸着四个手指头的店小伙踢翻在地口中叫道:“四文铜钱卖不卖?”叶卡娜见是黄仁仁惊笑一声道:“黄,怎么在这遇见你?”黄仁仁心中恨她每日勒索自 己几百两银子,索性当作没有听见。
店小伙被踢倒在地上,口中尖叫:“你敢打人?”黄仁仁心中不爽,又不敢对叶卡娜发,于是放下包袱,对着店小伙就是一阵暴打,很快店内后堂钻出一四十多岁的中年连忙阻住黄仁仁 口中叫道:“且慢,且慢!”黄仁仁收起拳脚,对着那中年望了望,只见他身材矮瘦,头戴八角帽,身穿漆黑色的丝绸大褂道:“朋友可是驻守东城的火枪队黄仁仁队长,久仰,久仰!”这 黄仁仁搁三岔五的跑到骚扰上京县令王福荣,整个上京城消息灵通的都知道黄仁仁现在才是上京的大爷。
“老子就是。”黄仁仁见对方认出自己,更加嚣张双手插腰口中道:“老子明天就带人来拆了你们这些黑店,等着瞧吧。”中年人现出一丝惊慌忙道:“小人这店伙不知道这位小姐是队 长大人的朋友,还望包涵,这件衣服就送给小姐,当小人向大人赔罪。”说完又从怀中掏出张五十两银票:“万望大人莫怪。”
黄仁仁迅速将银票塞入怀中,脸上立马换上笑容:“好说,好说!”也不愿再在这里纠缠,拉上叶卡娜连忙出店。
“黄,你和他说了些什么?怎么买衣服非但不用给钱,他还送你银票?”叶卡娜在身后一脸疑惑。
黄仁仁道:“没什么,这是华夏人之间的关系,你是不会懂的。”
“我听说上京附近普陀山上的白华庵非常在华夏非常有名,我打算去瞧瞧,您要是有空陪我一起去吧。”叶卡娜道。
黄仁仁本不想答应,但又怕她在山上被人黑了银两,又找自己报销,于是连忙答应。二人先回营中放下黄仁仁从衙门里抢夺来的包袱,又雇了辆马车,驶出城外,向普陀山绝尘而去。
普陀山四面环海,风光旖旎,幽幻独特,被誉为“第一人间清净地”。山石林木、寺塔崖刻、梵音涛声,皆充满佛国神秘色彩。岛上树木丰茂,古樟遍野,鸟语花香,置身其中,仿佛人 间仙境,不过黄仁仁倒没有多少兴趣,沿路上香客络绎不决,二人沿着清幽小径,径直上山,走了半个时辰,一群古色古香的建筑赫然出现在二人眼前,二人加快脚步走到殿门,只见殿门紧 锁,四周并无一人。黄仁仁心中有些奇怪:“沿路上到处都是人,怎么这里一个人也瞧不见。”转身对身后的叶卡娜道:“小姐,这白华庵似乎并没有人烟,我们还是回去罢。”
叶卡娜并不死心,走到门前使劲的敲门叫道:“有人么?”门噶然而开,露出一慈眉善目的老年女尼道:“施主,本庵今日并不会客。”她抬起头望了叶卡娜一眼,全身一颤,双脚竟有 些哆嗦。
黄仁仁忙道:“不必惊慌,她是个洋人。”女尼顿了顿点头道:“二人既与本庵有缘,便进来罢。”说着打开寺门,先请二人进了,这才合上。
庵中风光倒也别致,二人随着女尼走入一佛堂,四周皆贴满了字画,大堂正中则立着一座三人高的弥勒佛泊金塑像。黄仁仁心想:“不知这佛像是不是镀金,如果不是镀金,岂不是发了 。”
女尼叫了小沙弥奉上清茶,这才道:“贫尼有些事要办理,两位施主可安座一会。”又说了声告罪这才离开。黄仁仁百无聊赖,这佛堂尽弥漫着一股香烛的味道,让他很不舒服。而叶卡 娜则一脸的兴奋,好奇的望望佛像,又兴致昂然的看着墙面的字画:“黄,听说马可波罗先生也喜欢收集佛像。”
“关我鸟事!”黄仁仁心里想着,体内却生出一丝莫明的烦躁,脑中昏昏沉沉,他本想用手按了按太阳穴,打起精神。却不想全身无力,动弹不得。正疑惑间,站在墙边的叶卡娜突然倒 了下去。“不好!迷药。”黄仁仁有气无力的说了一声,便晕了过去,摊倒在地。
佛堂中突然出现几道人影,其中一道人打扮的人道:“慧觉,干的好,明日教主祭法正需要一个洋鬼来祭天,将他们搬到密室去。”其余众人点头,七手八脚的搬起昏迷中的二人,吹熄 佛堂蜡烛,瞬间隐入黑暗。
黑暗笼罩着整个房间,寂静却比黑暗更加可怕,黄仁仁呻吟一声,悠悠醒转,他发现自己全身以被粗麻绳与叶卡娜背靠背的绑的死死的,“这是在哪?”黄仁仁开始整理自己的思绪,他 依稀记得和叶卡娜在佛堂突然昏厥过去,“对了!佛堂里应该被人下了迷香之类的药。”黄仁仁口中喃喃念着,心里不知如何是好。
“黄!您醒了,这是在哪里?我们是不是遇见绑匪了?”叶卡娜呻吟一声道。
黄仁仁这才想起绑在身后的叶卡娜,心中安定了一些安慰她道:“美丽的小姐,不要过分担心,上帝会保佑我们的。”他背脊贴着叶卡娜的后背,身子传来一阵温暖又道:“如果他们是 绑匪倒好些,也许出些银子就能将我们赎出来,如果是山贼什么的那可就惨了,自己小命没了不说,身后的叶卡娜估计要改行做压寨夫人了。”
“我在马可波罗的书里也看过他被人绑架的情景,不知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否与他相似。”叶卡娜倒一点也不害怕,语气似乎有些浪漫。
“靠!都这个时候了还提马可波罗那个老玻璃。”黄仁仁心中暗怒,一阵饥饿感传来,又不知自己昏迷了多久,心中有些焦躁。
“黄!您说他们会怎么对待我们?”叶卡娜见黄仁仁不答,又道。
“不知道。”黄仁仁丧气道,他实在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来路。
“黄!我为上次的向您道歉,每日都要您为我和我的仆人付帐单,等将来我回了国一定会将钱寄给你。”叶卡娜沉吟了会道。
“无所谓。”到了这个时候能不能见到明天的太阳还难说,黄仁仁可顾不得这几千两银子,他试图挣脱了会,身上的绳子反而绑的跟紧,只好放弃:“小姐,你是水东国人还是浪漫国人 ?”
“不!我是丹麦人,您听说过这个国家么?。
“丹麦。”黄仁仁念了一句,差点吓了一跳,他怎么也想不到叶卡娜是个丹麦人,其实在他的印象中,对这个小国根本就没多大的概念:“听说过,你们国家有个叫安徒生的家伙吧?据 说很会写故事,虽然那些故事只能骗骗小屁孩。”
“安徒生。”叶卡娜仔细咀嚼了会,这才道:“没有听说过,他写过些什么故事?”
黄仁仁心叫不好,仔细的算了算,现在安徒生虽说以有四十多岁,不过貌似还是默默无闻。
叶卡娜见黄仁仁又不说话,道:“安徒生写过什么故事,您能跟我讲讲么?”
黄仁仁在脑海中仔细回忆,终于想起安徒生的一篇《丑小鸭》,于是开始娓娓动听的讲起故事来:乡下真是非常美丽。这正是夏天…从墙角那儿一直到水里,全盖满了牛蒡的大叶子。最 大的叶子长得非常高,那些鸭蛋一个接着一个地崩开了。“噼!噼!”蛋壳响起来。所有的蛋黄现在都变成了小动物。他们把小头都伸出来…”。
“丑小鸭怎么变成天鹅了?它的妈妈不是鸭子么?”叶卡娜听的迷迷糊糊。
“鬼知道!也许他妈妈背着他丈夫跟天鹅有一腿也不一定。”黄仁仁一本正经的解释道。
门噶的开了,一道光线从门外透了出来,黄仁仁见门口走出几个身穿道袍的汉子手中拿着各种武器冲了进来。
其中一个看似年长的人道:“教主有令,押这两个鬼子去祭堂。”众人应诺,七手八脚的叫二人解开绳子,将二人推搡着带出门口。
众人穿过几道长廊,来到一个大殿,殿中黑压压的竟有上千人众,个个跪拜在地上念念有词,大殿的正中仍是一个弥勒佛像,佛像下坐着一身穿华丽道袍的矮子,正对着众人,闭目养神 。
押二人前来的年长青年拜了一拜朗声道:“尊教主令,红毛鬼带到。”弥勒佛像下的矮子睁开眼睛:“带上来。”
众人应诺,又将二人推搡着带到那教主身旁,黄仁仁这才看算看清这个所谓的教主尊容,长的倒还有些仙风道骨的样子,只是一个酒槽鼻横在脸中间,破坏了整体格局。
教主打量了会黄仁仁、叶卡娜二人一眼,突然转身向上千拜在地上的信徒吼道:“天道不公、生灵涂炭、满清敲膏吸髓、红毛肆虐神州,弥勒尊下、顺应天命、驱除鞑虏、复我汉家江山 。”此言一出,无数教众站起身狂乱的叫着:“驱除鞑虏、复我汉家江山…驱除鞑虏、复我汉家江山”。
黄仁仁听的目瞪口呆,这口号怎么跟孙中山先生提的差不多,这年头的乱党怎么都跟驱除鞑虏沾点关系,难怪满清气数已尽,恐怕再来多少变法维新都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他见那些教众 个个眼睛发红,心中不禁害怕,看来今天是躲不过此劫了,他望了望身边的叶卡娜,叶卡娜不知对方念些什么,但是见这奇怪的场景倒有些莫名其妙的兴奋,显然还不知道眼前的这些家伙会 对她的生命造成威胁。
教主做了个禁声的手势,大殿内又开始恢复安静,复又开口道:“生火,烧红毛鬼。”接着殿下便有四,五人点燃火把,掷入墙角一个青铜大鼎中,鼎中可能放了些柴火、硝石之类的物 品,遇火立燃,片刻功夫,整个青铜大鼎被烧的通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