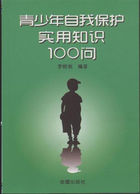"如果我的记忆还正确的话,根据过去我在派对里混的经验,经过昨晚之后,你们一定饿坏了,"他说,"谢谢,我不用了。你们男孩子要吃呀。把东西都吃光。"
他坐在那里咧开嘴笑,在折磨我们的过程里持续地抽着烟。尽管气温很高,他硬是不准我们开一扇窗子。我们在劫难逃。他的怒气从昨晚起,似乎已经烟消云散,可是让他生气一场,总得付出高昂的代价:把早餐吃掉,好供他取乐,似乎就是我们跟他胡闹之后,必须要偿还给苏瓦雷滋的债。
那两颗蛋瞪着我,像极了一双逼供的眼睛。血肠加了太多的香料。我勉强把全部的东西吃完,已经比法比恩强得多了,他吃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口齿不清地说:"我干吗要这么听话呀?"然后再一次飞跑去吐了。
熬到酷刑结束之后,我被安排搭公交车回家,再搭货梯到我们公寓的楼上,直接上床,倒头就睡。
07
有时候让人相信他们想相信的也没什么不好。真实的人生有时候是很令人失望的。
一个礼拜过去了,法比恩几乎没有跟我讲到话。我猜想他是为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感到尴尬,我想等他心甘情愿的时候,我们就会像以前那样常常碰面。结果事后证明他那时捉摸不定的心态并不是针对我。星期三的科学课,他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通常我们会随机地分成小组做实验,那天法比恩和薇芮娜.赫米斯分在同一个小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在实验室的另一头,我所知道的是一声爆炸和几声尖叫,但是后来我问薇芮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几天他好像中了邪一样,"她说,"我们才一开始做实验他就心不在焉,先是吸入氨气,然后又望着窗外的天空喃喃自语。真是头壳坏掉了。我根本不想理他,但是他就在我的耳边一直讲一直讲,我们正在做实验耶。都是他害我得了个鸭蛋。"
"你会赢回来的啦。他到底在喃喃自语些什么?"
"他一直重复讲'你看到她了吗?',真是怪胎。"
事情还不只这样。我听说,放学后在一场足球比赛里,他和某个家伙打了起来,用他的石膏夹猛敲那家伙的头。我也曾经从很远的地方,看到他一个人在操场的边缘,茫无头绪地大步走来走去,注视着山岭,仿佛从来没有看过它们一样。
星期五的下午,我们终于在学校的门口碰面,等着一起被接回家,我单刀直入地说:
"你不要再那个死样子好不好,你告诉我怎么回事嘛?"
他不理我。
"怎样啦?"我说,"你到底怎么了?"
他回答里的敌意吓了我一跳。"什么你到底怎么了?你为什么只在星期五的时候关心我到底怎么了?你是想我再请你回我家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