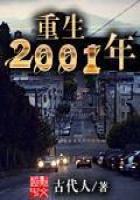刘宝库一脚将妈咪踹下床,许俏俏看见一个白色的物体呈抛物线下落,只听到皮球挤出气体的嗞嗞声音。
“它可能死啦。”她拉亮室内大灯。
“死了好,作(闹)人。”他绝情地说。
许俏俏白亮亮的一片下了床,像一片月光洒向妈咪。她嗔道:“踢球呢你,妈咪受得了?”
妈咪一时的昏迷,很快苏醒过来,它已经在她的怀里,贴在光滑的皮肤上,它喜爱她的肌肤弹性、光滑而温暖。
许俏俏抱妈咪走向床,她要给它以关怀,带它上床。
“许俏俏你干什么?”刘宝库的心情撕破纸一样坏,他容不得床上除了许俏俏以外的第三者。
“狗通人气,你虐待了它,及时给它关爱,它不记仇的。”许俏俏抱着妈咪离床沿很近了,她讲着她的理论:“家庭成员的矛盾最易化解,亲情是润滑剂。”
刘宝库再次飞起一脚,把妈咪从许俏俏的怀抱踢出去。
“做吗你?”许俏俏愤怒了。她第一次见刘宝库除了在她身上以外的特别粗鲁,生活中的他像只蟑螂在人前小心翼翼,暴力妈咪两次她不能容忍,数落道,“你心不顺拿妈咪抓邪火气(毫无起因的怒气),应该吗?”
“它老啃我的脚。”
“平常你教唆妈咪舔你的脚,还舔你那东西……”许俏俏动气语言就锋利、挖苦,“你高兴叫它舔这儿舔那儿,口喊着舒服死啦。不高兴就一脚踢下床,这么说哪一天你心不乐,也把我踢下床。”
刘宝库觉得问题严重了,许俏俏心疼狗把事情想复杂了。到什么时候,他也不会像踹妈咪一样踹她下床。她曾和他开玩笑说,哪一天扔你乌鸦大晒蛋。他真害怕了,许俏俏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滋润,说她是雨是空气都成,没有女人滋养男人就枯萎。
“俏俏,你别生气。”刘宝库掀起被子要下床去抱妈咪回来,说,“我给它道歉。”
妈咪躲在自己的宿处——专门为它量身制做的床上,许俏俏为做这张床动番脑筋,仿造家乡育儿放在炕上的撼车子,妈咪舒服舒服地睡在里面,它欣赏挂在床上方的风铃,叮咚叮咚的音乐声甚是好听。
“算啦,你让它安静一会儿。”她说。
刘宝库重新回到床上,许俏俏脸侧向外边,亮给他大块的后背。他没去碰他,今晚根本没心情碰。
刘宝库的坏心情事出有因,专案组找他,海小安和他谈,向他要一个情况。
“卐井什么时候停产?”海小安问。
“半年前。”刘宝库将时间朝前推移,说。
“我们要具体的时间。”海小安说。
“封井很久了,一下子想不起来。”刘宝库说,“嗯,容我想想。”
“那你慢慢想,把最后一班生产记录给我们。”海小安说。
刑警盯上卐井,不能不使他惶惶然。警察出身的他,明白破案的套路,专案组问卐井的情况,说明侦查的目标是卐井。
“姐夫,专案组开始调查卐井……”刘宝库头一次直接给海建设打电话,一切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对方的态度硬冷。
“大惊小怪什么?”海建设训斥道,“这么点风浪你就坐不稳钓鱼台了,今后怎成大事。”
“是,是。”刘宝库甘愿挨训的样子。
“按我说的去做,不要轻易给我打电话。”海建设说。
突遭冰雹袭击一样,刘宝库十分破败。他觉得海建设又是老板而不是姐夫,亲情显得那样苍白无力。红罂粟酒店的良好感觉再也找不到,口气的生硬使他接受不了。
“宝库,我想……”许俏俏突然转过身来,主动地说。
“我很累。”刘宝库婉转拒绝,没彻底拒绝,接受了她伸过来的一只胳膊,下巴颏抵了上去,说,“腰有些酸。”
“我给你按摩。”她说。
刘宝库弓身虾米在她的面前,她的手很有力气,穴位也找的准,捏鼓一阵后,他觉着舒服,有了被妈咪舔的舒服感觉。她通过他哼哼的节奏、声音大小来判断他的舒服程度,套他话的最佳时机是他舒服的时刻。到了,她盼望的时刻到了。
“宝库,我看你是给警察闹的。”她说。
“算是吧。”
“他们抓住李作明的车祸案子不放,车祸就是车祸,非在鸡蛋里挑出骨头?”她为巩固他的舒服,做了一个在他们之间是正常的动作,而在外人看来不雅的动作。
“哟,你撩扯(引逗)它,精神了怎么办?”他说。
“精神了岂不更好。”她说。
腰椎按摩在继续。她说:“你干脆出外走走,先躲一躲。”
“警察是线儿蚂涕(水蛭)盯上就没好。”刘宝库说,“你不知道海小安,他是刑警中的精英。”
“干什么?”
“破案啊!盘山的几大血案都是他破的。还有梅国栋,局长挂帅,有我们的好吗?”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许俏俏说,“你怕的没有道理。”
“是不该怕。”刘宝库自知还是说多了,收回话来,说,“明天专案组找矿上中层谈话,你也在找的人之中。”
“我会谈什么。”
“专案组说一个不落的找谈一遍。”刘宝库说,“你正常回答就成。”
真是灯下黑,刘宝库嘱咐下属,重点人单独叮嘱,可对许俏俏什么都没说,认为她绝对可靠,谁出岔她出不了。事实上,中层的人中真关注李作明的就是许俏俏。她潜伏在刘宝库的身边,说她卧底、眼线、间谍……都行。许俏俏关注李作明,继而是卐井,她要揭开秘密,从这一点上看,警察和她殊途同归,目标是一个。
忽略往往是身边、枕边人,刘宝库从没怀疑过许俏俏,自然就没在意她。他没注意她的眼神,总有一种探寻的东西。
海小安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一个神秘人出现。
“你是海小安吗?”神秘人电话里问。
“是,你是谁?”海小安问。
“暂时不能说。”
海小安问:“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知道卐井的秘密。”神秘人说。
嚯,这倒是天大喜讯,专案组渴望的是这样的线索。海小安赶紧接上茬儿,说:“请告诉我们。”
“不行。”神秘人说。
“那你……哦,条件?你说。”海小安说,“什么条件你讲。”
“见面谈。”神秘人停顿,说,“我见你再谈,只见你一个人。”
“可以。”海小安略作思忖。
“鲇鱼河有个汊子你知道吗?”神秘人问。
海小安对鲇鱼河还算熟悉,过去有两起命案在该河发生,他率刑警一寸一寸地丈量了鲇鱼河,多少道弯多少汊子了如指掌。流经罂粟沟这段,只支出一个河汊子,叫蛾眉河。不是因“如螓首蛾眉,细而长,美而艳”得名吧,又为何起了这么个脂粉气的名字,无从考究。蛾眉河像在水中裸浴给人看见的少女,慌忙逃入林莽间,海小安不知道它逃到哪里。据说,它通向白狼的领地,罂粟沟有白狼群存在的记载。
“蛾眉河你知道吗?”神秘人又问。
“知道。”海小安说。
“你想听我说,就在后天晚上8点钟后,你沿着蛾眉河走,我会在河边等你。见不到我你就一直往前走,别停脚。”神秘人说。
“喂,喂!”海小安听到对方关掉手机。
接神秘人电话时,李军一直在海小安身边。
“李军,喊小王他们上楼,我向你们通报一个重要电话。”海小安说。
“我去叫。”李军下楼去。
小王他们在招待所的院子里打羽毛球,每天海小安赶鸭子似的哄他们下楼,活动活动筋骨,也活跃活跃思维,一切为了精力充沛投入破案。
“小王,海队叫你们上楼。”李军走了捷径,到二楼的阳台上喊。
小王说才五分钟就结束,是不是海队看错了表。
“上来吧。”李军的身影在二楼的阳台上消失。
也就在小王望李军时,一个发亮的东西一闪,换一个角度看不到,再调到刚才的角度又看到发亮的东西。
“海队,”小王最后一个上楼,进屋便说,“招待所有问题。”
“噢?”海小安惊讶。
“我看见发亮的东西,在二楼的阳台上……”小王讲了一遍自己的发现,推测道,“有人安装了隐蔽探头,暗中监视我们。”
“危言耸听。”李军说。
小王想和李军争论,海小安说:“大家听我说一个电话,一个神秘人打来的。”
什么样的电话打给刑警支队长,再由他转述给办案警察?海小安传达了全部通话内容后,大家才觉得神秘人的出现有多么重要。
“我去见神秘人。”海小安说。
“海队,不行!”
“那可不行,海队。”
专案组的人异口同声地反对。
“嗬,你们都反对?”海小安说,“李军,连你也随声附和地反对。”
“不是随声附和,是真反对。”李军说。
“好,那你们说说反对的理由。”海小安说。
刑警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由李军来回答,他说:“神秘人打来神秘电话,再到神秘地方去见面,是不是个陷阱?圈套?”
“正是全神秘,才有必要去见一见。”海小安说。
“神秘人身份不明,动机不明。”小王说。
“三神秘两不明,你们谁还有高见?”海小安问。
一位刑警说:“一危险。”
“啊,三神秘两不明一危险,你们都改行别干刑警了,去机关写材料,三二一,一二三的,哪那么的按部就班。”海小安口气夹杂着责备。
气氛有些凉,刑警默然。
“我原以为自己多年辛苦带出来一群老虎,呵,一帮耗子。”海小安恨铁不成钢,他希望他的部下生龙活虎,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别生气,师傅。”李军改亲切一点、随便一点的称呼,说,“我们实在是为你安全担心。”
“你为我担心,谁为那些死去的冤魂担心。”海小安动情,话音带喘息,他说,“李作明的车祸,郭德学被分尸,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都看着我们盘山刑警,希望给他们一个说法。”
气氛朝严肃行走。
“将来卐井的秘密被揭开,说不定会是什么样子。”海小安语言豪壮起来,说,“我们是刑警,刑警意味着随时都有可能牺牲。”
谁也阻止不了海小安去见神秘人,李军提出建议:“我们查一下神秘人的手机号,看看机主是谁。”
“李军你去移动公司……”海小安说。
李军拿着号码找到移动公司,是本地推出的“动感地带”卡,持卡人叫马光辉,并有身份证记录。
回到公安局户籍科,查找到该人一年前已去世。
“有两种可能,现持卡人冒用了马光辉的身份证,再就是马光辉生前将手机转让给持卡人。”李军分析说。
“我们不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李军你明天催刘宝库,一定让他交出卐井的最后一班生产记录。”海小安安排明日工作,说,“小王继续拿着郭德学的照片,在矿工中辨认。”
“海队,提点建议。”小王吞吞吐吐。
“说吧。”海小安准许。
“明晚你去见神秘人,带上两支枪。”小王说。
直到这时,海小安才觉得有必要对部下下个命令,他说:“我见神秘人的事你们不准对梅局说,谁说了,卷铺盖给我走人!”
丛众和海小全沿着蛾眉河走上去,他们去鬼脸砬子煤矿没从正门进入,选择钻林子,是丛众的主意,她不愿让更多的目光瞅自己的左臂,黑纱会引起无聊人的无聊猜想。
宋雅杰是盘山市第一个注射死亡的人,完结一个生命要比孕育一个生命简单,几毫升致人于死地药物扎进血管,她感到身体如拆毁的家具散花开去,如云一样轻飘起来,而后进入被人们称为隧道的世界,痛苦、眷恋、爱和恨统统离开,她变成纯物质的东西,石头、树木、空气、尘土……真可谓万事皆休。
丛众捧着变成灰烬的母亲,走向鲇鱼河,让小河流走母亲。世间没有脚和翅膀能翻山越岭的是水流,还有风。
所以她选择送走母亲的载体——河与风,一部分骨灰扬向天空,她扬撒骨灰的情景让人撕肝裂肺。
“妈,走好啊!”
“如有来世你再做我的妈妈!”
丛众的泣呼诉唤,揪出海小全的眼泪。
“妈你放心,我一定找到继父。”丛众扬撒完最后一捧骨灰,对着远去的母亲说。
蛾眉河流淌了一段变窄,倘若从高处俯瞰这段河流,细而长如螓首,满河飘着秋天的落叶,令人怜惜。
宋雅杰的执行在上午10点14分,那天天气很好。她望眼透进监房的阳光,那情形和郭德学走下卐井一样,都是最后一眼。谁也说不清楚踏上死亡之路的人为什么仰首望天空望太阳。她望眼太阳,低头望自己的鞋,那上面别着一片鲜红的树叶。
“众儿,”宋雅杰恳求女儿,说,“给妈弄一片树叶来。”
“树叶?”丛众迷惑不解。
“别在我的鞋上,它带我走。”
丛众到山间选择树叶。
罂粟沟的山上有上百种树,有的叶子已在风霜中落下,有的正在飘落,也有的还顽强在枝条上。
是从地上拾一片叶子,还是到树枝上去摘。丛众沉思,母亲上路时为什么单单选择树叶带,而且是一片呢?她寻找到有关词汇,希望从中得到诠释。
一叶知秋,落叶归根,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叶子啊,母亲为什么选择了你?
百思不得其解,丛众凭自己对母亲的理解,最终选择了一片如血的红叶,它属枫树的一种。
蛾眉河面出现片片红色,枫叶点缀其间。
“母亲带片红叶走的。”丛众沉痛地说。
海小全凝视漂移的树叶若有所思。
“我妈去追赶树叶。”她无限伤感。
蛾眉河流入茂密的矬树林后,他们沿着山间小路攀登上去,最后路也钻进树林,消失得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