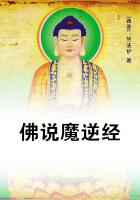野杏村的大户人家张百川家的一切麻烦是在苏芹凶狠的脚下猛然迸发的。朦朦的天色中,苏芹面对着张百川家夜一样漆黑的大门,抬起母鹿般结实的腿,踢出个炸雷似的裂响,那个裂响脆声声地传扬着,截断了野杏村公鸡们骄傲的报晓声,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便在公鸡的哑然中染遍了村落。
那是个阴冷的早春,冰冷的风携着整个夜晚的凉意贯穿进辽西走廊的清晨。野杏村朴素的鸡鸣逐渐地唤醒了村落,村中首户张百川家的那一溜孤独的二层小楼无依无靠地立在村子的极东端,混饨的天光缓慢地恢复着小楼原有的色彩,而那上下两排齐崭崭黑暗着的窗口却不断地吸收着小楼诱人的辉煌。这时的村落还很寂静,惹祸的苏芹还没有来到小楼前打扰公鸡们所晓的自由。
小楼的缔造者张百川并没有享受几天小楼的舒坦。这个时辰里的张百川正在辽西走廊上的那个日益繁华的海滨城市率领数以万计的建设大军,从一砖一瓦中积累财富。张百川的妻子儿女们日复一日地留守在小楼里,心安理得而又不厌其烦地享受着日出以后的生活。小楼极有层次地分出了几处套楼,套楼里依次住着张百川的老婆老甜、长子大江、长女三翠。待娶的四海把持着一套楼独住,倔犟的二河同老爹张百川闹翻了脸,举家搬迁,已是人去楼空。老疙瘩五湖身高刚满八十公分,本来就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张百川设计楼时也就把他忽略了过去,没有给五湖的将来留下一寸的安家立业之处。尽管那时的五湖距公民的资格尚有二年之差,也应该算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了,别人可以歧视五湖一层不变的顽童样子,可当爹的怎么也不应该拿儿不当儿。好在五湖人小心大,让人取笑惯了,也就不懂得和爹妈计较。
喜欢计较的是张百川的二儿媳苏芹。张百川家那几日许多难堪的乱子就是从苏芹那次不饶人的嘴中惹出来的。
野杏村的鸡鸣叫得透彻的时候,村子里除了这座小楼里的人们差不多都已经醒得透彻。苏芹躲过丈夫二河的注意,从自家的后门溜了出去,在逐渐明朗的天色中绕到婆婆老甜的大门外。小楼里懒散的安静就这样被苏芹的脚轻松地给踢得破碎了。苏芹抬起脚踢门的时候,面对漆黑而又阔大的铁门没有丝毫的犹豫,那只母鹿般结实的脚在半空中蜷缩一下,脚掌便有力地弹向铁门,如雷的炸响便果断地震荡了起来。院子里的几只狼狗被震荡得异常愤怒,挣动着铁链子,如狼似虎地狂叫。苏芹的脚被狗的狂叫惹得更加恼怒,携着气愤,接二连三地踢向铁门。铁门哆哆嗦嗦地震颤着,清脆而又坚决的声响一下紧过一下,伏在云层里懒洋洋的太阳似乎也忍耐不住,探出惊讶的脸,望着怒气冲天的苏芹。野杏村的天空也就在那一刻明朗了起来。
苏芹发怒的原因并没有后来村里人猜测的那么复杂,不过是人争一口气而已。苏芹记得,当初住在小楼里的时候,二河三天二头张罗搬跳出小楼另立门户单家独过。那一次张百川乘着蓝鸟匆匆回来,二河见到爹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搬出去”。张百川审视着二河,拧着眉头,暴跳如雷地训斥:“你他妈的有病呀,老子把窝造得比部长都宽绰,你却惦着住狗窝。想滚就滚,一辈子也别回来。”二河讨厌在老爹盛气凌人的鼻子底下胆颤心惊地过日子,更不习惯小楼里的懒散与没有节制的争吵,拧着脑袋领着老婆孩子搬了出去。二河没有理解到,自己搬出小楼是给老爹张百川的脸上抹黑呢,张百川在外边名声显赫,广交四方,在家里连自己的儿子都维持不下。
苏芹是不愿意搬出去的,大家的日子有帮有底,多靠一天也就多省一份心,二河瞪圆了眼珠子高低不在大家里混,自己给自己扫地出门搬了出去。如今婆婆老甜果然拿着老爷子的鸡毛当令箭,把他们二河这一股人家忘得个一干二净,老甜到城市里找了一趟老爷子,就给大儿媳春雁弄来了金镏子,给三翠戴上了金手链,苏芹再不济也给张家生个人见人爱的孙子,怎么会落得个屁也没有呢。本来,苏芹和二河每年都能喂出几百口猪,挣来的钱时常成千上万地数,不至于让金首饰气得眼睛发蓝。钱多钱少是小事,苏芹争的是一口气,一个理,她必须让婆婆记住儿子二河在这个家里应有的地位。
老甜那套楼的屋门终于开了,老甜揉了揉松弛的眼皮,打了个悠长的哈欠,走了出来。几只守候在门口的大花鹅,迈着绅士般的步子,从老甜的脚旁钻进楼里,随心所欲地扇动几下翅膀,从容不迫地把一滩滩温热的屎留地门厅的地板砖上。老甜熟视无睹地看了眼鹅,并没有驱赶的意图,继续打着哈欠,一截没有系牢的裤带便悬了下去。老甜提了下裤腰,走了出去,裤带在她的腰间无拘无束地荡来荡去。
苏芹的脚继续节奏分明而又铿锵有力地撞击着阔大的铁门。老甜还得意在自己能给儿女争取来金饰品的喜悦中,没有在意谁会这么凶猛地踢门,边开门边习惯地骂:“谁呀?我不心疼铁门,你还不心疼蹄子。”
大门“吱吱呀呀”地闪向两旁,理直气壮的苏芹便豁然亮出。狂叫的狗们认出了打扰它们的苏芹,无趣地扭回狂暴的头颅,伸出舌头,舔着嘴巴,惭愧地卧了下去,不再吱声。苏芹的脸色和刚才的天色一样的阴沉,她跺了几下自己的脚,说:“我说咱家咋出不来好事呢,原来都是长了蹄子。”
老甜的眼神呆愣了一下,直直地瞅着来者不善的二儿媳妇,觉出了刚才的话有些冒失,脸上显出了不自然。老甜的心里琢摸着,二媳妇哪来的这么大劲儿,哪个庙里的神得罪了她。苏芹横眉立眼地紧盯老甜的眼睛,一丝不放。婆媳俩一见面就呈现出这种难以融洽的尴尬,老甜努力让自己眼神活泛起来,避开苏芹刚才的话锋,问:“进来吧,进来吧,小青呢,咋没把我小孙子带来?”
苏芹露出了不屑一顾的神态,撇着嘴,说:“你还有孙子呀?你还惦记小青呀?二河都不是你的儿子了,你咋还会有孙子呢。再说了我们长蹄子的人,咋敢叫你妈叫你奶呢,我们娘们在你眼里连人都不是。”
老甜的眉疙瘩渐渐皱紧了,自己再不起眼也是婆婆,媳妇就是再有理也不该这么放肆,干啥不阴不白地使脸色。老甜的脸阴沉下来,说了句“不进拉倒”,伸手就去关大门。苏芹的右脚再次抬起,有力地踹向老甜关了半截的门,把老甜的手震得麻酥酥的。老甜气愤地骂道:“你的爪子折了,干嘛总抬蹄子。”
苏芹没有发怒,苏芹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站着,她的脊背倚在门框,双臂抱在胸前,瞅着老甜的发怒,嘴里露出了清冷而又干燥的笑声:“你说得对,我哪有资格长脚呀,我们一家人只配披驴皮,给驴蹄子穿金戴银那不是糟踏吗,金镏子、金链子套在人模人样的身上,也能让你体面些,戴在驴蹄子上算是啥?”苏芹越说越气,咬着牙,语调尖酸得像山枣一样:“我瞅你长得也是人模人样的,咋也说起了驴子话?”
老甜愣住了,老甜骂人的技巧是不亚于能工巧匠的,只是她没有料到苏芹竟敢骂她,她一时没有反过腔来。老甜顿了片刻,她心里很纳闷,苏芹的话明明是暗指给春雁和三翠戴首饰的事儿,这事儿咋让二媳妇给摸着风了?老甜本是想把苏芹骂得个狗血喷头的,又一想该摸一摸苏芹的底,就忍住了挨骂的难受,缓和了一些语气。老甜说:“妈这么大数了,这么多年当驴当马地拉扯孩儿们,不也过来了,驴就驴吧。妈的肠子没有几个弯卷,有啥不愿意的事儿,直来直去地说。”
苏芹嘲笑一声:“还用说吗?和尚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老甜一副浑然不觉的样子:“妈是喝糊涂汤长大的。”苏芹的脊背从门框上弹出来,伸出手直截了当地指着老甜:“春雁是你大儿媳妇,三翠是你宝贝闺女,老爷子不认二儿子我不管,他可没不认二儿媳妇,我哄得小青对你们老俩口又亲又抱,哪一点对不住你们老张家了?干嘛一样的河冻出两样的冰来。一个镏子值不了太多的钱,哪怕让我戴一天,也让村里人知道张家不只有一个儿媳妇。弄得二河都不愿姓张的份儿上,你们高兴呀?”
老甜被苏芹的这番话攻得有些心虚,她思忖着:从老爷子手里抠出这两件金货没有旁人知道呀,就是苏芹多得满脊骨背心眼儿,也瞅不见别人心里的小六九呀。老爷子的嘴比门都严,不可能和苏芹通光,会不会是春雁这个实心眼儿的一高兴说漏了嘴?这也不可能呀,春雁心眼儿再实也没有傻到卖自己的份儿上。老甜想来想去,就是没能想出个谱来,怀疑来怀疑去,就差怀疑自己了,老甜坚信自己从来不做傻事。
事实上,老甜的固执已经为自己铸成了不可挽回的纠葛,她早已把自己得意忘形时的那个小细节忘得个一干二净,野杏村中被金货照耀得心里发痒的妇人们却把这个细节牢牢地抓在心中,不错时机而又添油加醋地传递给正在抱怨没有得到家中财产的苏芹。妇人们很喜欢热闹,看大户人家闹别扭这比看戏更过瘾,戏再好也是假的,这不花钱还是真刀真枪的好戏谁不想多看几眼。于是苏芹就知道了老甜下轿车拍大腿的细节。
老甜丝毫没有感觉出儿媳妇的闹腾是自己的疏忽造成的。老甜想:苏芹是听风就想雨地生事端,我硬咬牙根不承认,她能怎么着,还能伸手到我肚子里把话掏出来?孙猴子再闹腾也扳不动如来佛的手指头,我再赖不济也是她婆婆。老甜的愤怒再也忍耐不住了,她“叭嗒”一声撂下了脸色:“二媳妇,说话得拍良心,你缺钱,我可以帮你向老爷子伸手,缺东少西可以到楼里去取,搬出去后悔了可以搬回来,干嘛讹我这个没能没水的老太婆。”老甜越说越气,伸手扯住苏芹的衣袖子,大声说:“走,到楼里去,咱找春雁对质,找三翠对质,你不是想弄明白吗,跟我走。”
苏芹挣开老甜的拉扯,用力地拍打着老甜扯过的衣袖,好像老甜给弄脏了似的。苏芹说:“我不是你们家的狗,拉来拉去的,我是你们家的儿媳妇,戴金镏子是你当婆婆份内的事儿,有春雁的就不应该没有我的。”
老甜的脸猛地变了卦,眼睛里睁出了一圈不同寻常的白眼仁。老甜的双手有力地掐在腰上,唾沫星和嘴里的话一同喷射出去:“反了你,没大没小了你,你公爹往我肚里种金子了,说屙就能屙出个镏子链子的,想编排也不能太离谱儿。门让你踹了,婆婆也让你给作贱了,孙猴子大闹天宫也得有个头哇,今个儿你不当着全家人的面给我说清楚,别想出这个家门。”老甜猛地将身扭回,“咣当”一声关了大门,死死地插住了门的铁栓,背靠在门栓上,看着被自己关进院里的苏芹喘粗气,随后便将渺视的眼光抬高,目空一切的脸仰向小楼的上方。
这时候的小楼已经在明朗的阳光中清清楚楚地显出了本相,黑暗的窗口在阳光的压制下脆弱得不堪一击,窗帘的色彩很无奈地暴露在阳光下,小楼的金壁辉煌再度玄耀出来。老甜的喊声升扬上去,开始在小楼间回荡:“春雁,你给我滚下来,二媳妇说我给你戴上了金镏子,你拿下来给她看看,让她的狗眼睛亮堂亮堂。”
苏芹扭过脖子,不安份地翻着眼珠着,阴冷的怪笑从鼻孔里无拘无束地喷泄出来。苏芹说:“别这么费劲地练节目了,春雁她会演戏吗,你不是不明白吗,我给你演完戏你就明白了。”苏芹做出了一种扭扭捏捏的怪态:“前几天呀,我去城里找一个挺能耐的老爷子,我是坐着什么鸟回来的,我坐在那个车里呀,一点尘土也没有,我下了车就拍大腿。我拍大腿是我愿意的事儿,不拍大腿谁能看到我戴金镏子挂金链子呢,不拍大腿谁又知道我大儿媳妇和三闺女孝顺呢。”苏芹说到这里就停止了扭动,脸色也变得更加难看,冲着老甜说了句难以承受的话:“我真是个老不知好歹的东西。”
老甜直呆呆地看着苏芹,她后背牢牢地靠在铁大门上,怅然若失地从记忆的深处寻找出了那个令她无限烦恼的小细节,那时,她确实被虚荣烧得得意忘形,拍大腿纯粹是下意识。
春雁早已站立在二楼的窗台前,将窗帘欠开一道缝,眼睛盯着婆婆和弟媳苏芹的对峙,耳朵听着她们的争吵。当争吵的内容牵扯到金镏子的时候,春雁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嗓子眼有了一股咸咸的味道。春雁立马把金镏子从手指上艰涩地褪下来,认真地掖藏好。春雁是个不摊事儿的人,她想,自己也没戴着金镏子街前街后臭显摆,苏芹咋会顺风寻味追来了呢?
春雁的丈夫大江还赖在床上,大江每天的起床差不多都是苏芹唤起来的,还要给大江穿衣服。大江是个永远停留在孩童时代的男人,他时常日复一日地给春雁讲他的那个夜复一夜循环往复的恶梦,有时被恶梦惊醒,伏在春雁的怀里痛哭不止。大江时常说:“那两个人飞下来了,炸楼了,满天都是血呀。”春雁便再一次哄孩子似的拍着大江,让大江别怕。
阳光从春雁欠开的窗帘缝间狭长地斜射进来。大江猛地从床上坐起,瞪着眼睛张大恐怖的嘴,愣愣地说:“爆炸了,爆炸了。”春雁便重新回到床前,抚摸着大江。大江说:“你搂搂我,我害怕。”春雁很敷衍地搂着大江,心事重重地说:“你这辈子就不会做别的梦吗?”大江依进春雁的怀,追求着无止无休的保护,很怯懦地摇晃着头颅。
老甜和苏芹依然僵持在院子里,眼睛喷射着毫不相让的光芒。院中间的狗们很无聊地趴在地上,挑起懒洋洋的眼皮,无精打彩地瞅着婆媳俩互不相让的争吵。楼上的春雁记得婆婆给她金镏子的那天,她正在院子里整理几个畦子。那一日的阳光已不吝啬,很体面地释放些温暖,春雁蹲在那片新翻的土前,准备在春分那日种上一些紫皮蒜。院里被鸡鸭鹅狗挠了一冬,早就不成个人家的样子了,春雁不去收拾,能有谁去收拾呢?老甜的那一双充满自信与力量的脚就在那一天的那个时刻停在了春雁的身后。老甜用充满温情的语调叫了声春雁,唤春雁到自己居住的楼里去。老甜携着春雁的手进了楼,眼睛释放着仲春才会有的暖意,喜滋滋地看着春雁,催促着春雁把手洗干净。春雁生就一双粗大的手,也就没有必要娇惯了,草草洗过,急着回到老甜面前。老甜笑吟吟地叮嘱,要把手洗干干净净,干净得像剥了皮的葱,婆妈要让春雁的手配得上住着的楼。春雁一一照办了,老甜便毫不迟疑地将指头上的金镏子褪下来,细心地套在春雁的指头上。那枚令苏芹发怒的金镏子就这样属于了春雁。
老甜继续倚在铁门上与苏芹对峙,既然破了脸,老甜豁出去也要弄到底。老甜的表面很强硬,硬得坚不可摧,可自己的心尖像裂开了似的疼痛,她觉得无形的血珠子正从她的心尖上一滴接一滴流进冰凉的腹腔。老甜开始后悔自己多余枉费心机地从老爷子手里往外抠这两件金货,自己同二儿媳争吵了这么一阵子,楼里的儿女们瞎了聋了似的没有一个出来帮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