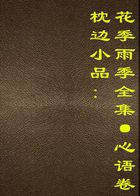丹·卡特的解释就比较具有说服力了:“犹金·威廉斯和洛伊·莱特在案发时都只有13岁,欧仁·蒙哥马利算半个瞎子,韦立·罗勃逊患淋病,离了拐杖寸步难行。所以检察长办公室就对沙缪尔说:‘得,这四个你领走吧。’”
对于还留在凯尔拜监狱里的几位,同伴们的获释更反衬出了他们的不幸境遇。他们感到绝望,感到自己是被出卖,成了某笔交易的牺牲品,被当作筹码,用他们的“失去自由”换取了他人的自由。克拉伦茨·诺里斯称他听到消息的那一天是“我一生中最痛苦、最伤心的一天”。更糟糕的是,“没有任何人向我们解释。所有的人,包括沙缪尔·列波维奇,全都躲得远远的”。
海武德·派特森的说法是:“对于被撤诉的几个人,那是胜利。至于我们,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司各勃洛辩护委员会”,即SDC,以及“司各勃洛少年”的支持者们仍一如既往地为狱中的五个人奋斗着。他们一面上诉,一面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不知疲倦地组织各种集会游行,号召民众向各级政府部门写信请愿。格罗威·豪尔在《蒙哥马利广告报》上撰文指出:“‘司各勃洛9少年’同时被捕,以同样的罪名被起诉,连针对他们的证据都是一模一样的,怎么可能一半人无罪,一半人有罪?”
不幸,SDC的数度上诉均被驳回。作为最后的努力,或希望,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当时的亚拉巴马州州长拜勃·格拉维斯。经与SDC的代表协商,格拉维斯州长答应,等5少年的案子递进州赦免委员会,他将力主假释。
但是,委员会里还有其他六名成员。到1941年,5少年分别向赦免委员会递交过三次假释申请,三次被拒绝。
这一年,“司各勃洛案”已历时十年。
这一年,州长办公室的主人已经不再是拜勃·格拉维斯。
这一年,“珍珠港事件”将美国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的注意力被更为重大的国际国内事件所吸引,无人再有闲暇顾及几个冤狱中的区区小民。
随着时光的流逝,“少年”们在大牢里长成了青年,到凯尔拜州立监狱探访他们的人越来越少。到后来,“司各勃洛少年”似乎真的被外界彻底地遗忘了。
有人说,正是外界的这种遗忘,解救了狱中的5少年。
也有人说,事实证明,真正能够解决问题,能够将“司各勃洛案”画上一个句号的,不是游行示威,不是上书请愿,也不是报纸上那些“评论员文章”,而是造物主对天下万民永久的、亘古不变的慷慨赐予——时间。
等到熬够了年头,等到“司各勃洛案”风平浪静,不再有外人对亚拉巴马指手画脚,评头品足,亚拉巴马人反倒能静下心来,开始他们自己对案情的推理论证,归纳总结。
1943年11月,州赦免委员会批准了查理·魏摩思的假释申请。度过了12年的铁窗生涯,这时的查理已经32岁。
两个月后,31岁的安迪·莱特被假释出狱,然后是30岁的克拉伦茨·诺里斯。
1946年11月,33岁的奥兹·鲍维尔获假释后,高墙后面只剩下了“最不服从管教,最令监狱当局头痛”的海武德·派特森。赦免委员会的听证记录上对他的评语是“恶毒,堕落,沉闷,阴险,屡教不改,无可救药……”一句话,海武德·派特森就是天生的囚犯,是亚拉巴马的“牢狱动物”(creature of prison)。
由于他的“顽劣不化”,海武德被狱方转到人称“杀人犯之家”的亚特蒙监狱农场。在那里,他每天和别的重犯要犯们用铁链子铐在一起,在毒日头下干12小时苦力。
海武德·派特森后来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夜里,我躺在上铺,仿佛还坐在免费厢中,颠颠簸簸,摇摇晃晃,四周围没有一件静止的物什……我一分钟一分钟地活人,一宿一宿地做着噩梦。在那些梦里,免费厢,牢吏们的脸,还有法庭等等,乱七八糟地交织成令人窒息的一大团……”
1948年7月一个炎热的下午,海武德和跟他铐在一起的其他8名囚犯集体越狱。为了躲过警犬和狱卒们的搜捕,9个人在沼泽地里泡了整整四天,后经同情他们的黑人相助,海武德·派特森辗转到达密执安州底特律市的姐姐家中。套用纪录片《司各勃洛——一出美国悲剧》的一句解说词:“最后一名‘司各勃洛少年’终于获得了自由。”
詹姆士·霍顿法官否决“德卡特审判”的第二年,正如朋友们所预言,在连任竞选中败北,并从此不再担任公职。在他的竞选演说中,霍顿法官谈到“司各勃洛案”时呼吁:“找出事实的真相,因为只有真相才会给我们以自由。”1973年,詹姆士·霍顿以95岁高龄,逝世于他的种植园中。
沙缪尔·列波维奇虽然没能在“司各勃洛案”中打赢任何一场官司,但他到底还是将9少年从电椅上救了下来。沙缪尔于1941年当选为纽约州肯斯地区法院法官,后来又担任州最高法院法官。和克拉任·达偌博士不一样,列波维奇法官是死刑的衷心拥护者。沙缪尔·列波维奇于1978年1月去世,享年80岁。
维多莉娅·普瑞斯在1937年7月,本案最后一轮庭审结束后,即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1969年,在丹·卡特所著《司各勃洛——美国南方的悲剧》第一版中,作者根据司各勃洛某报编辑提供的材料,称维多莉娅和茹碧·贝茨都已于20世纪60年代初去世。1976年,根据该书改编的电视纪录故事片(docudrama)《霍顿法官和司各勃洛少年》在全国广播公司(National Broadcast Company,缩写NBC)的电视台播出后,66岁的维多莉娅·普瑞斯突然“起死回生”。原来,她和茹碧都在结婚后改随夫姓。维多莉娅通过律师向NBC提起诉讼,称NBC在电视剧中将她描写成了“一个妓女和说谎者”,败坏了她的名誉。
“司各勃洛9少年”们出狱后都先后去了北方。然而,他们一直等待的“自由的新生活”却并不尽如人意。9少年中的不少人或者没有像样的工作,或者经常失业,还不时与法律发生摩擦。
海武德·派特森在底特律藏匿了两年,其间,出版了由他口述的自传《一个司各勃洛少年》。1950年,海武德被联邦调查局捕获,但密执安州州长G·曼能·威廉斯拒绝将他引渡回亚拉巴马州。第二年,海武德在一间酒吧里跟人斗殴误伤了人命,被判刑20年。1952年,海武德·派特森因肺癌病卒狱中,年仅39岁。
安迪·莱特落脚在纽约州的阿尔班尼。在那里,他又被指控强奸一位白人妇女,但最后无罪获释。
安迪的弟弟洛伊·莱特,9少年中最年幼的两人之一,出狱以后上过学,当过兵,也成了家。1959年,洛伊怀疑妻子对他不忠,便开枪杀死了妻子,尔后自杀。
只有克拉伦茨·诺里斯过上了“正常人的日子”。他于1946年违反“假释条例”,擅离亚拉巴马州。逃到纽约后,克拉伦茨顶着他兄弟的名字,做了一名本本分分的环卫工人,并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克拉伦茨过着半隐秘的生活,几乎从不接受记者和作家们的采访。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他的孩子们长大成人,克拉伦茨才意识到,迟早有一天,孩子们会了解他的过去。而他的“过去”,是一份写满了“强奸”二字的犯罪记录。
克拉伦茨找到他早年认识的ILD律师,通过他们请来了曾经为罗莎·派克斯辩护的蒙哥马利著名黑人律师弗莱德·格雷。克拉伦茨·诺里斯的要求很简单,也很难:为“司各勃洛9少年”彻底平反。
克拉伦茨说,他这样做是为了他自己,为了他的妻子不必再跟着他东躲西藏,生怕有一天联邦调查局会找上门来,为了他的孩子们不至于因为父亲而感到羞愧,也是为了他的那8个伙伴们。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离开了人世,至死仍背着“强奸犯”的罪名,比如掩埋在家乡查丹努加的安迪·莱特,他的亲属甚至不敢在他最后的安息之地立一块墓碑。
1976年10月25日,星期一,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瓦拉斯签字批准了州赦免委员会为“9少年”平反的决定。
仅过了两天,62岁的茹碧·贝茨病故。
同年11月底,在“负罪逃亡”30年后,在“司各勃洛9少年案”45年之后,“9少年”的唯一代表,也是唯一生者克拉伦茨·诺里斯终于堂堂正正地回到亚拉巴马州。从蒙哥马利机场到州府的一路上,克拉伦茨一行被长长的记者车队尾随着。在赦免委员会办公室里,克拉伦茨·诺里斯被授予“平反证书”(Pardon Certificate),并接受官员们的美好祝福。
有记者问克拉伦茨是否打算向亚拉巴马州索赔,克拉伦茨扬扬手中的“平反证书”,说他能亲手拿到这个,已经比另外“8个孩子”幸运了。很多年后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克拉伦茨的律师与赦免委员会达成的协定就是,以放弃索赔换取“平反证书”。
第二天,克拉伦茨·诺里斯应邀前往亚拉巴马大学,向大学生们发表讲话。
第三天,乔治·瓦拉斯州长亲自接见了他。州长让克拉伦茨坐在身旁,握着他的手说,亚拉巴马走过了一段漫长而艰辛的路程,说他很高兴能成为为“9少年”平反的州长。
1977年7月,联邦法庭驳回了维多莉娅·普瑞斯对全国广播公司NBC的起诉。又过了几年,1982年,维多莉娅才真的死了。她直到临死仍然坚持她确实在火车上被黑人们轮奸过。
1979年,克拉伦茨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最后一个司各勃洛少年》。1989年1月23日,克拉伦茨·诺里斯因患老年痴呆症病逝,终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