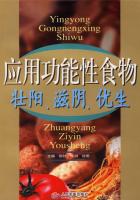按说,我够沉得住气了。
一九八一年,我三十三岁的时候才发表处女作《卖驴》和《“狐仙”择偶记》。那时,我的不少同龄人在文坛上已是纵横驰骋,如雷贯耳了。
并非我不想尽早跻身作家的行列。相反,十三岁时,我就开始做作家的梦了。这梦断断续续做了二十年。前十年,因为醉心于考大学,后又醉心于“文化大革命”,作家之梦显得遥远而飘忽。后十年,从一九七一年参加工作开始,这梦才做得认真起来。并由黑夜梦变成白日梦,一天到晚老想着当作家的事。记得我曾偷偷地向高中时的语文老师和几位要好的同学说过:“我想写小说了!”奇怪地是,当时他们没有一个人表示惊讶或反对,几乎都用相同的话鼓励我:“写吧!你应当写!”我也居然大言不惭,并不觉得是在吹牛皮。以后,每隔一段时间,他们便问我:“写了没有?”很急。其实,我比他们还急。可我知道我还不行。功力不到,徒费笔墨。想写和会写是两回事。我并没有急于动笔。在此后十年的准备过程中,我仅写过两个短篇、一部中篇,共计七万字左右。我不认为一直不停地写是个好办法。我只是扎扎实实从生活和读书两方面作准备。
但我毕竟是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自学的,文学的真谛和生活的哲理,只能靠自己去玩味和领悟。这虽然养成了我独立思考的习惯,却也延长了步入文坛的路途。但我心里很踏实,也很自信。因为一路走来,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没有虚浮和任何投机取巧的成份。我希望自己像北方寒冷地方的树种,虽然长得慢些,但要实在一点,不要空心。我第一次计划,三十岁以前出作品,但没有成功。实在说,我有点沮丧。也在心里埋怨自己太笨。于是又计划,三十五岁以前出作品。如果三十五岁以前再不出作品,就不要再做作家的梦了。这计划很有点悲壮。我竭力捺住急切的心情,不断告诉自己:沉住气,再沉住气!
终于,三十三岁发表了处女作《卖驴》。当朋友们前来祝贺时,我却流泪了。激动是可想而知的。
由是,我步入了文坛。由一个文学的看客,加入了文学的跑道。现在,我在这条跑道上已经跑了六年,发表了上百万字的作品,长篇、中篇、短篇,乃至微型小说,都作了尝试。其间甘苦是一言难尽的。
是的,这是一条跑道,一条拥挤而热闹的跑道。在这条跑道上,拥挤着老少五代作家和成千上万的业余作者。大家都想跑在前头,寻找自己跑动的最佳方式,不断调整和变换着招数。这阵容和气势都是极令人振奋的。新时期十年文学的每个阶段,都涌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或者说,在每一个百米线上,都有人破纪录。作家们是勤奋而严肃的,大家没有陶醉于已有的成就,几乎是呼啸着前进,实现一次又一次超越。并逐渐由集团军式的挺进,转向单兵作战,使作家和作品渐趋个性化。这是一次飞跃。是作家走向成熟的表现。
于是探索、变化,寻找自己的位置,成为近年来作家们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个作家的作品是否有所变化,也时时为评论家们和读者所关注。
变化的确是重要的。因为它显示了一个作家创作的活力。是否可以说,风格的形成是作家成熟的标志,而不断突破固有的模式和层面,从形式和内容上拓宽创作路子,深化思考内容,则是一个作家走向大家的开始。
探索、变化既然如此诱人,作家们追求变化就是极其自然的了。于是透过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变化和尝试。在小说形式上,从结构方法,到叙述方式,乃至语法修辞,都有许多新鲜的东西出现。过去那种单一的枯燥的千篇一律的表现形式,在作家的笔下已经少见。小说样式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局面。在内容上,从表层的人物、故事,到人的深层意识和情感,从现世的社会人生,到对历史的“寻根”和对未来的思考,内容大大丰富和深化了。哲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考古学、未来学,乃至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等等等,都在日益渗透文学的领域,成为作家们的翅膀。
在这样一个探索、变化的时尚中,我也想寻些变化,竭力跟上朋友们的步伐。那眼花缭乱的景象实在有点诱人,但也叫人心惊胆战——许多作品变得读不懂了。
这时,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作家在这上头下功夫不值得。起码我不想这么干。这样的作品,和那些始看浅显,愈读愈觉奥妙无穷的作品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变,是一定要变的。没有哪一个有追求的作家会墨守成规。问题是怎么变。为变而变就失去了变化的意义。变,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变化。犹如百米赛跑,假使因为落后不能引人注目,而突然掏出一条蛇来耍,大约终不能得冠军的。西方文学、拉美文学都有许多新的技术和形式,但我们要借鉴的须是活鲜的、让人感到愉悦的东西。而且形式的变化,最终是为内容服务的。红白喜丧都穿花裙子,会导致另一种千篇一律。
在形式和内容的变化上,我更看重内容。内容的变化可以包括横向的题材领域的拓展,以及同类题材纵向内蕴的掘进。我很愿意在这上头下些功夫。当然,这很不容易。六年多来,陆续发表了两部长篇和几十个中短篇小说,真正令人满意的作品并不多。起码我不满意。其实,《卖驴》发表不久,我就不满意了。那篇小说构思很精巧,但它所表现的到底是浅层生活,至多是一个时期的社会心理。故事也带有偶然性。于是第二篇写了《“狐仙”择偶记》。这篇作品曾引起不大不小的一场争论,读者尽可见仁见智,可在我看来,这个变化是一种进步。因为我写了日常细琐的生活。之后几年,我又有几次变化。尽管变得不明显,也很慢。直到去年四月以来,几乎一年停笔未写。不是没东西可写,而是苦恼于在一个水平线上波动。在内容和形式上,我都面临着一次挣脱。我要重新想一想。从鲁迅文学院毕业了,我却停笔了。直至今年三月,我才写了《涸辙》。这是一个六万字的中篇。也是一次探索。成功与否,我恭候读者的评判。
我在缓慢而痛苦地变化着,一如蝉蜕,文坛上眼花缭乱的景象已不能诱惑我。我很想离开那条跑道,独自跑向荒野。累了,就歇一歇,卧在草丛上躺一会;想跑了,就再跑,我真怕那么多人的呼啸和高下之争。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就我的心理秉性而言,更适宜孤独和散淡。我毕竟是一个村夫。那就一个人在荒野晃荡,慢慢道来吧。
1987.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