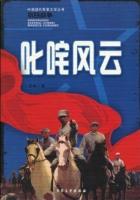云深九嶷庙,日落苍梧山。於恨在湘水,滔滔去不还。
越过宽可容百许人的天然石台,九嶷神庙的正殿问天殿赫然立于眼前。粉墙殿壁之上,乌漆大字所书的,便是这五言诗句。
苍劲凝重的隶体,映在檐下风灯微弱的光芒里,越是显得鲜明清晰。
已是熟读人间诗书的我,自然知道这四句诗词乃是唐朝才子高骈所写的著名《湘浦曲》。夜色深沉,远山苍茫,面对着那幽然的神庙深殿,再读这一首诗时,方觉自有一股苍凉郁沉之气,迎面而来。
陵诃引我入殿,言谈间甚是客气。他叫了一声:“迦儿!”灯影里有人应了一声,款款自内殿出来,手中托有一盏香茶。她是人类女子十八九岁的模样,眉目秀丽,长发顺滑,情态间温婉动人;只是腰间也系有红绦,仿佛那是神庙中人身份的一种昭示。
迦儿好奇地看了我一眼,柔顺地奉上茶来,但随即急切地问道:“陵诃哥哥,那抢夺宝珠的魔头可拦住了么?宝珠有没有夺回来?”
陵诃答道:“我们虽追了上去,却不是那魔头对手,幸好在山下遇见了大司命……”
迦儿身子一颤,问道:“大司命呢?”
陵诃叹了一口气,回头望了望殿外,当然殿门口不会有林宁的影子,可是他的眼中还是浮起了企盼之色,说道:“大司命让我们先回来……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的‘天青明罗’法术一旦施展,法力稍弱者定会受其波及……我们也真是没用,这种时候一点忙也帮不上。”
迦儿垂下头去,良久,方才说道:“我听说大司命早在年方十五之时,便轻易突破了道家‘上清’之界,又获‘诛邪’仙剑,几可跻入地仙之流。若论道行修为,在那时的九嶷山中,仅屈居于老宗主之下,被誉为神庙创始三百年来第一奇才……其实他根本无需动用‘天青明罗’之术,此术虽然具有降魔奇效,但既伤不了那魔头性命,又大大消耗大司命自己的真元;他只需祭出‘诛邪’仙剑,那妖魔立时便要伏毙当场……却为何……”
陵诃望了我一眼,叹道:“这位白姑娘先前于我有救护之恩,又是大司命带来的朋友,咱们原也算不得外人——迦儿,我便讲件旧事与你听,你听完之后,当知大司命为何宁弃那‘诛邪’不用,却要修炼‘天青明罗’之术了。”
“咱们九嶷神庙,也有将近千年之久的历史。虽说本是为祭祀那舜帝所建,其实却是道家始祖李耳当初游历人间之时,一脉传下的修真之派。庙中暗藏当初道祖传下的许多宝符仙药、神珠法器,所修习的又是正宗的道门玄功,故此弟子虽是凡胎肉身,却具有斩妖伏魔的高深法力,历来修仙得道者不下二十之数。直至第三代宗主青叶之时,他老人家眼见九嶷各族争斗杀戳太重,故此大发慈悲之心,发愿将由本宗世代相传,担负起守护九嶷之责。”
迦儿点了点头,道:“这些我都听别的师兄们说过。”
陵诃脸上掠过一抹淡淡的痛惜之色,又道:“嘿嘿,十年之前,大司命初破‘上清’境界,得入地仙之流。他风华正茂,英姿勃发之时,又何尝不是万般自负?他曾对我说起,那时自以为天下正义之道,俱在我一点赤心以论;天下曲直之分,俱由我掌中青锋而断……却不知这是非曲直、正邪之分,原也是难以辨别之事。”
他又叹息一声,说道:“那时大司命只道这三界之中,仙、人、鬼本来分明,可这妖怪,却不是这三界任何一属,既与人类杂居,也能成仙,若未能成仙,死后居然也沦入鬼道轮回,委实扰乱了三界秩序。且它们既为人类杂居,定然也是为害人间的作孽之辈。所以只要在山中见着妖怪,他轻则打回原形,重则干脆诛杀,还以为自己是以菩萨之心,而行金刚手段……嘿嘿,那时山中妖灵但闻林宁二字,都是为之色变颤栗,视同恶魔一般。若是迦儿你那时见了大司命,只怕是……”
他望了迦儿一眼,见她脸色煞白,便停住了话头。我听在耳中,心里却是一凛:莫非这个迦儿她……苦于我此时不能运用法力,故此也看不出她的原形。
陵诃又道:先师那时,虽是喜欢大司命——哦,那时我们都叫他大师兄,他入门不是最早,但不知为何,一入门辈份便排在我们之前。先前大家都有些不服,但后来也确是他最为出众,大家也就渐渐习惯了。
先师常说,大师兄修习功法的聪颖悟性,确是万中无一,但杀气过浓,恐为前生孽根所致,而非是九嶷福祉。他老人家苦口婆心,常与大师兄讲解道家丹经要诣,只盼与他除去身上戾气,不再妄动无名之嗔。
大师兄虽然将那些道经背得滚瓜乱熟,讲起经来也头头是道。背后却置若罔闻,仍然是对妖怪不分青红皂白,便要大开杀戒。
直到他将满十六岁的那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情,从此改变了大师兄的一生性情。
那时在众弟子之中,又是他第一个练成凌空御剑之术。他自己也颇为得意,有空便在山中御剑飞行。刚刚飞过碧虚洞时,却突然看见前方山道之上,有一年轻女子在蹒跚而行。
他若有所思,仿佛心绪又飞回了十年之前,接下来说道:当时大师兄心中觉得奇怪,因为这山中猛兽甚多,寻常百姓根本不敢独自入山,更何况她是一个纤纤弱女?他法眼已开,当即定晴看时,才发现那女子并非人类,而是一只大鹿,且是身怀有孕,才会行走如此笨拙。
迦儿,以大师兄那嫉妖如仇的性子,只道她既已会变幻人形,必然会为祸人间,迷惑人间男子,以供自己增进真元之需。更何况身怀六甲,将来诞下小妖怪来,只怕祸患更多。故此不由分说,御剑直飞过去!
那女妖一见他气势汹汹而来,知道是剑仙之流,吓得现出原形,望草丛之中落荒而逃!大师兄也不去追赶,当下祭出诛邪剑来,施以飞剑之术,终在三十步开外之处,剌入了它心脏之中!
我想起那血淋淋的场面,不觉也是心头一颤。
陵诃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不忍之色,又道:当时那宝剑正中那女妖的心脏,论理来讲生机当场立断,可是不知为何,她倒在地上,人的形体已渐渐化出兽毛,竟然是一只大鹿。一时她也没有断气,反而四蹄乱蹬,仿佛在经历什么巨大的痛苦,口中咿咿哀鸣不已,眼角中流下两滴泪来。那泪珠晶莹剔透,倒好似是人的眼泪一般。
大师兄心中奇怪,候它挣扎稍缓,走过去看时:只见它腹下皮毛之中,居然缓缓露出一只小小的脑袋,虽然皮毛犹自湿润未开,双眼紧闭,但已看得分明——那是一只刚刚生下的小鹿!
小鹿既然生出,那鹿妖似乎心愿已了,它那双圆圆的眼睛看了看大师兄,长出一口浊气,当即气绝身亡。唉,后来大师兄时常对我谈起这鹿妖临终之态,他说十年以来,最令他不敢忘记的,便是它临终时看向他的那一眼。
它本没来招惹任何人,却最终惨死山中。
当时那鹿妖中剑重伤之下,本来早该死去,想必是不舍得腹中小鹿,所以才拼了最后一丝力气,将小鹿生了下来,却是刚刚见面,便要天人永绝……大师兄理应是它最不共戴天的仇人,可是它看向他的那一眼之中,却全无怨毒之色,反而极是祥和安然,甚至还带有几分母性温柔的神情……好象在对他说,他也只是个不懂事的傻孩子,它也并不怨他一般……
当时大师兄怔怔地站在它的尸身之前,只在一刹那间,心中转过无数的念头,倒仿佛经过了千万长劫的时间。
曾经坚信不疑的信念,在那一刹那间,却仿佛全被颠覆得十分彻底——难道妖怪这种被视作是天地间不该出现的生物,也是最邪恶自私的一种生物,居然也会有那样温柔、坚强和博大的胸怀么?难道斩妖除魔的志向,竟然是从一开始,就完全是错误的么?
我心中颤栗,忍不住问道:“那……那小鹿呢?小鹿怎么样了?”
陵诃长叹一声,答道:“它本未到生产之期,是其母在临终之前,运用法力将它提前催生出来的,又无母乳哺养。虽然后来大师兄将它带到舜源峰上,细心哺育,但终是只活了短短四天时间……”
“一念之差,断送了两条无辜的性命,大师兄始终认为,这是他终身不能洗脱的罪孽。”
顿了一顿,他接下去说道:“当时小鹿死后,大师兄真是肝胆欲裂,心中伤痛之极,飞快地跑到先师跟前,忍不住嚎啕大哭。师父玄功精妙,大师兄虽没有开口言述,但先师自然知道他是为何事心痛。”
他说到自己师尊,一向平和的神色之中,也略略带有怅惘之意,显然是引起了孺慕之思:“我当时正好随侍先师身旁,却见师父拍了拍大师兄的肩膀,只说了两句话——往事已矣,来者可追。”
“迦儿,后来大师兄便似变了个人一般,他竟然封存了那柄具有无上神通的‘诛邪剑’,宣称毕生不再用剑。并随手折下一枝斑竹,作为自己法器。他对我们说,且不论我道家精义,便是佛家亦有云——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我皆令入无余涅盘而灭度之,上从诸佛,下至傍生,平等无所分别……天仙神佛、人妖鬼魅都是一般。神仙也不敢说自己一定没做过错事,妖怪也不一定就是十恶不赦……”
“正因为此,十年之后,当初妖灵惧之不迭的林宁,才会成为今日这令九嶷百族共同景仰的大司命啊……”
迦儿怔怔地呆了半晌,喃喃道:“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大司命他当初救我之时,也说……”她没有再说下去,眼中却闪动着莹亮的泪光。
陵诃叹了一口气,说道:“只可惜我也太过没用,遇上冥夜魔头,却是一点也帮不上大司命的忙。”
只听殿门外一人笑道:“你胡说什么?怎会帮不上忙?”
蓦有清凉山风自殿外吹入,灯火跳动。一个熟悉的身影大步走了进来,赫然正是林宁。
他迎着我们惊喜讶异的眼神,微微一笑,伸出手掌,掌心上托着一只小小的翠绿玉盒。陵诃和迦儿“呀”地一声,惊喜地叫了出来。林宁淡淡道:“冥夜走了,这清净宝珠,我就拿回来了。”
虽是寥寥数语,一带而过。然而他的神情间却有些疲惫,显然方才与冥夜一场争斗之激烈,绝非如他所说那般轻描淡写。
我们一起用过神庙中斋客的茶饭,用饭时偶听陵诃言谈,似乎这庙中众人年长者虽多,但却都算是林宁的下属,且大部分人的道术,还是由他代师传授。
然而众人于他虽有敬重之意,日常相处却极是随意,并非是肃然如对大宾;观这林宁的起居饮食也极是普通,毫无奢华之气。
饭后迦儿要领我去客房休息。我虽想向林宁询问招魂之术,但见他精神有些不济,想来是方才激斗之故,当下又将话头咽了回去。
迦儿领路前行,柳腰款摆,徐徐缓步,姿态袅娜动人。宽大的黑袍掩盖之下的一搦腰肢,摇摆起来竟似流水一般灵动,不觉看得呆了,喃喃道:“这姑娘走路的模样真是好看。”
林宁望了迦儿远去的身影一眼,低声道:“白姑娘,二更之后,你还是不要多看这姑娘才好。”
九嶷的夜晚山林静寂,连鸟鸣都不曾听闻,只有风簌簌吹过屋顶。然而我却久久不能入睡,捱到半夜,终于忍不住披衣起身,开门出去。如水月色泻了一地,山风徐来,精神顿时为之一爽。远山苍茫,在暗蓝的天色衬映下,只是一抹黛青的影子。
客堂至前殿之间,尚隔有一段起伏不平的山路。初秋的深夜,已略微有了寒意。月色下隐约可见路草衰黄,叶尖上秋露如珠,闪耀着冷冷的光芒。
忽听一阵“索索”微响,似是有人穿越草丛而来。我吃了一惊,待要用隐身之术,却又想起舜源峰顶,早被设下了禁绝法术的‘绝仙界’。当下疾速跳下路旁草丛,那里草长足有半人多高,极是茂密,恰好掩住了我的身形。
“索索”之声却越是近了,我从草丛缝隙之中,向外望了出去。
这一望之下,我险些叫出声来!
迦儿!是迦儿么?
走在前面的那名女子,正是白日里我所见到的那柔顺妩媚的迦儿。此时她脱去黑袍,仅着家常白衫,上身山峦起伏,曲线玲珑,着实有些诱人。然而当视线移向她的下半身时,却看见本该有两条修长的腿的地方,竟然变成了一条粗长的蛇尾!蛇尾惨青,鳞甲间隐现金纹,那样艳丽而妖异的颜色,在这暗夜之中陡然看见,着实有些可怖。
那“索索”之声,便是她扭动蛇尾,一路行走时所发出来的声响,无数的野草伏地倒下,在她面前自动分开。
迦儿是蛇?怪不得林宁叫我二更之后便不要与她独处,想必是因为这蛇妖本来修行较浅,白日尚可借日华保持人身,夜深之时便不得不化出部分原形。奇怪的是我怎么感受不到她有丝毫的妖气?况且这神圣的庙宇之中,供奉的都是煌煌的神明,为何竟会允许蛇妖留在此处呢?
迦儿身后还跟有一人,身形婀娜,显然乃是一个年轻女子。只是她全身覆以黑纱,纱长几可及地,就连面貌也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明亮的眼睛。
她二人自后山而来,一路行向前殿,却是默然无语,情形着实有些诡异。
我悄然蹑在其后,裙脚都被露水染得有些湿了。直到前面终于出现了一带墙垣暗影,外绕长廊,朱漆柱子撑起廊顶,一直接到了殿堂中去。
这不是问天殿外的长廊么?
沿廊两边俱摆有一排暗褐色的土陶矮盆,只有一尺来高,窄口圆肚,显然是当地土窑烧制的成品,没有花案纹路,质朴得近于厚重。临睡前迦儿带我经过此处,曾经告诉我说,盆里植着的那种叶片修长翠绿的植物,是出自九嶷的奇葩,名字叫作芷兰。它香气清幽,花形甚美,然而花期也不过只有六天,而且只在夜深人静之际,方才悄然绽放。
记得当时迦儿还笑着对我说:“白姑娘来得真巧,听大司命说,这些芷兰恰在今晚是第一天花期。只是姑娘远来体乏,不然倒可前来观赏呢。”
白天我看见它们的时候,那些白色的花苞合得极紧,掩藏在叶片深处,几乎看不清其真实面目。
然而现在,在幽暗的夜色里,那些花苞却悄然绽放,舒展开了薄纱般纤长洁白的花瓣。远远望去,便如是一只只小巧玲珑的花灯,果然极美。
迦儿和那个女子,默然地穿行在开满芷兰的长廊之中。清凉的山风,送来了细微而淡雅的香气。
突然,我看见了林宁。
他极随意地披着一件灰色长衫,立于长廊的尽头,手中执有一只铁水喷壶,正在细心地为每一盆芷兰浇水。他的袖袂宽大而飘逸,使得他的每一个动作看上去,都是那么的舒缓而自然。无数细密晶亮的水珠,温柔地自喷壶徐徐浇下,沿着叶片滚落开去,一直渗透到了根部的泥土之中,空气中顿时有了湿润的泥土味道。
芷兰花沐浴在水珠的清凉里,每朵花上都幻出一张小姑娘的俏脸来,对他甜甜一笑,又悄然隐去了。
那该是芷兰花的精灵吧?
林宁对花灵回报了一个柔和的笑容,放下手中喷壶。不知为何,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我悄悄地躲在一旁的柱后,却恍然觉得这情景如在梦中经历。
良久,他仰起头来,天幕暗蓝,月弯如线。只听他轻声吟道:“浮生欢爱如明月,半夕团圆半夕缺。悲喜无端翻旧曲,忍将明月填新阙。楚地衣冠葬白骨,夷宫荒草埋池榭。唯有清辉似旧时,引人幽思尽遥夜。古今一轮明月下,多少儿女挥泪别。”
诗句清雅别致,不知是出自于何人之手。然而淡淡忧愁之中,又似是蕴藏有无限苍凉之意。
这该是个什么样的男子啊,他的举止是那样的温和而蔼然;可是在他的心中,却分明隐藏着一个神秘的世界。
忽听“啪啪”两声清脆的击掌,我凝神看去,却是迦儿身后那身覆黑纱的女郎,两只白如玉雕般的素手,凌空轻轻地击了两下。
林宁向她微微一笑,但听她道:“大司命好雅兴,居然还在学那些凡人书生,临风感叹,对月抒怀!”
声音清雅柔和,煞是动听,却略带有三分薄谑之意。
迦儿上前躬身道:“大司命,奉你之命,迦儿已将这位……这位姑娘请上山来了。”
林宁点了点头,迦儿悄没声地退了开去。偌大的长廊之中,只余下林宁和那黑纱女郎二人——还有藏于柱后的我。
那黑纱女郎放下手掌,淡淡道:“倒要多谢你遣人前来,否则以我自身之能,断不能上得峰顶呢。”
林宁似是对她颇为熟悉,答道:“每日天黑之时,神庙山门即时封闭。兼之又有这隔绝法术的‘绝仙界’庇护,若没有我神庙弟子引导,寻常人仙妖魔,确是都不能上得峰顶。这‘绝仙界’本是我道家祖师老君所创,除了我宗派之中的道术以外,其他任何法术,在此结界之内均不能施展。为的也是在人间留下一方净土,保护我道门弟子,不受妖邪侵害——不过以姑娘之能,这‘绝仙界’倒也不见得……能隔绝姑娘玉趾之所及。”
那黑纱女郎笑了一声,声音清澈悦耳,说道:“太上老君么?那白发老儿,现在只是藏于兜率宫中,等闲难以见着他的尊颜。”虽虽是闲闲几句,却已是悄然引开话题,林宁淡淡一笑,话锋一转,说道:“今日斗胆请姑娘移尊鄙处,姑娘自然清楚,林某乃是为了何事。”
那黑纱女郎眼中笑意敛去,道:“我……我却并不明白。”
林宁仰首望着那弯明月,轻轻说道:当初湘水初见,我二人把酒畅谈之际,也正是如今夜一般的月夜,湘水上清辉如银,碧波微漾……而姑娘你妙语高论,意境幽远,风度迥异常人,英风豪气却又一如男儿,实令林某大为钦敬……
你当时写过的那首诗,我还记得很清楚呢。
他轻声吟道:湘江初冷碧水沉,山气空矇月色昏。兰舟随波轻触浪,清风过舷缓余温。江上对歌当侑酒,抒怀何寄难成文。若得人生终如此,自然朝暮是良辰……
以姑娘心性之淡泊,只需有对歌侑洒、啸傲江上的生活,便觉得朝朝暮暮,皆为良辰;时值今日,却为何一定要身涉这些纷争之中呢?
那黑纱女郎低下头来,道:“你……你还记得这样清楚么?”
我藏在柱后,心中却更是惊讶莫名:听他二人话中含意,竟似是许久之前便已经相识,而且交情非浅,那……那林宁他……
多么静谧而美丽的夜晚,还有这玉树琼花般的两个人儿。他们并肩而立,身披银辉,芷兰花在他们的身边轻轻摇曳……是那样的安然、和谐……
蓦然之间,一种莫名酸楚的痛感,竟是自我的心头缓缓升起,是在哪里,我曾依稀见过,这样美好的一幅画面呢?
只听林宁道:“今日再与姑娘相逢,却是意外之意……一切皆是命中注定,只怕强求不来。姑娘本是聪明人,难道还要林某出言点破么……”他看了一眼那垂首不语的黑纱女子,似有些不忍之意,便没有再说下去。
那黑纱女郎幽幽叹了一口气,说道:“情之所钟,如之奈何?”语意中颇多怅惘之意。
林宁衣袖一拂,向后退出两步,淡淡道:“既然如此,你动手罢。”
休道是我,便是那黑纱女郎也是吃了一惊,明若朗星的眸子之中,射出两道惊疑的神色来,脱口道:“你……你怎知……”
林宁苦笑道:“你虽是应我之邀上得峰顶,身上却暗藏‘碧烟尘’。你虽刻意收敛了法力,但仍然难以掩盖‘碧烟尘’天生的宝气。放眼三界之中,唯有这件出自兜率宫中的宝物,才能抗拒道祖布下的‘绝仙界’……起先冥夜来时,我便有些疑心了,如今你……你若不是为了前来夺取清净宝珠,却是为何?”
他挺直身子,语气虽然平和,直视那黑纱女郎的眼神之中,却隐有凛然之意,缓缓道:“姑娘法力高强,林某自然是一清二楚。可是姑娘也请再三思量,我九嶷神庙弟子,若都是浪得虚名之辈,只怕守护九嶷百族之责,也不过是一番空口白话罢了。”
那黑纱女郎默然凝视,林宁泰然对之,只是再也不发一言。一时之间,连那月色都仿佛凝固了一般。
我偶然一瞥,但见那黑纱女郎垂下的双手紧紧相握,指缝间陡有碧光闪动,显然掌心中隐藏着一件极为厉害的法宝。
林宁灰色的袖袂,在九嶷的夜风中飘动不已,一如山间最温柔的那抹晨霭,却也隐隐含有无限杀机。
黑纱女郎掌中碧光亮了一亮,终于黯淡下来。
只听她长叹一声,说道:“罢了……林兄,你我相交之情,永铭于心……我终是不能与你为敌……”
她身形陡转,凌空腾起,身姿轻盈娇软,有如烟雾一般,果然是能够自如施展法力。
林宁仰起头来,扬声道:“姑娘,林某还是有一言相劝——谋事虽是在人,成事却只在天啊……”
黑纱女郎破空飞去,闻言方才于半空中回过头来。山风过处,她身上黑色的绡纱层层临风飘飞,风姿飘缈,清丽出尘。
但闻她幽幽应道:“情之所钟,如之奈何?”竟还是先前回答林宁的那两句话语。然而其中暗含的那种忧伤叹惋之意,却显得更是浓了。
明月下但见她飘然飞远,直到终于消失在夜色之中。
林宁坐于廊椅之上,淡淡道:“是白姑娘么?月色怡人,何不出来清谈畅怀呢?”
我又惊又窘,只得自柱后出来,嗫嚅道:“我……并非有意偷听,只是想找……迦儿姑娘说话……”说到迦儿二字之时,忍不住偷偷看他一眼,想听听他对这蛇妖之事作何辩解。
林宁看我一眼,说道:“方才你不是都看见了么?迦儿她是修道的蛇妖,因为道行不够,到了夜晚便不能保持人形。白姑娘虽非常人,但恐怕还是有些看不惯她的真身。”
我不想他这么坦然便说了出来,脸上又是一热,忍不住问道:“可是白天看她的样子……并不象是世间传说之中的妖怪啊……再说九嶷神庙这道家圣地,何以允许迦儿在此呢?”
林宁轻轻抚弄芷兰叶片,答道:迦儿原是附近山中的蛇妖,初出道时,曾爱过一个凡间男子。两人来往时她无意间暴露了行藏,差点被那男子请来的道士诛杀。我恰从那里经过,见她道行虽浅,但心性良善,对那男子竟是真心相恋,又从来没有害过人,便出手救下了她。
入道门者,不过是看其有无道心,形态真身倒是其次。她虽是妖身,但其善良温柔之心与人无异,她自愿要留在我身边学道,我又何必拘泥于人妖之别?
他微微一笑,道:“白姑娘,依我看来,只怕你也不是常人罢?”
我腾地站起身来,惊道:“你……你……”
林宁神色如常,眼望我慢慢说道:弱质女流,能孤身一人,千里迢迢来到九嶷,那便是最大的不普通。我们九嶷山灵气充沛,精灵极多,除了那些能修成人形的精怪之外,因树木阴寒郁沉、枝叶积腐之气而生出的魑魅魍魉,也是为数不少,平时多散游在偏僻的山林之中。虽然它们是低等的精怪,根本不懂得任何法术,但阴气相侵,常人若是遇见,身体是必然受损。当地山民来神庙祭拜,事先都要佩戴我等神庙中人赠送的灵符,有灵符上灵光的保护,方能使那些精灵不敢近前,保得路上平安。可是姑娘你一路行来,穿越如此之多的山林,除了遇上相柳遗那毒物相害之外,却并无其他妖灵搔扰……
白姑娘,林宁见识浅薄,但也知道这三界之中,具先天之能,所到之处百邪辟易,而不受妖气侵扰之人,非神即仙。
我见他将话已说到这步田地,心里一横,当下开口说道:“大司命,实不相瞒,家父乃是三界之中,大有地位之人。最近却突遭横祸,元神好端端地被人摄去,不知所踪……我忧心如焚,遍访三界故旧,也曾四处寻找,终是不知家父元神的下落。”说到这里,心中一阵酸楚,喉咙也不禁哽住了。
林宁眉梢一动,道:“元神既失,若不是被人收去,定是归属冥府。你们可去冥府察探过么?何况三界都归天庭拘管,你父亲既有如此地位,为何天庭那些神仙们竟会坐视不理?”
我定了定神,含泪抬起头来,恳切说道:此事蹊跷,又事涉重大,故我们并不敢冒然将此事外泄……家父非同常人,便是死后魂灵也不归属冥府,也是无从察访。后来闻道说贵山之中,有擅招魂奇术之人,白莹盼着他或许能施展法力,召回家父魂魄。故不远千里前来探访,只盼着我一片诚心,能够打动他助我寻父。
但久已听说九嶷地界神妖混杂,我是外来之人,又不明底细,若是冒然亮出身份,若是被心怀叵测之人探知,反不利于寻访那人。所以才隐瞒形迹,并非有意相欺,还望大司命见谅。
父王失去元神之事,当时只有龙宫中人及朝臣在场。虽兹事重大,但时值龙族多事之秋,又有三海在旁虎视眈眈,为了安定海域,当时我确是下了严令,在我未寻访回父王元神之前,不准在场众人向外界有丝毫透露,否则定要处以极刑。故此虽是闹得天翻地覆,外界却鲜有人知。
林宁听到“招魂奇术”四字之时,明显地一怔,两道清澈的目光转了两转,落到了我的脸上。他沉吟片刻,方才说道:“原来如此,九嶷族中,确有一人,极擅招魂之术,只是他……”
我陡闻此言,顿时喜出望外,急不可耐地问道:“他在哪里?大司命,求你快告诉我啊!”
林宁看我一眼,似是难以启齿一般,缓缓说道:“此人……此人是九嶷旧族中人,确是极擅此术。然而他心术不正,为害四方,早已在三年之前,便已被家师亲手诛杀……”
仿佛有轻微的“崩”的一声,是心中一直紧绷着的那根弦,猛然间竟是断了……一切都变成了空白,语言也不复再有任何意义。我呆呆地望着他,却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被诛杀?此人已不在人世了?那招魂之事……我的父王……
我突然想起一事,仿佛溺水之人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般,急忙问道:“那他可还有传人?似这等奇术,不可能就此湮没于尘世之中啊!”
林宁叹了一口气,道:“白姑娘……”他没有再说下去,可是那脸上神情,却是写得明明白白:那个人,根本就没有什么传人啊……
好容易积起来的一点希望,如风中微弱的烛火,只是闪了两闪,噗地一声便灭得干干净净。林宁仿佛叫了我一声,但我却忘了应他。
无尽的绝望痛楚的黑暗之中,突然有一点火光闪了一下:“不能招魂便不招魂罢,不见得那个人死了,我就找不回我的父王!那人既是九嶷旧族,自然在此生活了多年。就算他没有正式授徒,但总是会在九嶷留下一丝痕迹罢。我便耐下心来,慢慢寻找,也不见得就寻不着招魂的法子!”
耳边忽闻林宁柔声道:“你很爱你的父亲罢?”
我咬了咬牙,点头道:“不错。大司命,我愿用自己的性命,却换回我父亲的平安。九嶷奇人无数,也不见得只有一个他……我不难过,我不会难过……我一定会救回我父亲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却有着发自内心的坚定,也不知是在说给他听,还是在对自己说话。
林宁两道目光,一直是温柔而怜爱地落在我的身上。
沉默片刻,林宁忽然说道:我……我是没有父母的,也不知自己的来历。听说大祭司——我的师父,他发现我的时候,我便是被丢在这九嶷的舜源峰下,一处山间草地之上。听说当时我睡得正酣,身边还有两只老虎在打转儿……也不知是被父母刻意地丢弃了,还是被猛虎从山下衔来的……师父收养了我,教我修真的法术咒语。或许是前生的善缘罢,我学起道术来进步十分神速,没有几年便超过了同辈中人。长大后我顺理成章地做了祭司,前年师父仙逝,大家便推举我为神庙宗主,号为大司命……
我从小在这神庙之中长大,庙中所有的祭司,都是出自于一个教派,说起来都是师门的伯叔兄弟。大家虽然和气,到底身为修道之人,性情都是淡泊得很……有时候看见前来进香的信民,人也好、妖也好,都是一家人亲亲热热的……别的祭司,虽然是在庙中修道,毕竟还有亲人前来探望,唯有我……我一直都是这样的,我自己……就是自己在天地之间唯一证明存在的痕迹,有时候我甚至想,好象上苍让我来这个世上,就是为了在九嶷做祭司的……
他自嘲地笑了一下,笑容虽然是一贯的恬淡,眼底却有着掩藏不住的哀伤:“白姑娘,你的心情,我是了解的……如果在这世上,也有一个对我来说这么重要的人不见了,我会跟你一样,不顾一切的去寻找他;若是找着了,我会把他看作自己的生命一般珍贵,好好地保护他……倾尽我所有的力量,让他这一辈子,都不再受到任何伤害……”
芷兰幽幽的香气,在月色中久久不散。
我深吸一口气,胡乱道:“这芷兰花很难得开放一次的,是么?这样美而贵重的花,怎么我在九嶷别的地方都没瞧见过?”
林宁看了一眼芷兰那小巧清丽的花朵,淡淡道:“是啊,芷兰四十年开放开次,花期却只有短短六天。养它也颇为麻烦,单只是浇水一事,便要要分时辰浇上六次,时辰不同,水量也不尽相同,很是难养。寻常人哪里有这个耐心?所以我在庙中之时,都是亲自动手浇灌。”
我心乱如麻,随口道:“既然难养,又只有六天的花期,不养就是了。世上兰花品种多了,也未必不如这种芷兰,又何必定要养它呢?”
天际开始有了微微的青色,风不知什么时候也悄悄停了,四周一片静谧。
林宁笑了,提起一旁放着的灯笼,旋开盖子,噗地一声吹灭了残烛的余光,随手摸了摸我的头。
我本能地想要躲开,但看他神色,却并无男女猥亵之意,反倒是多有怜爱,仿佛只当我是个小孩子一般。
他这个细微的动作,突然让我想起了我那生死未知的父王。他也是喜欢用他那宽厚的大手,那样爱怜地抚过我小小的丫形龙角。我鼻子一酸,倒是险些掉下泪来。
但闻他悠然道:“有生有灭,不垢不净。生老病死、繁茂枯荣都是必然的规律,不管是活过千年万年,甚或只有短短六天,又有什么区别?芷兰娇弱难养,花期极短,可是开的时候,你看它可有多美……生命的短暂与美好,大抵如此罢,也就分外地让人懂得去珍惜……”
熟悉的青草香气,慢慢地散发出来,渐渐取代了芷兰的幽香,萦绕在我的鼻端……那种淡淡的好闻的味儿,让我紧绷着的心也随之慢慢松弛下来……我的睡意渐渐上来了,眼皮发涩,迷迷糊糊之间,我似乎看到父王正在向我微笑着、敖宁表哥还是那样英姿勃发、还有坐着云车之上的、风流倜傥的三郎……母亲、严素秋、负相的影子,都在眼前一晃而过……我潜意识里挣扎着,想要让自己清醒起来……可是我真的是太累了,什么四海五岳、三界众生,什么龙神龙子、水族纷争,我什么都不想管,我只想这么舒舒服服的、没有无尽的担忧、没有时刻的警惕、没有悲伤、没有哀愁、乖乖的、单纯地睡下去……
恍惚一只温暖的手掌抚过我的头发,迟疑了片刻,又把几根乱了的发丝理到我的耳后。掌缘略带厚茧的肌肤,轻轻擦过我的耳垂。
只听他在耳边轻声叫我:“白姑娘……白……莹儿?唉呀,这孩子也真是……这样子……她倒也睡得着……”
本能地,我将自己偎得更深了一些,也在那一瞬间,我彻底地坠入了黑甜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