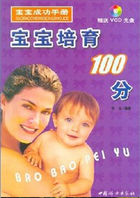5月3日,比斯特里察。5月1日晚8点35分离开慕尼黑,第二天一早抵达维也纳。预计到达时间是6点46分,但是火车晚点一小时。由于火车晚点了,并且可能很快发车,我没有离开车站太远。但是从火车上望去,在街道上溜达了一下,感觉布达佩斯是个很美的地方。
这地方留给我的印象是像来到了东方国度。这里的桥是多瑙河上最华丽的,又宽又高,散发着贵族气息,好似把我们带进了土耳其风情中。
随后我们离开了布达佩斯,夜幕降临之后到达了克劳森伯格。我在皇家旅店住了一晚。晚餐是一只用红辣椒烹制的鸡,味道非常好,只是吃完了很渴(备忘:要为米娜问到烹饪方法)。我询问了侍者,他说这道菜叫做“paprika hendl”。因为这是一道民族特色菜,所以在喀尔巴阡山一带应该都能吃到。
我发现我那点可怜的德语在这里居然派上了大用场。如果不会德语,我在这里简直待不下去。
由于在伦敦的时候留出了一些时间,我去了大英博物馆,查阅了一些关于特兰西瓦尼亚的书和地图。我惊讶地发现,跟该国的某位贵族打交道的时候,提前对他们的国家有一些了解会帮助你得到他的重视。
这位以贵族命名的地区在这个国家的最东边,地处特兰西瓦尼亚、摩尔达维亚、博科维纳三国交界处,喀尔巴阡山中段,也是整个欧洲最荒凉也最不为人所知的地方。
任何地图或书上都查不到德古拉伯爵城堡确切的位置。因为关于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份地图都还不如我们英国测绘局的地图详细。但是我发现,有一个德古拉伯爵命名的叫做“比斯特里察”的小镇非常有名。我应该在这里记下一笔,以便日后向米娜讲述我的旅行见闻时不会遗漏。
特兰西瓦尼亚的人口构成中有四个特殊的民族:南部是撒克逊人以及古代达西亚人的后裔华莱士人,西部是马扎尔人,东部和北部是希克里斯人。我要去的最后一个地方的人自称是匈奴王阿提拉和匈奴人的后代。这也许是真的,因为当11世纪马扎尔人占领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们发现了匈奴人居住在那里。
我在书中还读到,世界上每一种迷信都集中在喀尔巴阡山那一块马掌形的区域,就好像那里是某种想象的漩涡中心。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我在此地的停留将会非常有趣。
尽管我的床非常舒适,但是我却没睡好,总是被一些奇怪的梦惊扰。我的窗外有一只狗狂吠了一夜,可能没睡好跟这事有关系;也许是因为辣椒的缘故,我喝光了瓶里的水还是觉得口渴。快到早上的时候我才睡着,又被不停的敲门声吵醒。所以我想,被吵醒的时候我是熟睡的。
早餐我吃了更多的辣椒和一种叫做“mamaliga”的玉米面粥,还有一道叫做“impletata”的菜味道很棒,是中间填有五香碎肉的茄子。
因为按照时间表火车八点钟之前就要发车,所以我不得不很快结束早餐。但是当我七点半匆匆忙忙赶到车站之后,却不得不坐在车厢里等了一个多小时。看起来越往东火车越不准时。不知道中国的火车会是什么情况呢?
这一整天我们都在一个拥有各种各样美丽事物的国家中缓慢前行。时而看到陡峭的小山顶上矗立着小镇或城堡,好似古老的弥撒曲中描绘的情景;时而沿着河流或者小溪而行,从两侧宽阔的石岸判断,这里曾经发过洪水,奔腾汹涌的水流把两岸冲刷得干干净净。
每个国家都有形形色色的人们,穿着形形色色的服装。有些人穿着短夹克和家里做的裤子,戴着圆帽,就像英国、法国或者德国的农夫,但是也有些人穿得非常美丽。
如果不近看的话,女人们很漂亮,只是腰部非常粗拙。她们都带着白袖套,大部分人都系着大大的腰带,腰带上有很多飘带垂下来,像芭蕾舞裙一样,只不过她们里面穿着衬裙。
我们看到的最奇特的人是斯洛伐克人,他们比其他人更野蛮,戴着大大的牛仔帽,穿着大大的像口袋一样的灰白色裤子,白色亚麻布衬衫,系着差不多有一英尺宽的又大又沉的皮带,上面满是黄铜铆钉。他们穿高筒靴,裤腿塞进里面,留着长长的黑发和浓密的黑色胡须。他们非常独特,却不能给人带来好感。如果是在舞台上,他们会被立刻安排饰演一伙儿东方强盗。然而,我却被告知其实这些人非常温和,性格中相当缺乏自信。
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到达了比斯特里察这个非常有趣而古老的地方。客观地说,我现在还只是在比斯特里察的边界线上,因为波戈隘口正好经过这里通往博科维纳。这里曾经经历过很多灾难,至今还留有遗迹。十五年前发生了一连串大火灾,造成了五次严重的灾难。17世纪初还发生过战争,被围攻三个礼拜,一万三千人丧生,可能其中有一部分死于饥荒和疾病。
德古拉伯爵安排我住进了金皇冠旅馆。它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因为这里完全是古色古香。既然来到了这个国家,我当然想尽量从不同方面感受它的风情。
很明显旅馆里有人在迎候我,因为快走到门口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和蔼的中年妇人,一副普通的农妇装扮-穿着前后都有长围裙的白色贴身衣,装饰着花花绿绿的东西,衣服有些过紧而显得不太庄重。当我走近的时候她向我弯腰行礼,问道:“请问是英国来的先生吗?”
“是的,”我回答,“乔纳森·哈克。”
她笑了,向一个穿着白衬衫的中年男人示意随她进去。
男人进去之后很快又出来了,手上拿着一封信:我的朋友,欢迎来到喀尔巴阡山。我正热切地渴望你的到来。今晚睡个好觉。明天三点公共马车将从博科维纳出发,车上为你预留了一个座位。我的马车将在波戈隘口等候你,把你带到我这里。相信你从伦敦出发到这里的旅程是愉快的,你也将在我美丽的领地度过美好的时光。你的朋友,德古拉。
5月4日,我发现伯爵已经给旅馆老板寄过信,让他给我弄到马车上最好的位置。但是我向他询问细节的时候,他却保持沉默,并且假装听不懂我说的德语。这一定不是理由,因为在这之前他都能毫无障碍地听懂我的话,至少是准确地回答了我的问题。
老板和他的妻子,就是昨天接待我的那位女士,像受到惊吓似的彼此对看一眼。他咕哝着说,钱已经随信寄到了,他只知道这些。我又问他是否知道德古拉伯爵,是否能告诉我一些关于他的城堡的事情,老板和他的妻子马上在身上画十字,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并且拒绝再谈下去。出发的时间马上到了,我也没时间问更多的事情了。所有的事情都非常神秘,并且让我感到非常不舒服。
在我即将动身的时候,那位女士来到我的房间,有点歇斯底里地对我说:“您一定要去吗?哦,年轻的先生,您一定要去吗?”她的情绪如此激动,德语说得语无伦次,还混杂着某种我根本听不懂的语言,只有不停地问问题我才能弄明白她的意思。当我告诉她我必须马上动身,并且有重要的公务在身的时候,她再次问道:“您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我回答是5月4日。她摇了摇头,又问了一遍:“是的!这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您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我不明白她的意思。她继续说:“今天是圣乔治节前夜。您知道吗?当午夜的钟声敲响时,世界上所有邪恶的东西就会四处游荡。您知道您要去的是什么地方吗?您知道您将遇到什么吗?”看得出来她很痛苦,我试图去安慰她,但是一点用都没有。最后,她向我跪下,哀求我不要去,至少等一两天之后再动身。
这一切看上去如此滑稽,我却感到非常不舒服。我毕竟有公事需要完成,任何事情都不能阻碍我。我试图扶她起来,鼓足勇气告诉她,我谢谢她的好意,但是我的任务必须完成,所以我必须去。
她站起来,擦干眼泪,从脖子上摘下一个十字架递给了我。我不知所措,因为在一个英国教徒看来,这种东西带有偶像崇拜色彩,但是拒绝一位哀伤的年长女士的好意又似乎非常不礼貌。
我猜她一定看出了我脸上的疑惑,所以她把链子挂在我脖子上时说了一句:“看在您母亲分上。”然后就转身离开了。
马车晚点了,对此我已经习惯了。这段日记是在等车的间隙写的;十字架还挂在我的脖子上。
我的心情无法像平时一样轻松。到底是那位女士的恐惧,还是这里众多跟鬼怪有关的风俗,抑或是这个十字架造成的呢?我不知道。
如果有一天米娜收到了这本日记,而我却没能回来,就让它替我道别吧。马车来了!
5月5日,城堡。清晨的灰霾已经散去,太阳跃出了远处的地平线。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远处的树或小山的缘故,地平线看上去有点参差不齐,因为它离那些景物很远,并未混合在一起。
我没有困意,所以一直在写东西,直到睡着。醒来之后才有人来叫我。
这里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值得一记。为了避免读者的想象力太过丰富,认为我在比斯特里察吃的是玉酒仙肴,让我详细描述一下我的晚餐吧。
有一道菜他们叫做“强盗牛排”-把小块熏猪肉、洋葱、牛肉用红辣椒调味,用木签串好放在火上烤熟,简直就跟伦敦喂猫的肉一模一样。晚餐的酒是金梅迪克,入口之后舌头会有一种奇怪的灼烧感,让人感到不舒服。我只喝了几杯酒,没有碰其他的东西。
我坐上车以后,马车夫还没上来,我看到那位老板娘在跟他交谈。显然他们是在谈论我,因为他们不时地看我,一些坐在门外长凳上的人也围过来听,然后大部分用一种同情的目光打量我。因为那群人属于不同的民族,所以我听到了很多奇怪的词反复被提到。我悄悄地从包里拿出词典,想弄清楚那些词是什么意思。
我不得不承认他们说的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在那些词里面,“Ordog”是“撒旦”,“Pokol”是“地狱”,“stregoica”是“女巫”,“vrolok”和“vlkoslak”是一个意思,只不过一个是斯洛伐克语,一个是塞尔维亚语,指的是一种类似狼人或吸血鬼的东西。
我们启程的时候,人们已经把旅馆门口围得水泄不通了。他们都在身上画十字,并且伸出两根手指指向我。
经过一番周折,我才向一位乘客打听清楚刚刚那些人是什么意思。他一开始不肯说,得知我是英国人之后,他才解释说那是一种抵御“邪恶之眼”的魔法或护身咒。
刚要出发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拜访一个陌生的人就听到这种说法,我有些不太高兴。但是每个人看上去都如此善良、悲伤又富有同情心,我也不禁有些触动。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旅馆前那群独特的人在身上画十字的情景。他们围着宽宽的拱门站成一圈,身后是枝繁叶茂的夹竹桃和种在绿色的桶里的橘子树,集中摆在庭院中央。
车夫上了车,肥大的亚麻裤盖住了整个箱座的前部。他挥舞着大大的鞭子,用力抽打着那四匹小马。小马并排奔跑起来,我们就这样踏上了旅程。
随着马车向前奔驰,窗外的美景渐渐减弱了我对那些鬼怪的恐惧。尽管我能听懂其他乘客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我也不能从窗户里把他们扔出去。我们前方是一个布满森林的绿油油的缓坡。到处是陡峭的小丘,顶上有矮树丛和农居,单调的山墙一直延伸到路的尽头。山上果树茂盛,繁花盛开,有苹果花、李子花、梨花和樱桃花。我还不时看到绿色的草地上点缀着树上掉落的花瓣。这片绿色的小山被称为“密特尔之地”,道路就在这片郁郁葱葱的山间穿行,有时又被倾泻而下的茂密的松林遮掩得时隐时现。虽然路被遮掩着,但是我们仍然充满激情地一路奔驰。我不清楚为什么要那么急,但是很明显车夫想早点赶到波戈隘口。有人告诉我这条路在夏季风景极好,但是现在冬天的积雪痕迹还在,路况也不是很好。这里的路跟喀尔巴阡山一带大多数道路都不一样,因为过去这里的王公很少修缮,以免土耳其人怀疑他们准备联合别国军队,让本来一触即发的战争加速爆发。
走过密特尔之地绿色的山丘,那些布满密林的高耸入云的陡山就是喀尔巴阡山。它们矗立在我们左右,夕阳照在美丽的山上,幻化出美妙的色彩。山巅的阴影处是深蓝色和紫色,草和山岩混杂的地方是绿色和棕色。一眼望去都是参差不齐的岩石和尖耸的峭壁,远处是雄伟的雪峰。山上似乎到处都是大大的裂缝,透过这些裂缝看去,太阳正在下沉,我们不时看到山间的瀑布反射着微弱的白光。当我们从下面绕过一座山,走在弯弯曲曲的路上,向一座似乎横在我们正前方的陡峭的雪峰进发时,车上的一个乘客碰了碰我的胳膊:“快看!Isten szek!上帝的宝座!”然后他开始在身上虔诚地画十字。
我们在漫长的路上奔波时,夕阳在我们身后越来越低,夜幕悄悄地将我们包围。山峦的雪顶上仍然留有一抹晚霞,给它增加了一种柔和而冷静的粉色。路上的行人都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穿着漂亮的服装。我还注意到,这里的人普遍患有甲状腺肿大。路边有很多十字架,我的旅伴们在经过的时候都要画十字。我们还不时遇到跪在圣坛前面的农夫或农妇,即使我们从他们身边经过也浑然不觉,似乎完全沉浸在宗教情感中,眼睛和耳朵已不理会外面的世界。我看到了很多新鲜事,比如放在树上的干草垛,颇具美感的低垂的桦树枝,白白的枝干在柔美的绿叶掩映下闪烁着银子一般的光泽。
在路上,一种当地农民常用的马车不时从我们身边经过。这种马车的车架很长,像蛇一样,专门为了适应当地崎岖的山路。很显然车上的人是回家的农民。捷克人穿着白色羊皮衣,而斯洛伐克人则穿着彩色羊皮衣,还带着像长矛一样有一根长柄的斧头。随着夜晚的到来,气温也开始变低了,暮色似乎渐渐与橡树、山毛榉、松树等所有的树影融为一体。尽管山谷幽深,但是当我们沿路向上走的时候,黑色的冷杉还是能在白色积雪的映衬下看得分明。有时候,由于松林的遮挡,前面似乎没有路了,树上遍布灰影,营造出一种非常诡异而又庄严的效果,让人不禁联想到傍晚时由于夕阳和奇形怪状的云朵所引起的可怕的幻想。有时,那些山丘非常陡峭,马儿不用车夫勒缰绳就会自动减慢速度。我希望下车跟在后面步行,但是车夫不同意:“不行,不行,你不能下车,这里的狗太凶了。”然后他环视一周,似乎想在其他乘客脸上找到赞许的表情,故作严肃地说:“在你入睡之前,还会遇到很多类似的情况。”路上他只停了一次,是为了把灯点亮。
天色渐暗,乘客们都莫名兴奋起来,他们不停地跟车夫讲话,仿佛要催促他加快速度。车夫一边无情地挥舞着鞭子,一边大声吆喝着,让他的马儿跑得更快。透过黑暗能看到一些灰蒙蒙的地方,仿佛那里是山的出口。乘客们更加兴奋了。这辆疯狂的马车像弹簧一样颠簸着,又像在暴风雨中摇晃的一叶扁舟,我不得不紧紧地抓住扶手。路变得平坦一些,马车快得就像要飞起来。两边的大山离我们更近了,好像要压下来一样。我们正在驶入的就是波戈隘口。
几个乘客开始送给我“礼物”-带着一股子虔诚劲,并且不容拒绝。这些形形色色的礼物都非常怪异,但是都带着一份简单和美好。有人送我祝福,有人向我画十字,跟比斯特里察旅馆外的那些人一样。在我们行进途中,车夫的身体向前倾着,车厢里两侧的乘客都紧紧扒着车窗,紧张地向外看去。很明显外面有重要的事情正在或者即将发生,但是我问的每一个乘客都不愿意向我透露一星半点。这种兴奋状态持续了一会儿。后来我们看到隘口就在右前方,空中阴云密布,层层卷卷,还不时传来沉闷的雷声。似乎一座山隔出了两重天,我们现在正要进入的是一个电闪雷鸣的世界。
我开始小心把我载到伯爵处的马车。每一刻我都期望看到黑暗中出现一束炫目的灯光,但是四周都是黑暗。唯一的光亮就是我们的车灯发出的摇摆不定的灯光,透过灯光还能看到奋力拉车的马儿呼出的白气。看得出来,我们正行驶在白色的沙路上,但是前方没有任何车辆。乘客们高兴地收回身来,松了口气,跟我的失望形成鲜明的对比。我开始考虑应该怎么办,这时车夫看了一下表,然后跟其他乘客用一种轻微得几乎听不出来的声音嘀咕了一句什么,好像是“提前一个小时”。然后他转向我,用比我还差的德语说到:“这里没有车,毕竟绅士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现在他要去博科维纳,明天或者后天回来。最好是明天。”
他正说着,马儿开始嘶鸣,变得不安分起来,车夫不得不拉紧缰绳。这时一辆四匹马的马车从后面追上来,停在我们马车的旁边。乘客们开始尖叫,并且不停地在身上划十字。透过车灯的光亮我看了一下那辆车,四匹马都是黑色的,毛皮油光水滑。车夫是一个留着长长的棕色胡子的高个子男人,戴着一顶大大的黑帽子,把脸都藏了起来。我只能看到一双精光闪烁的眼睛,当他转向我们的时候,这双眼睛在灯光下看上去是红色的。
他对车夫说:“你今晚提前到了,我的朋友。”车夫结结巴巴地回答:“那位英国绅士有急事。”陌生人又说:“我猜这就是你希望他去博科维纳的原因吧。你骗不了我,我的朋友,我都知道。我的马跑得也快。”
他说话的时候面带微笑,他的嘴在灯光下看上去很难看,嘴唇鲜红,牙齿很尖,并且像象牙一样白。一位乘客跟另外一位小声地嘀咕了一句伯格的《勒诺》中的台词:“死人跑得快。”
那个奇怪的车夫显然听到了这句话,因为他向那个人诡异地一笑。那位乘客把脸别过去,伸出两根手指在胸前画十字。“把那位先生的行李给我。”那个车夫说。我的包很快被递了出去,放到了那辆车上。随后我从马车的一边出来,因为两辆马车离得很近,那位奇怪的车夫伸手扶我上了他的车,他的手像铁钳一样有力。他一定力大无穷。
车夫一言不发地抖了一下缰绳,四匹马掉转方向,我们的马车冲进了夜幕之中。我回头望了一眼来时的马车,还能看到灯光下那些马儿呼出的白气,我的旅伴们在自己的身上划着十字。车夫甩了一下鞭子,冲着马吆喝了一声,重新踏上了去博科维纳的路。目送他们消失在夜幕中之后,我突然感到一阵寒冷,一种孤独感包围着我。车夫扔给我一件斗篷和一条毛毯,用流利的德语说:“晚上冷,先生,我的主人吩咐我照顾好您。如果您需要的话,座位下面有一瓶李子白兰地。”
我没有喝酒,但是知道座位下有瓶酒已经让我感到欣慰。我感到有些奇怪,但是并不害怕。现在想想,如果必须二选一的话,我应该喝下那瓶酒,也不应该清醒地面对这次未知的夜行。马车艰难地向前走着,然后转了个大弯,继续前行。我感觉我们是在兜圈子,于是留心了一下路上明显的标志,发现事实果真如此。我真想问一下车夫这是什么意思,但是退缩了,因为我想,就目前的处境看来,如果他是故意拖延时间的话,提出异议不会对解决问题有任何帮助。
过了一会儿,我想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于是擦亮了一根火柴,借着火光看了看表:还差几分钟就到午夜了。这令我感到震惊,因为最近的经历让我想起了那个广为人知的关于午夜的传说。我焦虑地等待着。
前方远处某户农家的狗开始号叫,那种叫声拖着长音,夹杂着痛苦,似乎对什么感到恐惧。另一只狗也开始跟着叫,越来越多的狗都叫起来,直到吹过隘口的风中都弥漫着这种叫声。随后出现了一种狂野的号叫,这种叫声好像来自四面八方,远得超乎想象,刺破了黑暗。
当哀号响起的时候,马匹开始躁动不安,在车夫的安抚下它们镇静下来,但是却瑟瑟发抖,汗流浃背,就像突然受惊奔跑过一样。随后,当远处山中传来更响更尖的狼的叫声时,不光是马,我也同样感到害怕。我的脑中甚至闪过跳车逃跑的念头。马儿上蹿下跳,暴跳如雷,车夫必须用尽全力才能不让它们脱缰。过了几分钟,我已经习惯了周围的声音,马也开始安静下来。车夫跳下马车,站在马的前面。
他温柔地抚摸它们,不时冲它们的耳朵低语着什么,就像驯马师一样。车夫的做法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因为在他的爱抚下,马尽管还在发颤,但是又变得温顺起来。车夫又回到座位,抖动缰绳,马车开始疾驶起来。这次,沿着与隘口相反的方向走了一会儿之后,突然转向了右边一条狭窄的小路。
很快我们就被树丛包围起来,有些地方两旁的树围成了一个拱门,我们行驶其中仿佛在穿过隧道。路旁怪石嶙峋。尽管在车厢里面,还是能听到风吹过岩石发出的时高时低的声音,像口哨,又像叹息。树枝也被风吹动,互相拍打。气温越来越低,空中开始飘下小雪,我们以及我们周围的事物很快就披上了白色的毯子。狗的叫声还是会随风传来,尽管随着马车不断前行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是车夫却显得心神不宁。他不停地左右张望,但是除了一片黑暗我什么都看不到。
突然,我们的左边出现了一簇微弱闪烁的蓝色火焰。车夫也看到了。他检查了一下马匹,跳下车,消失在了黑暗之中。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随着狼嚎的逼近越来越不知所措。我正纳闷,车夫又突然出现了,一言不发地上了马车,再次出发了。我想我一定是睡着了,不停地梦到刚才的场景,因为好像一切都在无止境地重复。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切就像一场可怕的噩梦。只要火焰离路不远,我就能借着火光透过黑暗看到车夫的动作。他会迅速地走到有蓝火的地方,捡几块石头拼成某种图案。火一定非常微弱,因为似乎并不能把周围照亮。
一度出现了一种奇特的视觉效果,当车夫站在我和火焰之间时,并没有挡住火焰,因为我仍然能看到火焰诡异地摇曳。这让我感到吃惊,但是因为只是一瞬间的事,我以为我的眼睛因为在黑暗中尽力睁大出现了幻觉。然后有一段时间没有蓝色火焰,我们就在黑暗中不断前行,周围都是狼叫,好像它们也坐着马车紧紧跟着我们。
后来有一次,车夫走得比以前都远,就在他不在的时候,马突然开始战栗,比以前都严重,还发出恐惧的嘶鸣。我不明白它们怎么了,因为狼已经停止号叫。但是这时月亮从乌云中露出脸来,出现在一座覆盖着松树的凹凸不平的山坡后面。借着月光我看到一群狼围着我们,露着白色的牙齿,伸着红色的舌头,长得高大健壮,毛又浓又长。狼群寂静下来甚至比号叫还要可怕百倍。我已经害怕得浑身瘫软。一个人只有如此近距离地面对这些恶魔时才能真切地体会到它们的可怕。
突然,狼群又开始号叫,仿佛受到了月光的影响。马开始乱蹦乱跳,眼睛无助地四处张望,看上去非常痛苦。但是那可怕的狼群把马都包围起来,它们逃不掉。我大声喊着车夫,因为在我看来,似乎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试着冲出包围圈。为了帮助车夫靠近,我大喊大叫,使劲敲打车厢,希望噪音能够吓退旁边的狼群,给车夫制造一个靠近的机会。我不清楚车夫是怎么回来的,但是我听到了他的声音,在高声喊着什么。循着声音望去,车夫正站在路上。他挥舞着长长的胳膊,好像要挥开某种障碍。狼群开始不停地后退。正在此时一大块云彩遮住了月亮,我们又陷入了黑暗。
我的眼睛适应黑暗之后,发现车夫正爬上马车,狼群消失了。这一切都如此荒诞离奇,我开始感到强烈的恐惧,吓得说不出话来,也动弹不得。我们在路上的时间似乎漫长得没有尽头。因为云遮住了月亮,所以我们完全陷入黑暗之中。
我们一直在爬坡,中间偶尔下坡,但是主要是在上坡。突然,我感到车夫正牵着马走进一座巨大、破损的城堡的庭院,高高的窗户里黑漆漆的,没有一丝光亮,破损的城垛在空中留下凹凸不平的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