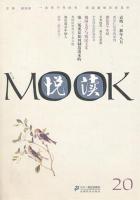随着《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节目在中央电视台10套《百家讲坛》的热播,民间关于“红学”的讨论又掀起一个高潮。对于刘心武先生勇于钻研学问,并以民间红学家的身份向传统“红学”挑战的精神,笔者深感敬佩。然而,认真辨析了刘心武先生的若干论述之后,却又深深地感到他的研究方法和得出的学术观点,实为在下所难以苟同。故,笔者不揣冒昧,特写下这么一篇《“秦学”献疑》,与刘心武先生商榷,并与诸位“红学”爱好者共同讨论。
一、 秦可卿是否出身高贵
秦可卿研究是刘心武先生“秦学”研究的核心,而在这个核心当中,所谓秦可卿的原型人物乃康熙废太子胤礽之女,理亲王弘皙之妹,又是刘先生全部立论的中心和归依点。围绕着这一中心论点,刘先生主要从四个方面阐述了秦可卿这个人物必然“出身高贵”的理由:
1. 秦可卿是宁国府的重孙媳妇。贾府是“四大家族”之一,是名门望族,其挑选媳妇,必然讲究门当户对,身份相当。秦可卿能嫁入宁国府这样的大家,故绝不会是小官宦人家的养女,而只能是其有“高贵”血统的人。
2. 秦可卿具有非凡的政治才能,深受贾府上下的喜爱,故不可能是小户人家出身,而应该是高等贵族出身甚至皇室后裔。
3. 秦可卿在太虚幻境中为警幻仙姑之妹,这说明她的地位非常特殊。
4. 秦可卿死后备极哀荣: 睡的是曾为“义忠亲王老千岁”准备的上等棺木,发丧时北静王也来路祭,大明宫内相戴权也“打伞呜锣,亲来上祭”。如此风光,如此招摇,都说明秦可卿实具有“公主”一级的身份。
然而,事实果真如刘心武先生所说的那样吗?秦可卿其人是否真的具有如此非凡的“高贵”出身呢?我们不妨对刘先生提出上述四大理由进行一番剖析,或许能澄清不少的疑问。
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贾府的婚姻。刘心武先生在《贾府的富贵眼光》一讲中,花了很大的篇幅论述贾府之中势利之风盛行。言下之意,贾府既系名门,上上下下又都是“一个富贵心,两只体面眼”,所以其为子孙挑选配偶,必然不会看中一个“从养生堂抱来的野婴”,而只能选择出身高贵的女子。从泛泛而言的角度上讲,刘先生的论述自然是没错的。然而,具体到为子孙娶妻婚配的问题上,贾府的掌权者们又是否一定就是按照所谓“富贵心”、“体面眼”的势利原则来行事的呢?在这一点上,刘先生却显然没有认真地去听一听贾母自己的意见。我们还是来看看小说第二十九回中,贾母如何阐释她的择(孙)媳标准的:
贾母道: “上回有和尚说了,这孩子命里不该早娶,等再大一大儿再定罢。你可如今打听着,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配的上就好,来告诉我。便是那家子穷,不过给他几两银子罢了。只是模样性格儿难得好的。”(第二十九回)
很清楚,贾母为宝玉择妻,她所看重的,就恰恰不是什么门第,而是那女孩子的“模样”和“性格儿”,而且顺序绝对是“模样”第一,“性格儿”第二!——为什么要把“模样”放在“性格儿”之上呢?说穿了,道理也很简单,因为“模样”是天生的,改不了,“性格儿”却可以慢慢调教。——而至于那姑娘是否“根基富贵”,贾母表示得也很明白,这竟然可以“不管”,“便是那家子穷,不过给他几两银子罢了”。从小说的实际描写来看,贾蓉在宁国府的地位,也未必比贾宝玉在荣国府的地位更高。贾母为宝玉择偶的标准,居然是相貌第一,性格第二,门第都可以不问。你又怎能保证贾珍、尤氏在为贾蓉娶媳妇的时候,不会是持有同样或相似的想法呢?所以,秦可卿嫁入贾府,这并不必然说明她一定出身“高贵”!
不错,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贾家上上下下都是一双富贵眼睛”。不过,人性却是复杂的,具体到为子孙选择合适的媳妇的问题上,家长们也完全可能各有各的特殊考虑,并不一定就非得受势利之风的束缚不可。毫无疑问,在贾府的众多媳妇当中,有一多半都是豪家名宦出身,如史太君、王夫人、王熙凤、李纨等等。但贾赦之妻邢夫人混迹其中,却无疑是一个明显的例外。据小说第七十五回交代,这邢家原也有三个姐妹,两个兄弟。只是因为当年邢夫人嫁到贾府,把绝大部分的家资都当作嫁妆带了过来,于是就弄得两个妹妹、两个兄弟生活日益窘困,不得不相继厚着脸皮,跑到贾府前来投靠。——那邢家仅仅因为筹备了一次像样一点的嫁妆,就弄到了这步田地,显然绝不可能是什么显赫的世家。虽也不至于是那种“极卑污”的“小家”(脂砚斋语),但肯定不可能是那种能与贾、史、王、薛相提并论的人家。而邢夫人这么一个并非出身显赫家庭的女人,竟然也能成为贾赦的正房、荣国府堂堂正正的大太太,这对于我们认识秦可卿这么一个小官宦的养女、从养生堂抱来的野婴竟然也可以嫁入宁国府,是不是多少也有些启示的意义呢?自然,刘心武先生可以辩解说,那邢夫人是贾赦的填房,并非元配。可是,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展到邢夫人的侄女——邢岫烟的身上,就连这样的辩解,也是断难成立的。众所周知,作者在小说中,是一再地描写了这位邢姑娘的家境贫寒。如第四十九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诸位小姐都穿上了华丽的斗篷,惟独邢岫烟“仍是家常旧衣,并无避雪之衣”。第五十七回,又写邢岫烟受下人欺负,大冬天里不得不将棉衣典当换钱。而就是这样一个“钗荆裙布”的女儿,最后却被薛姨妈给看中,聘给了薛蝌做媳妇。而且,她所做的,还不是薛蝌的继配,而正是元配!且看小说第五十七回中的这一段:
因薛姨妈看见邢岫烟生得端雅稳重,且家道贫寒,是个钗荆裙布的女儿,便欲说与薛蟠为妻。因薛蟠素习行止浮奢,又恐糟踏人家的女儿。正在踌躇之际,忽想起薛蝌未娶,看他二人恰是一对天生地设的夫妻,因谋之于凤姐儿。凤姐儿叹道: “姑妈素知我们太太有些左性的,这事等我慢谋。”因贾母去瞧凤姐儿时,凤姐儿便和贾母说: “薛姑妈有件事求老祖宗,只是不好启齿的。”贾母忙问何事,凤姐便将求亲一事说了。贾母笑道: “这有什么不好启齿?这是极好的事。等我和你婆婆说了,怕他不依?”因回房来,即刻就命人来请邢夫人过来,硬作保山。邢夫人想了一想: 薛家根基不错,且现今大富,薛蝌生得又好,且贾母硬作保山,将计就计便应了。(第五十七回)
薛家和贾家同属“四大家族”,其豪富的程度,甚至还超过了贾家。既然“钗荆裙布”的贫家女儿邢岫烟仅仅因为“端雅稳重”,就可以嫁到薛家,成为薛蝌的元配正室,那么,作为小官宦人家养女的秦可卿,又如何做不得宁国府贾蓉的媳妇呢?把上述薛姨妈的择媳标准,与前述贾母的那番表示结合起来,我们倒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贾家、薛家这样的大家族中,除了所谓“富贵心”、“体面眼”之外,所通行的另一套婚配标准。固然,“四家皆联络有亲”,搞点门当户对的政治联姻,对这样的大家族来说也是常有的事情,但这却并不意味着其每一个子弟都娶妻必出名门,“模样”和“性格儿”,也同样可能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如何能仅凭秦可卿的婚配情况,就一口断定秦可卿的出身必然另有隐情呢?这恐怕也很难说是一个严肃的结论吧?
其次,关于秦可卿的政治才能。在这个问题上,刘心武先生的论述,亦同样缺乏严肃性可言。刘先生依据秦可卿具有非凡的政治才能,深受贾府上下的喜爱,便断定她不可能是小户人家出身,而只能出身高贵。然而,历史上出身寒微,却深具政治才能和政治远见的人,又何尝少见呢?男人且不去说他,单看历史上许多杰出的女性,很多就并非什么天潢贵胄。如武则天不过是木材商的女儿,朱元璋的皇后马氏,亦不过是一乡下土财主的养女。既然武则天、马皇后能够凭借过人的天赋和自身的努力,成为中国杰出的女政治家和一代贤后,那么,小家出身的秦可卿能聪明过人,成为贾母“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又何足为怪?一定要把能力与出身挂起钩来,这是不是又有些“血统论”的思维残迹呢?窃以为,刘先生的思维在这一点上,也多少进入了逻辑的误区。
其三,关于秦可卿与警幻仙姑。刘心武先生以秦可卿系警幻仙姑之妹的理由,来论证她的地位特殊。但刘先生却可能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 实际上,凡在太虚幻境中注过册的女子,都是警幻仙姑的妹子。何以见得?我们来看太虚幻境中,包括警幻仙姑本人在内的众仙子是如何称呼林黛玉的生魂的:
……又听警幻笑道: “你们快出来迎接贵客!”一语未了,只见房中又走出几个仙子来,皆是荷袂蹁跹,羽衣飘舞,姣若春花,媚如秋月。一见了宝玉,都怨谤警幻道: “我们不知系何‘贵客’,忙的接了出来!姐姐曾说今日今时必有绛珠妹子的生魂前来游玩,故我等久待。何故反引这浊物来污染这清净女儿之境?”宝玉听如此说,便吓得欲退不能退,果觉自形污秽不堪。(第五回)
林黛玉的生魂被仙姑们称为“绛珠妹子”。如果按刘先生的逻辑,秦可卿因为是警幻仙姑的妹妹,便具有高贵非凡的出身,那么,黛玉的生魂在太虚幻境中,与警幻同样以姐妹相称,这是否又说明她也是某个皇室成员的女儿呢?再来看警幻仙姑将可卿许配于宝玉时,她所说的那番原话:
……今既遇令祖宁荣二公剖腹深嘱,吾不忍君独为我闺阁增光,见弃于世道,是特引前来,醉以灵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将吾妹一人,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许配于汝。今夕良时,即可成姻。不过令汝领略此仙闺幻境之风光尚如此,何况尘境之情景哉?而今后万万解释,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第五回)
请注意,那警幻的原话是“再将吾妹一人,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许配于汝”。从句式上看,她显然并不止有秦可卿这么一个妹妹。所谓“吾妹一人,乳名兼美,字可卿者”,也不过是她众多妹妹中的一个罢了。
最后,我们来说一说秦可卿的出殡何以如此风光,何以如此兴师动众。按小说交代,秦可卿死后,她睡的是曾为“义忠亲王老千岁”准备的上等棺木,发丧时北静王也来路祭,大明宫内相戴权也“打伞呜锣,亲来上祭”。对此,刘心武先生的意见,自然是认为秦可卿的出身非凡,具有“公主”一级的隐秘身份。然而,这样的判断在逻辑上却十分危险。因为在明、清时代,官员“逾制”的现象可谓十分普遍。从建筑、饮食、服饰、出行,到婚丧嫁娶,都不乏下级僭越上级,甚至臣僚僭越皇家的例子。别的不说,就《红楼梦》中的宁国府而言,早就有人指出其建筑形制和规模都属于严重逾制。按清朝《钦定大清会典》规定,亲王府、世子府、贝勒府、贝子府其中轴线上,只能包括正门、正殿、后殿、后寝、后楼五重建筑。然而,《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写“宁国府除夕祭宗祠”,宁国府的中轴线上却分明出现了九重建筑: “宁国府从大门、仪门、大厅、暖阁、内厅、内三门、内仪门并内塞门,直到正堂,一路正门大开,两边阶下一色朱红大高照,点的两条金龙一般。”——正式的法律规定是“五重”,宁国府实际上却修造成了“九重”,按刘心武先生的逻辑,这是否能说明贾敬、贾珍也有什么了不起的皇族血统呢?很显然,我们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而惟一的解释只能是“逾制”乃是当时的一种相当普遍的风气。还是回到秦可卿的丧事上。秦可卿的出殡何以如此风光?说穿了,道理也并不复杂,因为贾珍自以为对秦可卿之死有愧于她,他不惜以严重逾制的方式来补偿他这个最为心爱的儿媳。而小说中的贾府,与现实中的曹家不同。现实中,曹家仅仅是内务府包衣,属于皇家私奴。而小说中的贾府,却是“国公”一级的封爵,是历代王朝仅次于王爵的最高封爵(异姓臣子一般不得封王)。宁国公发狠要摆阔,王公大臣,谁又好意思不给赏脸呢?大明宫内相戴权又为何“打伞呜锣,亲来上祭”?因为这样的场合,对于那些内宫太监来说,还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发财的机会。稍后,小说便写了贾珍为贾蓉捐官,给那个大明宫掌宫内相戴权,一次性地送了一千二百两白银。而既然要拿人家的银子,其“打伞呜锣”,前来为人助威,那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综上所述,刘心武先生举出的四大理由,都远不足以认定秦可卿具有皇族的血统。而真要认真起来,甲戌本中倒有两条非常重要的脂批,可以说是对所谓秦可卿出身“高贵”说的有力否定。不知何故,刘先生对此却总是在回避不谈。其批云:
出明秦氏究竟不知系出何氏,所谓寓褒贬、别善恶是也。秉刀斧之笔、具菩萨之心,亦甚难矣,如此写出可儿来历,亦甚苦矣。又知作者是欲天下人共来哭此情字。(甲戌本第八回双行夹批)
写可儿出身自养生堂,是褒中贬。后死封龙禁尉,是贬中褒。灵巧一至于此。(甲戌本第八回眉批)
——何谓之“褒中贬”?曹雪芹写秦可卿聪明、美丽,都是在“褒”奖她。但此处写她出身自养生堂,却是在“贬”她。因为她具有生性风流、淫荡的特点。秦可卿死于“淫丧天香楼”,这是桩丑闻、秽事,本应该“贬”她,但秦氏托梦,为贾府的长远利益出谋献策,又有功。所以,作者特意写贾珍给贾蓉捐了个“五品龙禁尉”,让秦可卿死后享受到了正五品命妇——“恭人”的哀荣。这又是在“褒”她了。如果按刘心武先生的说法,秦可卿本是金枝玉叶,地位相当于郡主,写她的出身,又何以是“褒中贬”呢?反过来,本来应该成为郡主,甚至公主的人,死后仅仅得了一个“恭人”的诰封,这又哪里说得上是“贬中褒”呢?自然,脂砚斋的观点并不能完全与曹雪芹的想法划等号。然而,无论是刘心武先生,还是赞同刘先生说法的周汝昌老先生,都承认脂砚斋是曹雪芹生前最亲密的知己,所谓“一芹一脂”,思想上、情感上皆亲近之至,二者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大的分歧。如何惟独在秦可卿的问题上,不肯听一听脂批的见解呢?对此,笔者倒不得不为刘先生立论的主观,而深深地感到遗憾了。
二、 宁国府真是“三世单传”吗?
刘心武先生在论述秦可卿出身“高贵”的同时,显然提及了宁国府中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所谓“三世单传”的问题。依刘心武先生的看法,宁国府既然是贾敬、贾珍、贾蓉“三世单传”,那么,家长们为贾蓉选媳妇,一定是慎之又慎。故而,那秦可卿绝不会是“从养生堂抱来的野婴”,只能具有高贵非凡的血统。然而,《红楼梦》中的宁国府真的是“三世单传”吗?在笔者看来,这本身倒也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因为种种迹象来看,宁、荣二府的血脉传承,并不像小说在字面上交代那样简单,而是另有隐情!
按《红楼梦》之现行本交代,荣国府史老太君(即贾母)有两个儿子,长即贾赦,次即贾政。贾赦有二子一女,即贾琏、贾琮、贾迎春。贾政有三子二女,即贾珠、贾宝玉、贾环、贾元春、贾探春。如此构成了荣国府族谱的主要框架。然而,很多读者可能并没有想到,在曹雪芹的心目中,那个贾赦其实并不是贾母的儿子,甚至根本就不是荣国府的成员。他实际上应该是宁国府的人,是贾敬的亲兄弟!连带着邢夫人、贾琏、贾琮、贾迎春,也都不是荣国府的人,而属于宁国府的成员。今本(包括脂评本与程高本)虽然在纸面上声称荣国府“长子贾赦袭着官”,但实际上,作者的潜意识中,却始终没有把贾赦真正当作荣国府的人,而是写着写着就露出了破绽,自觉不自觉地显示了贾赦原本是宁国府老二的身份。
破绽之一: 在书中,贾琏被称为“二爷”。按小说交代,贾赦有二子,即贾琏和贾琮。贾琮年龄比贾宝玉还要幼小,显然是弟弟,而不是哥哥。贾琏既上无长兄,居然也称起“二爷”来,岂不可怪?如果把贾政这一支也算进来,假定贾珠年长于贾琏,这样贾琏倒是可以称“二爷”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 贾宝玉为何也被称为“二爷”?显然,这样来排行计算,也是讲不通的。但如果我们把贾赦这一支算到宁国府中,贾琏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贾敬与贾赦是亲兄弟,那么,贾敬之子贾珍就是宁国府“玉”字辈的老大,贾赦之子贾琏就是老二。所以,“宝二爷”实与“珠大爷”相对,同为荣国府的人。“琏二爷”实与“珍大爷”相对,同为宁国府的人。
破绽之二: 第六十八回,“酸凤姐大闹宁国府”,王熙凤在数落贾蓉的时候,竟然把已死的贾敬称为贾琏的“亲大爷”: “出去请大哥哥来。我对面问他,亲大爷的孝才五七,侄儿娶亲,这个礼我竟不知道。我问问,也好学着日后教导子侄的。”这种话,也只有在贾敬与贾赦是亲兄弟,贾琏是贾敬的亲侄儿的情况下,才有成立的可能。
破绽之三: 第七十五回,贾赦居然怂恿贾环争取将来“世袭”爵位。且看以下一段文字:
贾赦乃要诗瞧了一遍,连声赞好,道: “这诗据我看甚是有骨气。想来咱们这样人家,原不比那起寒酸,定要‘雪窗荧火’,一日蟾宫折桂,方得扬眉吐气。咱们的子弟都原该读些书,不过比别人略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时就跑不了一个官的。何必多费了工夫,反弄出书呆子来。所以我爱他这诗,竟不失咱们侯门的气概。”因回头吩咐人去取了自己的许多玩物来赏赐与他。因又拍着贾环的头,笑道: “以后就这么做去,方是咱们的口气,将来这世袭的前程定跑不了你袭呢。”贾政听说,忙劝说: “不过他胡诌如此,那里就论到后事了。”说着便斟上酒,又行了一回令。(第七十五回)
——贾赦怂恿贾环,说什么“将来这世袭的前程定跑不了你袭呢”,自然是居心叵测,有意给贾政、王夫人的嫡子贾宝玉找麻烦。但这里又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问题。按《红楼梦》之现行本交代,贾赦自己现袭着荣国府的爵位,他又不是没有儿子。如一位“红迷”朋友所说,“日后他的爵位传与贾琏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此怂恿贾环夺嫡,岂不更是给自己的亲生儿子找麻烦?而贾赦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显然只能有一个解释,即在作者的潜意识中,根本没有把他当成荣国府的嫡传爵公,而是依然把他看成了宁国府“文”字辈的老二。
诸如此类的破绽,在书中实有许多。这些迹象都无不指向一点,贾赦实为宁国府贾敬之弟。而把他写成贾母的儿子、贾政的哥哥,不过是曹雪芹不得已采用的改笔!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作者不得不作如此改动呢?笔者看重王熙凤这个人物的作用。今本《红楼梦》(或者叫《石头记》)的主要描写对象是以贾宝玉为中心的大观园群芳,而不再是宁府的那些秽事。主要描写对象发生变化,主要人物活动的空间,亦由宁国府转移到荣国府。王熙凤作为曹雪芹精心塑造的一个人物形象,在贾府由盛而衰的过程中,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么一个人物,理应浓墨重彩,但她原来作为宁国府孙媳的身份,却显然限制了她经常出没于荣国府中的情形。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调整她的身份,把她由宁国府孙媳的身份,置换为荣国府孙媳。只是这样一来,贾赦连带着邢夫人、贾琏、贾琮、贾迎春的身份,也都不能不改了。但贾赦、贾琏父子在作者的心目中作为宁国府成员的情形,已由来已久,早就进入了其创作的潜意识中。所以,曹雪芹才一方面声称荣国府“长子贾赦袭着官”,但另一方面却又鬼使神差般地让贾赦说出真正袭爵之人不可能说出的话来,同时继续让贾琏保留了“二爷”的称呼以及作为贾敬亲侄儿的身份!而因为一个人,竟然可以改变整整一个家庭的全部血缘关系,这正是《红楼梦》作为小说,不同于现实的地方!
明白了《红楼梦》中隐藏的上述奥秘,刘心武先生反复强调的所谓宁国府“三世单传”的问题,实际上,也就不攻自破了。那宁国府何尝“单传”?贾敬一支,有贾珍为其后,是谓之“珍大爷”,贾赦一支,有贾琏为其后,是谓之“琏二爷”,正与荣国府的“珠大爷”、“宝二爷”遥遥相对!只是因为作者不得已对贾赦一支的血脉进行了调整,才造成宁国府所谓“单传”的假象。刘心武先生没有从假象中看出作者真实的想法,却径直以这个假象来作为立论的依据,这究竟让人说什么好呢?无疑还是那四个字: 令人遗憾!
澄清了宁国府所谓“三世单传”的误会,刘心武先生在“揭秘”系列中提到的荣国府贾赦居长反住偏屋,贾政为次反居正堂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刘先生自己的解释:
……但是当时康熙实在是太喜欢曹家了,也特别喜欢李煦,喜欢贾母娘家她哥哥,所以康熙就亲自问李煦,说你看一看曹寅的侄子里面,有没有好的,选一个过继给曹寅,虽然这个人死了,但是还可以名义上过继一个儿子,好让他侍奉李氏,来接任这个江宁织造,后来李煦就很认真地帮他挑选,挑选曹寅的侄子曹,挑选曹过继给曹寅,也就是过继给李氏,成为他的一个儿子,而且曹又生了一个儿子曹霑,就是曹雪芹的原型。所以他根据自己家族的体验,他的父亲是过继给祖母的,所以你再回过头来看《红楼梦》,你觉得它太写实了,他写贾母和贾政的关系非常淡薄,她喜欢她孙子,因为根据封建社会的观念,儿子如果不是亲生的是过继的话,孙子就一定是亲生的。儿子老大了才过来,双方论骨肉比较困难,孙子从小可以瞒着他,是不是?长大你再告诉他或他自己想办法知道,是另外一回事,就可以很亲地当作自己骨肉的延续。所以你看,曹雪芹为什么这么写,就是因为他有生活原型,他的父亲曹就是贾政的原型,原型人物,曹不是贾母的亲儿子,但是又过继给贾母,继承了荣国府的家业,所以他住在荣国府的正堂大院。实际上荣国府只有这么一个过继的儿子,为什么他要写贾赦呢?这点就是他发挥他的艺术想像力,以及他的艺术虚构了,如果太忠实于生活的真实写起来就很麻烦,所以他就归并同类项,因为贾赦确实在小说里面是贾政的哥哥,在生活原型当中也确实是曹的哥哥,明白吗?他和贾政之间他们是亲兄弟,懂这个道理吗?但是他没有过继给贾母,明白吗?他没过继给贾母,他怎么能住在荣国府的院里面呢?他当然是在另外一个院落居住,明白这个逻辑了吧。是不是,对吧,曹雪芹因为太忠于生活原型了,所以写来写去写成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刘先生是否感到了自己这一番解释的自相矛盾。一会儿说“《红楼梦》太写实了”,“曹雪芹太忠于生活原型了”,一会儿却又说什么“太忠实于生活的真实写起来就很麻烦,所以他就归并同类项”,那曹雪芹对于生活,他到底是“忠实”,还是不“忠实”呢?其实,只要弄清楚贾赦原是宁国府的一员,根本用不着扯到曹颙、曹的那一桩公案上去。为什么贾赦居长,他反住偏屋?很简单,他原本就不是荣国府的子孙。只是作者后来不得已调整了宁、荣二府的血脉传承,才让他在形式上成了贾母的大儿子。又为什么贾政为次,他反居正堂?因为他本是贾母的独子,他才是真正袭着爵位的荣国公!
三、 《红楼梦》是“写实”,还是虚构
经过前面两部分的讨论,我们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 《红楼梦》究竟是一部以“写实”为主的“自传”,还是一部以虚构为主的小说?刘心武先生显然倾向于前者。在他的“揭秘”系列中,他多次提到这样的论断,典型的如以下一些言论:
“《红楼梦》可以拿出很多证据证明,它是一个写实的作品,是带有自叙色彩的作品,是一个写人物从原型出发的作品。”(《秦可卿的原型》)
“我就知道小说有不同的类别,其中有一种带有自叙性,自传性,就是小说的人物是有生活原型的。”(《贾府婚配之谜》)
“上一讲我们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贾氏宗族在娶媳妇上是不含糊的,第二个结论就是《红楼梦》是一个自叙性的小说,它的人物都是有生活原型的。”(《秦可卿的出身之谜》)
“原来觉得不可理喻,现在一梳理,肯定有生活原型,生活原型当时对待这件事情就是这样的态度,导致了最后《红楼梦》一个自叙性作品对人物的设置,对人物的描写,对情节的描写是这样的。”(《秦可卿的原型就是废太子胤礽的女儿》)
事实上,刘心武先生的整个“秦学”也都是建立在所谓《红楼梦》是“写实”,是“自传”的判断之上的。然而,《红楼梦》是否真的那样“写实”呢?书中的人物又是否一定能在真实的历史中找到可以刚好对榫的原型呢?或许,通过对书中人物的年龄及生辰的仔细探讨,可以使我们的认识更接近于事实的真相。
毫无疑问,《红楼梦》笔法细腻,贴近生活,作者又大量使用限知视角及白描手法,这些都很容易让读者产生这部小说的叙写对象皆真实存在,即所谓“写实”的感觉。然而,如果读者肯于认真地比对书中的许多细琐文字的话,也不难发现这部伟大的作品,其在微观情节上乖谬难合,甚至自相矛盾的地方,亦复不少,特别是集中在小说的时序及人物的年龄、生辰的问题上。由于这类的问题,数量甚巨,不能一一尽举。这里,我们就只以林黛玉、史湘云、薛姨妈、贾母四人为例,来说一说《红楼梦》的所谓“写实”,到底“实”与不“实”!
(一) 关于黛玉的年龄问题
黛玉初进贾府时,她到底多少岁?按《红楼梦》第二回交代,黛玉师从于贾雨村时,她“年方五岁”。“堪堪又是一载的光阴”,黛玉之母贾敏去世,林如海乃遣贾雨村护送黛玉入京。若依此说,黛玉初进贾府时,其年龄为六岁,已读书一年。但到了小说第三回中,黛玉初入荣国府时,作者却特意写了她心里的算计。她是“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耻笑了他去”。一个六岁的女童,能有这样的心计,是不是有事太“超常”了呢?再来看作者对此时黛玉形貌的描写: “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早有论者指出,这怎么看也不像是六岁女童,而绝似妙龄少女。更重要的,黛玉初见宝玉时,她看到的宝玉,已是一个“年轻公子”的形象。既曰“年轻”,不云“年幼”,那宝玉的年龄至少也在十二三岁之间。这也符合作者对宝玉相貌、情态的描写: “天然一段风骚,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据黛玉自云: “在家时亦曾听见母亲常说,这位哥哥比我大一岁,小名就唤宝玉”,黛玉此时的年龄,就至少应该在十一二岁之间。若黛玉六岁从苏州出发,及进京已在十一二岁之间,短短的一路上竟然“暴长”了五六岁,这岂不是怪事?
这样的怪事,显然还不止一桩,到第四十五回,作者又一次莫名其妙地让黛玉“暴长”了三岁。且看这一回中,黛玉对宝钗的表白:
“……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早,又无姊妹兄弟,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一个人像你前日的话教导我。怨不得云丫头说你好,我往日见他赞你,我还不受用,昨儿我亲自经过,才知道了。”(第四十五回)
《红楼梦》第二十五回,癞头和尚持诵通灵,有云: “青埂峰一别,展眼已过十三载矣!”准此,是年宝玉为十三岁。根据周汝昌先生所编“红楼年表”,从小说第十八回到第五十三回所写为同一年。那么,到第四十五回时,黛玉的年龄只应该有十二岁。如何能突然长到十五岁,比宝玉还大了呢?对此,周汝昌先生的解释是“按黛玉小宝玉一岁,实当十二岁。所叙明明不合,疑字有讹误,或后人嫌小,妄改‘二’为‘五’”。同刘心武先生一样,周老先生对自叙说深信不疑,不得不把书中所有“不合”的地方都合理化。不过,周老先生又如何解释以下一条脂批呢?
黛玉才十五岁,记清。(庚辰本第四十五回双行夹批)
——不仅曹雪芹,就连脂砚斋也口口声声说黛玉此时是“十五岁”。假如《红楼梦》真是在“写实”,而历史上也真有那么一个“林黛玉”,于某年进入曹家,与曹雪芹相识。作者会连她的年龄都搞不清楚,像这样信口胡说吗?
(二) 关于湘云的年龄问题
在湘云的问题,作者甚至错得更加可笑。且看第三十二回中,袭人与湘云的一段对话:
袭人斟了茶来与史湘云吃,一面笑道: “大姑娘,听见前儿你大喜了。”史湘云红了脸,吃茶不答。袭人道: “这会子又害臊了。你还记得十年前,咱们在西边暖阁住着,晚上你同我说的话儿?那会子不害臊,这会子怎么又害臊了?”史湘云笑道: “你还说呢。那会子咱们那么好。后来我们太太没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么就把你派了跟二哥哥,我来了,你就不像先待我了。”袭人笑道: “你还说呢。先姐姐长姐姐短哄着我替你梳头洗脸,作这个弄那个,如今大了,就拿出小姐的款来。你既拿小姐的款,我怎敢亲近呢?”(第三十二回)
黛玉小宝玉一岁,湘云比黛玉更小。依《红楼梦》第二十五回,宝玉为十三岁,湘云最多为十二岁。袭人所谓“十年前”云云,那时湘云不过一两岁。一两岁的小儿能对袭人说出什么“不害臊”的话来?有意思的是,从甲戌本到程甲本,这一段文字皆作“十年前”。惟程乙本将“十年前”改为“那几年”,看来是整理者发现了曹雪芹留下的破绽。问题也是同样的,若湘云是有固定原型的,作者何至于犯这样的错误?
(三) 关于薛姨妈的生辰问题
第三十六回,黛玉曾对宝玉云: “我才在舅母跟前听的明儿是薛姨妈的生日,叫我顺便来问你出去不出去。你打发人前头说一声去。”按小说这一段的景观描写来看,此时应为夏末秋初。准此,薛姨妈的生日应在农历八月间。然而,第五十七回,写到次年仲春二月某日,作者又云: “目今是薛姨妈的生日,自贾母起,诸人皆有祝贺之礼。”——那薛姨妈的生日究竟是在二月间,还是在八月间呢?难道一个人可以有两个生日不成?这又是“写实”说的一个致命伤。
(四) 关于贾母的生辰和年龄问题
在《红楼梦》中,贾母更是集此类问题于大成。不仅生辰问题错的可笑,就连年龄也前后矛盾。先来说生辰。第六十三回,探春有云:
“倒有些意思,一年十二个月,月月有几个生日。人多了,便这等巧,也有三个一日、两个一日的。大年初一日也不白过,大姐姐占了去。怨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别人就占先。又是太祖太爷的生日。过了灯节,就是老太太和宝姐姐,他们娘儿两个遇的巧。三月初一日是太太,初九日是琏二哥哥。二月没人。”
“灯节”即正月十五元宵节。据小说第二十二回交代,宝钗生日为正月二十一日。准此,贾母的寿辰,也该在正月中下旬才对。然而,书至第七十一回,作者又作了自我否定:
因今岁八月初三日乃贾母八旬之庆,又因亲友全来,恐筵宴排设不开,便早同贾赦及贾珍贾琏等商议,议定于七月二十八日起至八月初五日止荣宁两处齐开筵宴,宁国府中单请官客,荣国府中单请堂客,大观园中收拾出缀锦阁并嘉荫堂等几处大地方来作退居。
那贾母的寿辰,到底是在正月,还是在八月呢?按刘心武先生的说法,贾母的原型就是曹寅之妻李氏,即曹雪芹的祖母。而曹雪芹竟然连自己祖母的生日都弄不清楚,如此前后矛盾地乱开玩笑,他就不怕亵渎了自己的祖宗吗?
不仅贾母的生日有问题,就是年龄也前后冲突。且看第三十九回贾母与刘姥姥的一段对话:
贾母道: “老亲家,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刘姥姥忙立身答道: “我今年七十五了。”贾母向众人道: “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健朗。比我大好几岁呢。我要到这么大年纪,还不知怎么动不得呢。”刘姥姥笑道: “我们生来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来是享福的。若我们也这样,那些庄家活也没人作了。”
刘姥姥时年七十五岁,贾母小刘姥姥几岁,当在七十岁左右。第四十七回,贾母有云: “我进了这门子作重孙子媳妇起,到如今我也有了重孙子媳妇了,连头带尾五十四年,凭着大惊大险千奇百怪的事,也经了些,从没经过这些事。还不离了我这里呢!”
假定贾母十六岁出嫁,五十四年后,即为七十岁整,与上述交代相合。然而,根据周汝昌先生所编“红楼年表”,从小说第十八回到第五十三回所写为同一年,从第五十三回到第七十回又为一年,从第七十回到第八十回再是一年。仅仅两年时光以后,贾母就到了“八旬之庆”。这与前述黛玉年龄的“暴长”,是不是有得一拼呢?假如作者在第七十一回上说的话是可信的,则倒推回两年,贾母则为七十八岁,比刘姥姥还大。再回推五十四年,贾母则要到二十四岁才出嫁!在那个年代,这不嫌太晚了么?可见,这也是“自传”说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周汝昌老先生曾在《红楼纪历》一文中称赞《红楼梦》,说书中岁时年龄“井然不紊”,“若合符契”。刘心武先生作为“自叙”说的信奉者,自然也认可这一观点。然而,仅就以上四例,我们便不难看出《红楼梦》在时序问题上,不仅说不上什么“井然不紊”,“若合符契”,不客气地讲简直就错的一塌糊涂!试想,若《红楼梦》真是一部“写实”的“自传”,而现实中也真有那么一个“贾母”,那么一个“薛姨妈”,那么一个“林黛玉”,那么一个“史湘云”,作者只需秉笔实录,就可以避免所有的矛盾,哪里还会出现那么多前言不搭后语的情况呢?其实,只要抛却所谓“写实”、“自传”的成见,《红楼梦》中大量出现的时序混乱的问题,便一点也不难解释。《红楼梦》首先是小说,是以虚构为主的文学作品。虽然书中的人物也可以带有现实中某些人的吉光片羽,但其形貌、性格、思想、意志,乃至具体的生辰、年龄,终究是作者自己主观精神世界的产物。作者可以根据情节的需要,为人物设置他所认为合适的年龄,也可以随着设计思路的变化而对该人物的年龄进行重新的调整。同样地,若情节需要,他可以为人物凭空地设计出一个生辰,也可以因为情节的改变,而把人物的生辰作任意的挪动。如上述“八月初三日”的贾母“八旬之庆”,就明显看出是为描写“嫌隙人有心生嫌隙”等一系列事件而作的必要铺垫,终究是为营造贾府即将衰败的秋日气氛而作的虚构。这一点,脂砚斋在庚辰本的第四十三回上讲得很清楚:
看他写与宝钗作生日,后又偏写与凤姐作生日。阿凤何人也,岂不为彼之华诞大用一回笔墨哉?只是亏他如何想来。特写于宝钗之后,较姊妹胜而有余;于贾母之前,较诸父母相去不远。一部书中若一个一个只管写过生日,复成何文哉?故起用宝钗,盛用阿凤,终用贾母,各有妙文,各有妙景。余者诸人或一笔不写,或偶因一语带过,或丰或简,其情当理合,不表可知。岂必谆谆死笔按数而写众人之生日哉?迥不犯宝钗。(庚辰本第四十三回双行夹批)
所谓“起用宝钗,盛用阿凤,终用贾母”,皆是文情所致,顺手虚构,哪里有半点“写实”,或“自传”的影子呢?当然,《红楼梦》是一百一十回的大书(脂评本八十回加后三十回佚稿),作者要做诸如此类的改动,再精细的人也难免会有改了后面,忘了前面,或改了前面,忘了后面的情形。而曹雪芹生前又来不及对整部小说进行最后的抛光打磨,所以留下大量的破绽,也就毫不奇怪了。——问题并不复杂,只是周、刘二位先生,对“自叙”说迷信太深,反悟不出这样浅显的道理,则不免左支右绌,一步步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境地了。
关于“写实”说之不可迷信,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实例。这就是大观园及大观园群芳的“真”、“假”问题。大观园及其中众多美丽可爱的女儿,是真的存在过的吗?作者真的亲睹过如此群芳汇集、佳丽如云的盛况吗?如果你观察仔细的话,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大观园中那些美丽姑娘(丫鬟除外),只要她不是荣国府的,其要么是父亲早死,要么就是父亲为根本不管子女的糊涂人。属于父亲早死的有: 宝钗、黛玉、湘云、妙玉、宝琴、李纹、李绮。父亲根本不管子女的有: 惜春、邢岫烟。——惜春的父亲贾敬对子女、家事“一概不管”,“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们胡羼”(第二回)。邢岫烟的父母则是“酒糟透之人”,“于女儿分中平常”(第五十七回)。为什么这么多女孩子都没有父亲,或者虽有亦无?这种现象如果是在现实中出现的话,概率究竟有多大呢?其实,只要承认《红楼梦》是虚构,道理就异常地简单。旧时,成年男子是要成家立业,顶门立户。俗话说“子不教,父之过”。若父亲尚在,且不是那种“酒糟透之人”,又怎么能让自己的女儿长期居住在别人家呢?可如果众多的女儿不能汇聚到荣国府中,作者又如何能构建出姹紫嫣红、兰菊竞芳的大观园来呢?作者为了艺术的构思,宁可牺牲所谓的“真实”,所以,才让这么多女孩子都一下子没了父亲。由此可见,这世上原本就没有那个大观园,也没有那个林黛玉,那个薛宝钗,一切都是作者凭空塑造的产物。硬要从中去寻找林黛玉的原型是谁,薛宝钗的原型是谁,乃至真实历史中的“秦可卿”、“贾元春”,则不免是胶柱鼓瑟、刻舟求剑了。
四、 大作家的小错误
或许正是因为胶柱于所谓“写实”说、“自传”说,又太急于将小说人物与现实中人挂起钩来,刘心武先生的“秦学”论证,在整体上总让人感到急躁而缺乏严肃性可言。不仅如此,整个“揭秘”系列,还表现为小错误不断,常识性的失误不少。无疑,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影响了刘先生立论的可信性。这一部分,我们就具体地来说一说“揭秘”系列中的,被笔者所发现的一些常识性的错误。
错误之一: “千岁”=“太子”。
《红楼梦》第十三回提及贾珍为秦可卿选择棺木,所用的是当年为“义忠亲王老千岁”准备的上好樯木寿材。这樯木棺材还是当年薛蟠之父带进京城的,“原系义忠亲王老千岁要的,因他坏了事,就不曾拿去”。对于这里出现的“义忠亲王老千岁”,刘心武先生作了如下的解释:
这个木料原来是谁定的货呀?是义忠亲王老千岁定的货。义忠亲王这个符码倒还罢了,当然级别就很高了,但是他又是老千岁!什么叫做千岁?万岁之下只有一个千岁,也就是说,在万岁没有了以后,将升格为万岁的那个人才叫千岁,是不是啊?是这样一个人物。(《秦可卿她应该是什么样的出身》)
这却错得着实厉害了。万岁之下真的“只有一个千岁”?称“千岁”的人,只能是太子?如果刘先生熟悉明、清两代的历史的话,只怕就说不出这样的话来了。我们先来看看在一些清代小说中,所谓“千岁”的用法。
清·如莲居士《薛刚反唐》,第六回“江夏王救护真龙通城虎打奸闯祸”:
此时已有四更时分,江夏王李开芳尚在宴客未散。……当下江夏王正与马周、敬业吃酒,一闻鼓声,忙问何人传鼓,家将回禀是掌宫太监杜回,江夏王分付唤进来。杜回抱了太子,慌慌张张走到殿上,叫了一声“千岁”,看见了英王及马周,便住了口。开芳道: “所抱之子是谁,为何暮夜至此传鼓?”杜回道: “奴婢因抱此子,不便叩头,求千岁屏去人众,奴婢好讲。”开芳喝退人众,殿上只有敬业、马周。开芳道: “英王乃开国元勋,马爷又忠直义士,纵有机密事,皆可与闻不妨。有何大事,你快说来!”杜回道: “有正宫王娘娘哀书在此,请千岁一看,便知明白。”开芳接书一看,与敬业、马周一齐大惊,且喜救出了太子。开芳接过太子,仔细一看,不觉泪下。敬业、马周皆泪流,叫一声: “千岁,当今圣上听信奸佞,将王后贬入冷宫,又遭武氏谋害,幸亏杜太监一片忠心,救出小主,投奔千岁。千岁当抚养府中,待圣上万岁后,当扶小主正位。我二人愿与千岁共之!”开芳道: “日后天子登天,嫡庶之分,理应此子正位。孤当与二位仁兄共佐之,上不负先帝之恩,下不负王后之托。”
——江夏王李开芳不过是唐皇的远房兄弟,根本不可能像太子那样将来接班登基。但显然,在小说中,这并不妨碍别人称他为“千岁”。
清·佚名《说唐》,第四十回,“罗成力抢状元魁阔海压死千金闸”:
天锡见了,将混金铛又望顶上盖下,师泰躲闪不及,正中头盔,跌下马来,复一铛结果了性命,大叫道: “那一位敢再来考?”李元霸看见大怒,纵马进前道: “孤家来了!”伍天锡见是李元霸,大惊失色道: “千岁为何也来考试?末将让千岁进关。”元霸大喝道: “红面贼,你把孤家开路将打死了,孤家来取你命也。”
——按《说唐》的说法,李元霸为唐高祖李渊第四子(正史无此人),并非太子(太子是李渊长子李建成),但这里伍天锡照样称李元霸为“千岁”!
清·李雨堂《万花楼》(又名《狄青初传》)第九回,“急求名题诗得祸报私怨越律伤人”:
不表众将、众兵私谈,再表狄青正在推出教场之际,忽报来说,五位王爷千岁到教场看操。孙秀吩咐将狄青带在一旁等候开刀。是时兵部躬身出迎,林贵带狄青在西边两扇绣旗里隐住他的身躯。林贵附耳,教他待王爷一到,快速喊救,可得活命。却说兵部迎接的王爷,第一位潞花王赵璧;第二位汝南王郑印,是郑恩之子;第三位是勇平王高琼,高怀德之子;第四位静山王呼延显,呼延赞之子;第五位东平王曹伟,曹彬之子。此五位王爷,除了潞花王一人,皆在七旬以外,在少年时,皆是马上功名,故今还来看军人操演。当下五人徐徐而至,许多文武官员伺候两边,林贵悄悄将狄青肩背一拍,狄青便高声大喊: “千岁王爷冤枉,救命呵!”一连三声,孙兵部呆了一呆。
——刘心武先生说“万岁之下只有一个千岁”,但这里居然出现了“五位王爷千岁”!对于这种情形,是叫人相信刘先生的判断好呢,还是相信古人的叙述好呢?
很明显,所谓“千岁”,不过是对“王”一级人物的俗称或尊称。事实上,在明、清两代,凡亲王、郡王、皇后、皇贵妃,俱可以称为“千岁”。甚至,连独揽权柄的大太监,也有公然称“九千岁”的,如魏忠贤之流。据《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五,各地为魏忠贤建生祠,“金像用冕旒,凡疏词一如颂圣,称以尧天舜德,至圣至神。而阁臣辄以骄语褒答。运泰迎忠贤像,五拜、三稽首,……诣像前祝称: 某事赖九千岁扶植”。难道魏忠贤之流亦是太子?可见,刘心武先生仅凭一个“老千岁”的称呼,就断定其为废太子胤礽,实在难以令人信服。至于刘心武先生反复强调的“坏了事”三字,这也并没有什么神秘性可言。须知,在雍、乾时代,清皇族内部权力斗争中遭到整肃而倒霉的皇族成员,并不鲜见。譬如,仅雍正时代著名的就有康熙第八子胤禩(即“阿其那”)、康熙第九子胤禟(即“塞思黑”)、康熙第十四子胤禵、雍正第三子弘时、老平郡王纳尔苏等等。无论哪一桩案件,都足以给曹雪芹在小说中虚构所谓“坏了事”的“义忠亲王老千岁”提供现成的素材,也根本不足以认定这就是康熙朝太子胤礽被废的旧案。
错误之二: 太子留下的对联。
为了将小说中的贾府、历史上的曹家与康熙废太子胤礽联系起来,刘心武先生在《红楼望月》一书中提出了以下一种说法:
这个太子有很多故事,我现在不细说,我现在就告诉你,由于康熙从小培养他,一方面要精通满文,一方面要精通汉文,请很多名师大儒,让他学“四书”、“五经”,让他学汉族的经典,同时让他学诗词歌赋,让他对对子。太子留下一副对联很有名,在康熙朝一位大儒王士祯所留下的《居易录》这本书里就有记载。这副对子是这样的“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请注意他的平仄,请注意这副对联的最后一个字,上联最后是“月”字,下联最后是“霞”字。林黛玉在荣国府正堂所看见的对联”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上联最后是“月”字,下联最后是“霞”字。
但早有“红迷”朋友指出,所谓“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并非太子所作。它是刘禹锡《送蕲州李郎中赴任》的诗句:
楚关蕲水路非赊, 东望云山日夕佳。
薤叶照人呈夏簟, 松花满碗试新茶。
楼中饮兴因明月, 江上诗情为晚霞。
北地交亲长引领, 早将玄鬓到京华。
——刘先生的这个证据,显然也不足以认定贾府或曹家与胤礽、弘皙一家的关系。
错误之三: “星宿”读作“星塑”。
在《秦可卿的原型》一讲中,刘心武先生对张友士给秦可卿开的药方子,作了以下的解释:
这个药方的头一句如果要用谐音的方式来解释的话,人参,白术,按我的思路,应该代表着她的父母……人参,这个参,可以理解成天上的星星,人已经化为星辰了,高高在上,我觉得可以理解为是象征长辈;白术,作为一味中药,术的读音应该是zhu(第二声),但是曹雪芹从南方来到北京,他还保留着不少江南人的发音习惯……因此“白术”作为黑话,也可以理解成“白宿”,“宿”也有星辰的意思……总之,我觉得“参”和“术”都隐含着星辰的意思……这药方里的头四个字,代表着秦可卿家里的长辈,她的父母,她的兄长……把第三味药的两个字拆开,与前后两味药连成句子,那意思就很直白了,它是这样的: 人参白术云: 苓熟地归身。意思就是她的父母说,告诉她底下这句话,说老实话,她的父母可能心情也很沉重,她自己看了以后也会更痛苦,就是“令(苓)熟地归身”,也即命令她,在关键时刻,在她生长的熟悉的地方,结束她的生命。
这却又犯了常识性的错误。须知,普通话中“星宿”的“宿”字,根本不是读作“塑”的音,而是读作“秀”!且看《新华字典》(1998年修订本)549页上,对“宿”字的解释:
宿③xiù: 我国古代的天文学家把天上某些星的集合体叫做宿: 星宿、二十八宿。
①sù: 见468页。
②xiǔ: 见548页。
不知道这个“星宿”的“宿”,与“白术”的“术”,有何“谐音”可言?另外,把“星宿”解释成“星星的意思”,也属于常识性错误。“星宿”是某个星区下所有肉眼可见星的集合,并非单独的“星星”。中国古人将星空划分为二十八个星区,是有二十八宿。每七宿又组成一个大的组合,分别用动物表示,依次为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而东、西、南、北、中,又分别与“五行”相对: 东方属木、西方属金、南方属火、北方属水、中央属土。由此构成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基础。刘先生大概只忙着作“揭秘”的事,竟忘记了在这些古文化常识上下点工夫了吧?
错误之四: “清虚观”读作“清虚关”。
与上一个错误类似,刘心武先生在《贾元春原型之谜》也读错了一个不该读错的字。以下为刘先生的原话:
那么,她最早可能是哪儿的王妃呢?我们就要说到,“清虚观打醮”这件事情。这个事情我在前几回里面讲过,你还有印象吗?很重要的情节。那么清虚观打醮它的起因是什么?为什么要在清虚观打醮?为什么?有人说,你已经讲了呀,那不是贾母她“享福人福多还祷福”,贾母是这样一个目的,但是清虚观打醮的发起者是贾元春,书里面是非常清楚地给我们写出来的。在第二十八回,通过袭人的话报告给宝玉,说: “昨儿贵妃打发夏太监出来,送了一百二十两银子,叫在清虚观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清虚观打醮最早的起因,不是说贾母本人她要求福,贾母求福的由头,是因为贾元春有一个交代。这里我想,这一笔曹雪芹他不会乱写,更不可能是我就要写一句废话。曹雪芹的《红楼梦》每句话他都是认真下笔,都有用意的。清虚观打醮由头,是贾元春她要贾府做这件事。在什么日子做呢?在五月的初一至初三,在端午节前。打什么醮呢?打平安醮。打醮就是祈福。她显然是要为某一个人祈求平安,如果是活着的人,她希望他活着平安;如果是死去的人,希望他的灵魂能得到安息。
在这段讲话中,刘心武先生将“清虚观”一律读作“清虚关”,这也不符合普通话的习惯。“观”字,作道教建筑讲,应读去声,读作“贯”。且看《新华字典》(1998年修订本)169页上,对“观”字的解释:
观(觀)②ɡuàn: 道教的庙宇。
①ɡuān: 见167页。
这个错误虽没有上面一个错误那样致命,但也足以显示出刘心武先生之“揭秘”系列的不严谨。
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也可以同刘心武先生商榷几句。这就是贾元春判词的问题。正如刘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该判词的最后一句,实有两种不同的版本: 一作“虎兔相逢大梦归”,一作“虎兕相逢大梦归”。刘先生相信“虎兕”为曹雪芹原稿,“虎兔”为后人改稿,且在“揭秘”系列节目中拟出了一个图表,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梳理、概括。该图表如下:
虎兔——通行本
虎兕——古本
然而,笔者却不能不说,刘先生这样的概括实在来得草率!刘先生所称“通行本”实际为程高本系统,所称“古本”实际为脂评本系统。说程高本系统中该句判词一律写作“虎兔相逢大梦归”,自然不错。然而,脂评本系统中,却远不是所有的版本写的都是“虎兕相逢大梦归”!恰恰相反,除己卯本、梦稿本以外的绝大部分钞本、印本,都与程高本一样,写的是“虎兔相逢大梦归”!我们也可以将刘心武先生所称“古本”中“虎兔”、“虎兕”的情况,拟出一个简表供诸位一览:
虎兔——甲戌本、庚辰本、北师大本、蒙府本、戚序本、南图本、甲辰本、己酉本
虎兕——己卯本、梦稿本
如果取“古本”的“古”义,与“通行本”的“今”义相对,则甲戌本是目前公认的年代最古,行文也最接近曹雪芹原稿的版本。而甲戌本上亦赫然抄写着“虎兔相逢大梦归”,口口声声“古本”的刘心武先生又为何不采信此最古版本的写法呢?如果说“虎兕”为原稿,“虎兔”为高鹗“篡改”,高鹗又如何能够将曹雪芹生前形成定本的甲戌本、庚辰本一律改过?所以,“虎兔”与“虎兕”,孰真,孰假,对于这种问题,笔者的看法与刘先生正好相反: 所谓“虎兔”才是曹雪芹的原稿,所谓“虎兕”恰恰是抄手的错改。据史料,康熙皇帝卒于清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即公元1722年。次年,雍正登基改元,是为雍正元年癸卯。壬寅为虎年,癸卯为兔年——这即是“虎兔相逢”的由来!曹雪芹的家族在康熙朝备极荣宠,在雍正朝获罪抄家。这种局面的出现,不能不说是与康熙驾崩,曹家失去最大的政治靠山有关。惨痛的家族经历,完全有可能让曹雪芹在创作小说时,有意让元春于某个壬寅年与癸卯年相交的时刻死去——生于大年初一,卒于年末除夕,以对应曾经给自己家族命运造成巨大影响的康、雍两朝交替的政治事变。至于“虎兔”何以变为“虎兕”,原因也不复杂。一则“兔”与“兕”,草书形近。二则,《论语·季氏将伐颛臾》中有云: “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虎兕”是成典。当底本上字迹潦草,不好辨认的时候,读过《论语》的抄书人很容易根据他对《论语》的记忆,将此处擅改为“虎兕”。——当然,以上这些也是笔者的一家之言,刘先生也可以不赞同。但无论如何,刘心武先生不细辨脂评本中的歧见,一古脑地将“虎兕”与所谓“古本”对应起来,实在难脱误导听众之嫌!
五、 “自叙”说辨正
前面四部分,我们辨析了刘心武先生所谓“秦学”的诸多错误。而这些问题的基础正是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以“写实”为主的“自传”,从而使我们的讨论最终指向了一点,即在“红学”界影响甚大的所谓“自叙”说。《红楼梦》的“自叙”说,自20世纪20年代由胡适先生提出以来,在国内可谓几经沉浮。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自叙”说以科学的考证、翔实的资料,有力地反驳了民国初年盛极一时的种种“索隐”派论调,开创了20世纪的“新红学”时代。50年代以后,“自叙”说遭到政治评论派的猛烈攻击,被指为“地主资产阶级的谬论”,又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8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评论派“红学”的日益没落,“自叙”说又再度兴起,似有重新占据“红学”主流地位的趋势。然而,这样一种“自叙”说,在学理上又是否真的站得住脚呢?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强”、“弱”两个意义上来讨论。
在“弱”的意义上,“自叙”说认为,《红楼梦》的作者为曹雪芹,曹雪芹在创作这部小说时大量地以自己和家族的经历为蓝本,但这也并不排除小说中有为数更多的虚构。书中的贾宝玉有曹雪芹自己的影子,但又不能简单地与作者本人划等号,而是属于一种类似于“童心复来梦中身”的虚实结合等等。
在“强”的意义上,“自叙”说则以周汝昌老先生的观点为代表。这一派学者认为,《红楼梦》就是曹雪芹的“自传”,就是老老实实的“写实”。书中的每一件稍微重要一点的事情,都必定是曹雪芹亲身经历过的,在真实的历史中存在过的。甚至,书中所发生的事情,都可以到历史中精确到年,编成“红楼年表”,再来反推曹家的历史。同时,这一派学者还认为,书中的人物都有确凿的生活原型,贾宝玉就是曹雪芹,薛宝钗就是曹雪芹的元配,史湘云就是曹雪芹的继配,也就是脂砚斋。曹雪芹的一生是“先娶薛宝钗,再娶史湘云”。贾宝玉有个姐姐(贾元春)做了皇妃,曹雪芹也一定有一个姐妹做了乾隆的妃子云云。一句话,在他们看来,简直没有区分艺术形象与现实生活的必要。
毫无疑问,在“弱”的意义上,“自叙”说是言之有理的,也符合文学的基本原理,直到今天仍不失为我们从事“红学”研究的一条指导。而“强”的“自叙”说,则是在前者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然而却又把“自叙”二字的含义,给推向了极端,使这种继承和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异。孔老夫子有云: “过犹不及。”凡事太过于极端,就会丧失掉其原有的合理内核,而滑向荒谬。法国皇帝拿破仑曾说“伟大与可笑仅一步之遥”,这似乎正好可以用来形容“自叙”说由“弱”的意义转向“强”的意义时所发生的“癌变”!然而,可惜的是“癌变”的细胞总是与正常的细胞混淆在一起,让人一时难辨。赞同“自叙”说者,往往全盘接受,连“强”的意义上的“自叙”说,也囫囵吞枣般地咽下。反“自叙”说者,又往往全盘否定,连“弱”的意义上的“自叙”说,也弃如敝屣。这使得正常的、一分为二的讨论总难以展开。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刘心武先生的所谓“秦学”,才获得了发展的空间,直至走上中央电视台的讲坛。
在笔者看来,所谓“秦学”的产生,不过是“强”的意义上的“自叙”说的一个死结的间接产物,而要解开这个死结,则不能不提到“红学”史上又一桩有名的公案。这就是曹雪芹的生年问题。学术界一般是依据曹雪芹的卒年来推测其生年的。而关于曹雪芹的卒年,最明确的记载来自于以下一条脂批: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常哭芹,泪亦待尽。每思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申)八月泪笔。(甲戌本第一回眉批)
据此,曹雪芹应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公元1763年2月12日)。敦诚《挽曹雪芹》中有“四十年华付杳冥”等语。由此上推四十年,曹雪芹当生于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公元1722年2月至1723年2月)。①熟悉“红学”或“曹学”的朋友都知道,江南曹家早在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就被籍没了家产。时年,曹雪芹不过五六岁的年纪。如果坚持“强”的意义的“自叙”说,曹雪芹在小小年纪就遭遇到了家庭巨变,他又如何去亲身经历那一场富贵风月呢?用胡适的话说,就是江南的繁华,他是赶不上了。对于这个问题,胡适的解决办法是尽量把曹雪芹的生年往前提,用“增寿”的方法,让曹雪芹去“赶”上那一场江南的繁华。敦诚不是说曹雪芹“四十年华付杳冥”么?“四十”是举成数,其含义可能是“四十多”,比如四十五行不行?于是,到雍正六年,曹雪芹就有十一岁了。但还是嫌小,又比如四十九行不行?到雍正六年,曹雪芹就有十五岁了。——只是这样引来的问题,可能比解决的还要多。按一般中国人的习惯,说别人“享年”多少,通常都宁可说大,不大可能说小。若曹雪芹年近五十而卒,与他相识的朋友,只应该“增寿”说成“五十年华”,断没有“减寿”说成是“四十年华”的道理。所以,胡适的办法有明显的漏洞。而周汝昌的思路别出心裁,他假想了所谓曹家于乾隆元年在北京“复兴”的说法。这样也可以让曹雪芹去赶上一段繁华——只不过,不是江南的繁华,而是北京的繁华罢了。然而,众所周知,曹雪芹后来是落到了极端穷困潦倒的境地。所谓“举家食粥酒常赊”,“日望西山餐暮霞”(敦诚《赠曹芹圃》)。所以,曹家如果有乾隆元年的“复兴”,则必然有第二次被抄家。但可惜得很,无论是“复兴”,还是“第二次抄家”,都是于史无证的东西,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这就迫使这一派学者不得不在《红楼梦》本身上打主意,总企图通过对一些诗词的刻意曲解,来把这部小说同当时的一些政治事件联系起来。周汝昌老先生自己选中的政治事件是发生于乾隆四年的所谓“弘皙逆案”。然而,早已没落的曹家,实在没有资本再卷入到乾隆初年的这场新的皇权斗争之中。历史也没有给周老先生留下曹家确实与胤礽、弘皙一支有牵连的确凿证据。所以,周老先生的“新自叙说”(邓遂夫语)依然面临着崩塌的危险。而刘心武先生的“秦学”的出现,就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新自叙说”的先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