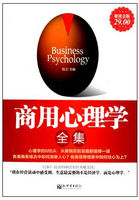尽管人们一度将BERLE和MEANS(1932)所描述的高度分散的所有权模式看作现代公司的基本特征,但最近却有许多文献对其提出了质疑(EISENBERG,1976;DEMSETZ,1983;DEMSETZ和LEHN,1985;SHLEIFER和VISHNY,1986;MORK等,1988)。例如,DEMSETZ和LEHN(1985)认为,如果需要,高度分散的所有权完全可以方便地集中起来以实现对经理的监督。实际上,HOLDER-NESS和SHEEHAN(1988)在美国证券市场也发现了100多家存在绝对控股股东(即持股比例超过50%)的上市公司,而最近关于欧洲以及亚洲等国的研究则进一步证明,集中的所有权(特别是控制权)似乎更为普遍(CLAESSENS等,2000;LA PORTA等,2000;MORCK等,2000)。因此,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最近受到了普遍关注(SHLEIFER和VISHNY,1997)。
理论上,由于在公司有更大的收益要求权,大股东有强烈的动机对经理进行监督,而相对集中的控制权也保证了大股东可以对公司决策行为施加足够的影响力(JENSEN和MECKLING,1976)。例如,SHLEIFER和VISHNY(1986)给出了一个模型用来说明,当公司经理人员存在牺牲股东利益建造个人帝国的行为时,大股东可以通过代理权争夺或接管的方式将其撤换。HARRIS和 RAVIV(1988)、STULZ(1988)、GROSSMAN和 HART(1988)以及 BECHUK(1994)也都从理论上对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进行了证明。
但也有文献认为,大股东的存在可能导致公司某些成本的增加。这些成本包括:首先,大股东对公司的过度干预可能限制经理人员的非合同性人力资本在公司的投入以及对工作的积极主动意识(BURKART等,1997)。其次,大股东为了获得足够的控制权必须将大量的资本集中在同一公司,从而无法通过分散化的投资规避风险(HUDDART,1993;ADMATI等,1994)。另外,大量财富的过度集中还会降低股票市场的流动性(BECHT,1999),而流动性的降低对大股东监督作用的消极影响已被许多文献所证明(MAUG,1998)。最后,也是最为严重的是,大股东可能凭借其
对公司的控制权利用公司资源牟取私利(SHLEIFER和 VISHNY,1997),特别当大股东通过金字塔、交叉持股以及双重股票等方式实现对公司的控制时,由于现金收益权与投票权的严重背离,大股东的寻租行为可能更为严重(BURKART等,1998;BECHUK,1999;WOLFENZON,1999;BECHUK等,2000)。
以上分析表明,大股东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讲是模棱两可的。那么,有关的实证研究是否得出了一致结论呢?下文将从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两个方面对相关实证文献进行总结。
一、大股东的积极作用
(一)来自大股东与企业绩效相互关系的证据
虽然早在20世纪30年代,BERLE和MEANS(1932)就提到了股权结构对公司业绩的可能影响,但直至60年代,有关的实证研究才开始大量涌现,并一直持续到现在。GUGLER(2001)对截至目前有关美国和英国市场的研究进行了总结,结果表明大部分的文献提供了大股东具有积极作用的证据,少量的文献发现大股东对公司业绩没有显著影响,只有WARE(1975)以及THONET和POENSGEN(1979)发现大股东的存在损害了公司价值。
由于美国和英国的股权结构相对分散,上述研究在定义大股东时对其持股比例的要求较低。例如,在许多研究中,持股超过5%~10%的投资者(包括内部经理人员)即被定义为大股东。但在英国和美国之外的其他许多国家(例如欧洲和东亚等),大股东持有的所有权(特别是控制权)股份远高于上述两个国家的情况,被大股东绝对控股的上市公司在这些国家非常普遍。例如,在澳大利亚、比利时、德国和意大利,有超过50%的上市公司存在绝对控股股东,西班牙、法国、新西兰和瑞士等国也分别有超过30%的公司存在控股股东,而英国和美国存在绝对控股股东的上市公司则不足10%(BARCA和BECHT,2000)。CLASE-SENS等(2000)以及LA PORTA(1999)的研究也发现,在东亚各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分别有32%和77%(大公司为65%)的公司存在持股(指控制权股份)比例超过20%的大股东,而在美国和英国的上述数字分别为10%和30%(大公司分别为20%和0%)。另外在德国和日本,由于其特殊的融资体制,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也与大股东非常类似(SHLEIFER和 VISHNY,1997)。因此,来自欧洲以及东亚各国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大股东的作用。
来自德国的证据显示,大股东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依赖于大股东的性质,银行的监督能力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的大股东。例如,THONET和POENSGEN(1979)发现,经理控制型公司的业绩(以总资产收益率以及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的比值衡量)要显著低于股东控制型公司②。但是,FRANKS和MAYER(1997)以及GOER-GEN(1999)的研究却没有发现股权结构对企业绩效的显著影响,而GEDAJLOVIC和SHAPIRO(1998)则证明,股权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当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总资产收益率)负相关,而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股权结构对企业绩效则有显著为正的影响。LEHMANN和WEIGAND(2000)认为,大股东的性质可能影响其监督行为,因为,家族、相关的非金融公司、银行以及持股公司等内部投资者可能比外部投资者(例如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有更强的动机对企业行为进行干预(CUBBIN和 LECH,1983;MAYER,1992)。他们的研究发现虽然总体看来大股东对企业盈利能力(总资产收益率)没有显著影响,但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公司业绩显著高于其他公司的业绩。其他研究也发现,与银行相联系公司的盈利能力显著强于其他公司,并且银行的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的业绩越好(CABLE,1985;GORTON和 SCHMID,2000,EDWARDS和 NIBLER,2000)。但是关于日本的研究则表明,银行持有较高的公司股份可能损害公司价值。例如,MORCK等(2000)发现,在较低的水平上,银行的持股比例越高,以TOBINS Q衡量的企业绩效越差;这种负相关关系虽然当银行持股比例较高时不再出现,但也不存在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他们的研究同时发现,非银行的第一大股东以及经理人员的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遗憾的是,来自欧洲以及亚洲其他不同国家的研究也没有提供一致的结论。例如,MITTON(2002)对来自5个东亚国家或地区的398家公司的研究发现,在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期间,公司的股票价格与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GUGLER(2001)对澳大利亚、GOERGEN和RENNEBOOG(2001)对比利时的研究也发现大股东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是,法国(KREMP和SEVESTREC,2001)、新西兰(DE JONG,2001)和西班牙(CRESPI-CLADERA,2001)的证据则表明,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对企业绩效没有显著影响。
(二)来自大股东与经理人员变更关系的证据
有研究表明,股权结构对于企业绩效可能是一个内生变量,即企业绩效决定了股权结构,而不是相反(DEMSETZ,1983;DEMSETZ和 LEHN,1985;DEMSETZ和 VILLALONGA,2001;CHO,1998;HIMMELBERG等,1999;DEMSETZ和 VILLALONGA,2002),因此,通过考察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可能受到方法论的限制,直接考察大股东对某些企业决策行为的影响,可能更容易检验大股东的价值。其中,经理人员的更换就是一项大股东可能对其施加重大影响的决策行为,并且已有许多文献提供了相关的证据。
DENIS和SERRANO(1996)对美国公司的研究发现,当公司击败接管要约后,业绩低劣并存在大股东的公司的经理人员的变更频率显著高于其他公司,HOLDERNESS和SHEEHAN(1988)的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他们发现大宗股权交易(超过50%)往往伴随着高频率的经理人员变更现象。DAHYA等(1998)以及RENNEBOOG和TROJANOWSKI(2002)对英国公司的研究也提供了大股东对经理人员更换具有积极影响的证据,他们证明经理人员的更换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随着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而增强,但随着内部经理人员持股比例的提高而减弱。KAPLAN和MINTON(1994)以及KANG和SHIVDASANI(1995)对日本的研究也发现,经理人员变更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随着大股东(或财阀)的出现而增强。
上述研究充分证明了大股东在监督经理人员方面的积极作用。DHERMENT-FERERE和RENNEBOOG(2000)对法国公司的研究则进一步证明不同性质的大股东具有不同的监督作用。他们发现,银行、政府以及机构投资者虽然拥有较高比例的所有权股份,但似乎并没有影响到经理人员的更换行为,而在行业性公司作为大股东的公司中,企业绩效对经理人员的更换则具有显著影响。从而说明,银行、政府与机构投资者对经理人员的监督作用弱于其他公司。另外,来自比利时的证据也表明不同身份的大股东在监督经理人员方面存在显著差异(GOERGEN和 RENNEBOOG,2000;RENNEBOOG,2000)。
二、大股东的消极作用
大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的证据已经逐渐累积起来。这些证据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控制权溢价、公司价值、股利政策、资产转移以及经理更换等。
虽然 GROSSMAN和 HART(1980)很早就提出了控制权收益的概念,但正如DYCK和ZINGALES(2001)所指出的,由于控制权收益的不可观测性,很难找到一种可靠的方法对其进行计量,截至目前所有关于控制权收益存在的证据都是间接的。相关的研究主要采用两种方法来衡量控制权收益。第一种方法最先由BARCLAY和HODERNESS(1989)提出,即通过比较大宗股权(控制性股份)转让时大股东付出的价格与股权转让公告后一日市场交易的价格之间的差额来衡量控制权收益。第二种方法则是通过比较两种具有不同投票权的股票(有相同或类似的现金收益权)的市场交易价格来计量控制权收益。BARCLAY和HODERNESS(1989)运用第一种方法对美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溢价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在大宗股权交易中,大股东支付的价格平均高于市场交易价格的20%。DYCK和ZINGALES(2001)运用同样的方法对来自39个国家的1990~2000年间的412起控制权交易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国家的控制权溢价水平有很大的差异,最小为-4%(日本),最高则达65%(巴西),所有样本的平均水平为14%。他们发现,资本市场的规模、股权集中程度以及私有化方式都对控制权溢价程度具有显著影响,该结果与相关理论的预期相符(ZINGALES,1995;BEBCHUK,1999;DYCK,2001)。另外,来自双重股票交易价格的研究也证明了控制权溢价现象的存在,并表明不同国家的控制权溢价水平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从最小的3%(美国)到81%(意大利)不等。从理论上来讲,控制权溢价的存在不一定必然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但相关的实证研究却发现,一国控制权溢价水平的高低与该国法律体系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具有显著的相关性:法律体系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越好,控制权溢价水平越低,反之亦然(DYCK和ZINGALES,2001)。因此,控制权溢价现象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权为其带来了超额收益。
两权分离程度对公司价值的负面影响提供了大股东消极作用的另一个间接证据。SHLEIFER和 WOLFENZON(2002)从 BECKER(1968)的“犯罪与惩罚”理论出发,证明大股东对其他股东剥削的可能性越大(法律体系对投资者的保护越弱以及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程度越高时),控制权收益越大,从而公司的价值越低。LA PORTA等(2002)以及 CLAESSENS等(2002)为其提供了证据。VOLPIN(2002)的研究也发现,控股股东持有的现金收益权低于50%的公司价值显著低于被大股东绝对控股的公司(即现金收益权和控制权比例都高于50%)。
自从 MODIGLIANI和 MILLER(1958)以及 MILLER和 MODIGLIANI(1961)的“股利无关论”提出后,经济学家已经建立了众多理论来解释BLACK(1976)所称的“股利之谜”(DIVIDEND PUZZLE)。其中,曾一度流行的信号理论(SIGNAL THEORY)认为,股利政策被经理用来向外界传递有关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的信息(BHATTA-CHARYA,1979;JOHN和 WILLIAMS,1985;MILLER和 ROCK;1985;AMBARISH等,1987)。许多文献用股利宣告的市场反应对其进行了验证(AHARONY和 SWARY,1980;ASQUITY和 MULLINS,1983),但最近有文献对该理论的正确性提出了质疑。例如,DEANGELO等(1996)以及BENARTZI等(1997)发现,当期股利政策的变化无助于对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的预测。因此,用代理理论来解释公司的股利政策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根据该理论,公司内部人一般不愿意将公司利润分配给外部投资者,而是更倾向于将其留在公司或投资于一些并不划算的项目以从中获得私人利益(EASTER-BROOK,1984;JENSEN,1986;FLUCK,1998;FLUCK,1999;HART和MOORE,1994;GOMES,2000;ZWIEBEL,1996)。基于股利分配的代理理论,相关文献表明大股东可能通过将更多的利润留在公司实现对小股东的剥削。LA PORTA等(2000)对来自33个国家的4 000家公司的股利政策的研究证实了上述假设。他们发现,法律体系对投资者保护较好国家的股利分配比率显著高于法律体系对投资者保护较差的国家。并且,在法律体系对投资者保护较好的国家,公司成长机会对股利分配比率有着显著影响(成长性高,分配率低,反之亦然),但在法律体系对投资者保护程度较弱的国家,两者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作者认为,在其他条件(例如成长机会等)等同的情况下,股利分配比率的高低反应了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剥削程度。DEANGELO和 DEANGELO(2000)对TIMES MIRROR公司的案例研究提供了大股东利用股利政策剥削小股东的详细过程。FACCIO等(2001)以及 VIENNA(2001)的研究则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结论。FACCIO等(2001)对东亚各国的研究发现,控股股东的现金收益权与投票权的分离程度越高的公司以及与某财团相关联的公司越倾向于分配较少的股利;GUGLER和YURTOGLU(2001)对德国公司的研究也证明,当公司股权结构的安排更有利于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剥削时(例如公司采用金字塔或交叉持股的方式),股利减少的公告将会引起显著为负的市场反应(权益资本的2%),并且这类公司的股利分配比例也显著低于其他公司。
除了不分配股利外,直接窃取公司资产是大股东剥削小股东的另一种表现方式。例如,BERTRAND等(2002)提供了控股股东通过掏空剥削小股东的证据。另外,WEINSTEIN和 YAFEH(1998)的研究也提供了与此相关的证据。他们以日本700家制造业公司1977~1986年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发现受到主要银行支持的公司之所以表现出较低的资本密集度和较低的盈利能力(WEINSTEIN和YAFEH,1995;MORCK等,2000),主要是受到以下两个因素影响:(1)出于对风险的厌恶,主银行更倾向于让公司投资一些低风险项目,因此必然对应着低的收益率。(2)主银行利用其对公司的有效控制进行寻租。他们发现,受到主银行支持的公司的债务成本显著高于其他同类公司,从而表明主银行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强制公司支付了较高的利息。
在东南亚、西欧、中东、拉丁美洲以及非洲,许多上市公司由家族控制(LA PORTA等,1999;CLAESSENS等,2000;FACCIO和LANG,2002)。BURKART等(2002)建立了一个模型用来说明家族控股企业创始人退休时的决策行为。他们的研究表明,当法律体系可以实现对投资者的有效保护时,雇佣职业经理人经营企业并将其全部出售是一种最好的方式,这时公司代理问题主要表现为职业经理与外部投资者的利益冲突;当法律体系可以有效保护小股东但却不足以制止经理人员的“懈怠行为”时,创始人或其后代将雇佣职业经理经营企业但却持有足够股份以监督经理行为,这时公司的代理问题将表现出双重特征,一方面是大小股东的利益冲突,另一方面是经理与股东的利益冲突;当小股东的利益也无法得到法律体系有效保护时,创始人或其后代将继续经营企业并同时拥有控制型股份,这时公司代理问题主要表现为大小股东的利益冲突。因此,对家族控股企业经理人员变更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大股东控制对公司经营的重要影响。VOLPIN(2002)对意大利公司的研究为其提供了证据支持。他们发现,具有以下特征的公司经理人员变更对企业绩效的敏感性显著低于其他公司:(1)公司控股股东同时担任经理。(2)控股股东持有的现金收益权低于50%,并且其他股东持有的股份不足以对公司施加任何实质性影响。
三、大股东产权特征的影响
KANG和SORENSEN(1999)指出,不同类型的股东在外在权威(FORMAL AUTHORITY)、社会影响(SOCIAL INFLUENCE)以及专业技术(EXPERTISE)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他们监督管理者的愿望和能力可能随其收益权和使用权的多少而变化,从而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可能并不完全相同。无论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都面临同样的公司治理问题,即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所导致的内部经营者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代理问题。但是,不同产权所有者对上述问题的处理方式并不完全相同,从而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效率也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SHIRLEY和WALSH(2000)从监督(MONITORING)、合同(CONTRACTS)、接管(TAKEOVERS)以及破产(BANKRUPTCY)四个方面分析了当大股东产权为公有性质时(即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公司),相对于大股东产权为私有性质时在公司治理结构上的缺陷。
(一)监督
来自股东的直接监督是解决代理问题的最佳方案,但是,如果将全体公民看作国有企业的股东,国有企业的股权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比私有企业更为分散,并且由于国有企业的股东不能像私有企业的股东一样自由买卖其拥有的企业股份,进而企业绩效对其财富的影响也显著小于私有企业。ALCHAIN(1965)认为上述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国有企业股东的监督效率要显著低于私有企业。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由于不存在公有产权市场,国有企业股东也就无法像私有企业股东一样通过产权市场获得有关企业绩效的信息。VIKERS和YARROW(1991)以及LIN、CAI和LI(1998)认为,来自产权市场的反映企业绩效的信息提供了私有企业股东相对于公有企业股东不可比拟的监督优越性。KANE(1999)也持类似的观点,指出股权分散与信息匮乏都会导致国有企业股东监督的低效率。这说明,由于公有产权监督的无效率,国有企业的经理比私有企业的经理有更多地“偷懒”机会,从而国有企业绩效也会劣于私有企业。
当然,还有一种观点是将政府视作国有企业的股东(YAR-ROW,1986)。此时,国有企业的股权将高度集中,从而可能得出国有企业股东的直接监督要强于私有企业的结论。但是,政府作为大股东同样要承担股权集中的各种成本,例如无法规避财富集中的风险,无视小股东的利益追求社会效益等等。因此,即使认为国有企业的股权是高度集中的,一旦考虑上述成本以及政府作为选民代理人的各种败德行为,国有企业股东的监督能力也不一定优于私有企业(VICKERS和YARROW,1991;BOARDMAN和VINING,1992)。
(二)合同
求助法律保护是解决代理问题的第二个选择,其中外部投资者与内部经营者之间的合同被视作法律保护的主要手段。这里的合同不仅是指对经理人员进行奖惩的薪酬合同,而是泛指股东与经理就各自资源进行交换的一种协议,即经理通过承诺为股东提供利润最大化的管理服务以换取由股东提供的经营资金。根据上述协议,股东如果认为经理行为违背了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就可以通过法庭对其进行制止并有权取得补偿。DYCK(1999)指出,上述合同能否有效执行依赖于股东是否拥有关于经理人员“懈怠”的充分信息,这些信息足以使股东提起诉讼并向法庭证明经理人员的“违约”行为。但是,由于经理与股东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也是两权分离的必要条件),股东并不总是能够获得上述足够信息,因此通过合同控制代理问题也并不总是有效的(SHLEIFER和VISHNY,1997)。特别当政府作为企业股东时,公有产权固有的信息匮乏特征更限制了合同在控制代理问题中的作用。虽然来自中国的证据表明,政府与国有企业经理签订的业绩合同(PER-FORMANCE CONTRACT)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有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GROVES、HONG、MCMILLAN和NAUGHTON,1994;GROVES、HONG、MCMILLAN和 NAUGHTON,1995;LI,1997;SHIRLEY和 XU,1998),但来自更多国家的证据显示,不可知事件、政治压力以及政府违约等因素导致业绩合同发挥的作用甚为有限(NELLIS,1989;SHIRLEY和XU,2001)。
(三)接管
如果大股东直接监督和法律保护都不能有效地控制经理人员的“懈怠”行为,接管市场提供了第三种可能的控制手段。但是如前所述,接管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在于企业股份可以自由流动,外部接管者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接管公司控制权以撤换不称职的经理人员。很显然,国有企业股份不可自由出售的特征,严重限制了接管市场对经理人员的监督作用(YAR-ROW,1986;VICKERS和YARROW,1989)。因此,即使业绩再差,国有企业的经理也不会像私有企业经理那样由于控制权转移而丢掉工作。
(四)破产
即使以上所有机制都不能有效地控制经理对企业效率的侵害行为,一个相对竞争的市场也不会允许亏损企业永远存在下去。当企业亏损到一定程度,破产机制将会自动纠正企业经理的“懈怠”行为(STIGLITZ,1999)。尽管各国对破产程序的规定不尽一致,但基本上所有企业的破产都会导致经理变更、资产清算和债务重组。不过,由于破产后往往很难收回本金(BAIRD和JACK-SON,1985;WEISS,1990;GERTNER和 SCHARFSTEIN,1991;WHITE,1993),债权人和股东都倾向于将破产作为一种对企业经理懈怠行为的事前威胁机制,而不是事后惩罚机制。因此,如果国有企业也会面临真正破产的威胁,破产机制可能就会成为控制国有企业经理道德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遗憾的是,对于国有企业来讲,破产机制的效用依赖于政府特殊的政策选择(VICKERS和YARROW,1989;VICKERS和YARROW,1991;LAFFONT和TIROLE,1991;LAFFONT和TIROLE,1993;STIGLITZ,1993)。众多实证结果显示,政府的这些政策选择更多的是基于政治,而非经济优先的考虑。例如,KORNAI(1980)以及KORNAI和WEIBULL(1983)发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政府通常会对亏损企业进行补贴,而不是让其破产,国有企业的经理很少有动机提高企业效率或避免非盈利的投资。SHESHINSKI和LOPEZ-CALVA(1999)甚至建立了一个模型用来证明,只要对企业进行补贴的政治成本小于让企业破产的政治成本,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就不会停止。DEWATRIPONT和MASKIN(1995)、BERGLOF和ROLAND(1998)以及SCHMIDT(1996)也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政府补贴对破产威胁的限制作用。实际上,国有企业的无效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预算软约束(即政府补贴)造成的(SHIRLEY和NELLIS,1991;WORLD BANK,1995;CLAES-SENS和PETERS,1997;DJANKOV,1999等)。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许多文献论证了公有产权性质对大股东作用的消极影响,但截至目前仍缺乏直接的经验证据为上述理论提供支持。
四、控制大股东的机制
上述分析表明,大股东的存在虽然可以强化对经理人员的监督,但由于与其他股东效用函数的差异,大股东对公司经营决策的干预可能并非基于全体股东的利益,而是可能利用公司资源谋取控制权收益,从而对其他股东的权益造成损害。PAGANO和ROELL(1998)证明,理想的股权结构需要多个大股东的同时存在,并认为他们之间的相互监督可以内部化控制权私人收益,LA POTRA等(1999)也认为,拥有足够股份的第二大股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大股东对其他股东的剥削行为。
最近,已有文献建立了相关模型用于解释同时存在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在 BENNEDSEN和 WOLFENZON(2000)的模型中,企业创始人可以决定公司的股东人数及各自持有的股份数额,由于并不存在提供股权交易的二级市场,股权结构一旦确定将不再改变。创始人为了吸引更多的资金,将会选取多个大股东相互制衡的股权结构以防止单个股东对其他股东的剥削。也就是说,通过对控制权的稀释,创始人向其他股东承诺不会采取单独行动。他们证明,理想的股权结构有两种表现形式,即只存在一个大股东或同时存在多个持股基本相同的大股东②。但是,LA POTRA等(1999)却发现在他们的样本中只有25%的公司同时存在可以跟大股东相互制衡的第二大股东,特别在家族企业内部相互制衡的股权结构更是少见,CLAESSENS等(2000)对东亚国家的研究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GOMES和NOVAES(2001)认为,控制权联盟(CONTROLLING COALITION)虽然可以有效防止单一股东采取单独行动对其他股东进行剥削,但联盟内部的不统一也可能导致公司丧失有利的投资机会。因此,多个大股东同时存在的股权结构只适用于部分公司(例如,存在过度投资问题或有强烈融资需求的公司等)。不同于 BENNEDSEN和 WOLFENZON(2000)以及GOMES和NOVAES(2001)的多个大股东相互合作分享公司控制权的假设,BLOCH和HEGE(2001)假设大股东通过对控制权的争夺取得公司控制权。在他们的模型中,两个大股东为了取得其他小股东的支持以夺得公司的控制权,都向小股东承诺他们会更有效地使用控制权(即承诺不会损害小股东的权益)。他们证明,公司价值是控股股东竞争能力(CONTESTABILITY)的增函数,而控股股东的竞争能力则受到其持有的所有权股份以及对其他股东剥削程度的共同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三个模型虽然对多个大股东行使控制权的方式做出了不同的假定,但他们都强调其他股东的监督可以防止大股东对其他股东的剥削行为。另外,上述模型的理论预期已经得到了实证文献的支持。例如,GUGLER和YURTOGLU(2001)对德国公司的研究发现,第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的股利分配率越高,FACCIO等(2001)对5个西欧国家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结论。EDWARDS和WEICHENRIEDER(1999)证明持有较多股份的第二大股东的存在提高了公司价值。VOLPIN(2002)从经理人员变更的角度对第二大股东的作用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存在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的公司的经理人员变更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显著强于一股独大的公司。EDWARDS和 NIBLER(2000)进一步指出,当第二大股东持有足够多的股份时,不需要组成小股东联盟即可实现对大股东的监督,因此第二大股东的监督作用与其持有的股份比例显著正相关,他们对德国公司的研究证实了上述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