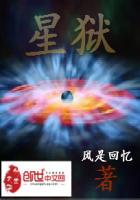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荀子·礼论》云:“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故制礼义以分之。”亦即是说,“礼”起于对人欲的规约和限制。因此,“礼”是人们有意为之,是一种“伪”,也即人为修饰的结果。不过,一旦这种“伪”表现于行动上,不管这个人内心的真实想法是怎样的,它就显示了作“伪”者的一种道德姿态,这种姿态会给对方形成一种压力。这是许多精于权术的人经常采用的伎俩。《陈小手》中的团长也应该精于此道。尽管他对陈小手的“非礼”愤懑不已,但他还可以摆出一副感恩戴德的姿态来,这种姿态就是“礼”,尽管这是“伪饰”的东西,但一旦他尽到了“礼”,他就不至于在道德上落下风,并且可以心安理得地置陈小手于死地。团长并非不清楚陈小手的处境,让这个男“老娘”去接生实在是迫不得已。但为什么团长不把这种“权”变的情况当作常“礼”来接受呢?就像朱老夫子所教诲的那样?就是因为他始终带着“私欲”的眼光去打量女性(尤其是其太太)的身体,而且一旦这种“私欲”被他人僭越,那就会被视为破坏了那个“礼”。一般人没有办法保全这个“礼”,只好变通为“权”。但掌握了生杀大权的团长就不同了,他可以死守这个“礼”,保全自己虚假的尊严。如果把这个故事归结为“礼教杀人”,那就会流于庸俗社会学的说教。其实,问题的真正症结是文化视阈中的真实人性。
这两个故事都有着具体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陈小手》是军阀混战时期,《夫妻》是文革时期。这两个时期可谓天道沦丧、人民倒悬,出现如此离奇之事也是事出有因的。但我更愿意将这两个故事看作是一种心理真实而不是现实真实,它展现的不仅是历史的,更是文化的和心理的真实图景。《夫妻》的故事很容易让人想起庄子寓言中的那株歪脖子树,正是因为这棵树不中规,不合矩,才免于斧斤之祸而得久长。可见这种“抱残守缺”的观念早就渊源有自。但《夫妻》所展现的内容似乎比这还要丰富。当一个弱者没有办法对抗外来的强势力量的时候,他就会“反求诸己”,从自己这边找原因。譬如别人抢他的宝贝,但他打不过别人,只好将宝贝毁掉。实际上就是“自戕”,以求得息事宁人,心理平衡。《陈小手》展现的是另一个极端。当一个强者权势过于强大,他就可以抛开一切道德的阻滞,完全依照“人欲”的逻辑行事,通过“戕人”的方式寻求心理势能的快速释放。
二
更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这两个故事还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文学应该从什么角度来关注身体。在当代社会,身体也成了消费的对象。正如波德里亚所指出的:“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①可以说,“消费身体”成了这个时代最时髦的口号。文身、身体彩绘、器官穿孔等等现象随处可见。不仅如此,身体的消费还进入到文学创作的领域,“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隐私展览、体位特写等等,已经成了一个不可回避也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有些“美女作家”打着解放女性身体意识的幌子,与商业炒作合谋,肆无忌惮地宣泄一己之私欲,将身体抽空成为没有文化意味和人性内涵的空壳。消费意识对身体(主要是女性身体)的侵入,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美丽,二是性欲。在商业资本运作的过程中,这两个方面都是“功用性”的。“美丽之于女性,变成了宗教式的绝对命令。”女人“像保养灵魂一样保养面部和线条”②。同时,性欲也被包装起来,身体被“色情化”,行使着“交换的社会功能”③。波德里亚区分了作为纯粹欲望的身体和作为色情工具的身体,前者蕴含着原始的性欲和生命冲动,是本来意义上的身体。后者则是欲望缺场的结果,身体成了一个商业符号。他指出:“就是在这一范畴中,身体,尤其是女性的身体,特别是时装模特这种绝对范例的身体,构成了与其他功用性无性物品同质的、作为广告载体的商品。”④
那么,问题在于,身体的全面呈露是身体在场的唯一方式吗?在“身体消费”的欲望风暴中,文学究竟何为?是推波助澜,还是力挽狂澜?当然,“身体消费”有着其产生的现实原因,并非完全是人为炒作造成的。身体意识的凸显和泛化,也体现了女性对男权文化中心的反抗,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当一件具有积极意义的新事物尚处于青萍之末时,需要有人倡导之、壮大之。但是,等到事情发展成滔滔大势并且泥沙俱下的时候,则需要加以认真的反思和批判,而不能继续鼓噪助势。我想,这是每一个具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写作者和批评者所应该禀有的德性操持与文化品格。
波德里亚说:“身体的地位是一种文化事实。现在,无论在何种文化之中,身体关系的组织模式都反映了事物关系的组织模式及社会关系的组织模式。”①中国文化可谓源远流长、意蕴深厚,在这个博大渊深的思想宝库中,难道就找不到与身体相关的资源?其实,从老子开始就出现了重视身体的思想。老子说:“贵大患若身。”也即像对待大患一样对待身体。为什么要这样呢?老子解释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②但老子并不是要忘却身体,而是要重视身体。老子说,圣人“为腹不为目”,但求饱暖、恬静的生活,不追逐声色货利,若此可以养性全真,贵身无患。不难看到,当下的身体意识与老子的这种“贵身”思想相去壤霄。当代社会所“贵”的是欲望之身、肉体之身,而遗忘了文化之身、精神之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身体的意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干瘪和空洞,很难想象,一副被抽空了文化意蕴和人性内容的赤裸的肉身,如果不是商业的肆意炒作,它怎么会凌驾于精神之上,一度成为新一代的僭主呢?然而,我们仍然无法抑制问这样的问题:难道身体就是性欲的代名词,而“身体写作”除了写人欲之外就没有什么可写的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夫妻》和《陈小手》这两个故事都是在写身体,不过作者的写法很巧妙,不是就欲望肉身做机械的白描,而是深入到文化的腠理,挖掘社会日常生活中的身体意义。换句话说,这里展现的不是“欲望身体”,而是“文化身体”与“社会身体”。这种写法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鲜见。如杜甫《月夜》诗中有这样的描写:“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安史之乱期间,杜甫带妻小逃到鄜州,后又只身前去投奔刚在灵武即位的肃宗,途中被安史叛军所俘,送于长安,杜甫望月思家,写下了这首名作。这里也写到了“身体”,但意义非比寻常。诗歌表现的是杜甫思念流落鄜州的家人,但他不直接道出,而是用换位思考法来写,即设想妻子在鄜州对月思念远在长安的丈夫。由于在月下伫望时间太长了,露水沾湿了妻子的头发,清辉使得妻子玉臂生寒。这里的“身体”道出的是丈夫对妻子的挂念与爱怜,是夫妻在战乱颠沛中患难与共的生死爱情。再如,在《红楼梦》中也有许多关于身体的细节,甚至可以说,“身体意识”是解读《红楼梦》这部经典之作的一个重要视角。宝黛二人一个是通灵宝玉,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神瑛侍者,一个是绛珠仙子。为了实现“木石前盟”,他们必须幻化成具有世俗欲望的人身。宝玉之“玉”寓指欲望之“欲”,而欲望必须要有身体作承载,所以,这块宝玉获得了一副形貌俊美、品性特异的皮囊。宝玉生来不喜欢男性(准确地说是不喜欢男性身体,俊美的男性除外),而喜欢和同龄的姐妹在一块厮混。他不仅喜欢吃丫鬟嘴上的胭脂,还喜欢同长得俊秀白皙的小后生耳鬓厮磨,关系甚为暧昧。他看到宝钗长着雪白丰腴的玉臂,心想:要是这臂膀长在林妹妹身上倒是可以摸一摸的。这些身体细节意蕴丰富,它不仅可以从多个角度展现宝玉个人的心理世界,还可以展现当时的整体社会趋尚。
由此,“身体写作”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敞露身体隐私,身体不仅仅是个体的,同时也是社会的,它既具有生物性,又具有文化内蕴。在中国文化中,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携带着丰富的社会和文化信息,挖掘和展现“社会身体”与“文化身体”的意义是当下“身体写作”的自我救赎之路。
(原载《名作欣赏》2008年第2期)
坚硬的执著—读吴旭的诗
2010年下半年刚开学不久,信箱里发现一个挂号,厚厚的一本。打开一看,原来是外地一个刚满20岁的文学青年寄来的诗稿,想让我指点一下。一开始随便翻了一下,读了几首诗歌,觉得还不错。后来因为公事撄神,静不下心来,结果一拖就大半年了。我做事有些拖,其实很不好。今年到校后公事稍微少些,每晚在睡觉前,总是想起还有吴旭的诗稿没有回复。心里终究觉得是一件不能就这样放下的事情。
之所以隔了这么久,一是因为诸事干扰,无暇顾及。二是因为这些诗的确值得我认真静心读读,并且要写点什么。
自己从事文学研究已经接近15年了,虽然也读过一些文学作品,但读得更多的是理论著作。这样一来,自己的理性思辨能力是提高了不少,但是文学想象和感悟能力似乎未见长进。读到吴旭的诗稿,我却被这些文字吸引住了。我非常惊讶20岁的人竟然能写出这样凝重、老练、激情的文字来。诗稿一共56首,只有两首是古体诗词,其余都是现代诗。我想,一个刚满20岁的人,他的思想触角能伸到哪里呢?他的人生阅历、生命体验、情感储备能够达到何种程度?他的文字功夫又能锤炼到何等水平?回想自己20岁的样子,正读大二,对未来虽然有所筹划,但还是感觉比较迷茫。那时自己也写些小文章发表,曾经在《九江日报》发了一些豆腐块。当时隔壁班上有个老乡,很喜欢写现代诗,写好了之后给我看,看了半天还是云里雾里的。但是觉得蛮好的,就向他请教如何写,他说要善于捕捉意象。但我始终没有学会。
吴旭的诗,符合他这个年龄,又超出了这个年龄。之所以说符合,是因为诗稿所涉及的内容正是这个年龄的人所思所感。弱冠之年,正是一个编织未来的季节,也是一个绽放可能性的阶段。他将这个年龄所体验到的迷惘、寂寞、愤懑、憧憬、哀伤全部织进他的文字里。如《在大学》,一开篇就透露出他对当下大学生活的反思:在大学/理想佝偻/时光生锈……大学里充斥着虚伪,学生不认真学习,以补考为荣,肆意地糟蹋时间。教师不认真教书,以谎话梦话搪塞课堂。作者反讽地说:光明在夜里传授。并且继续愤恨地写道:
在大学/追求和理想在酒杯战斗/然后夜里在下水道咆哮/艺术系为它画飞翔肖像:/裸女在啤酒瓶奔跑/工程系用泡沫做地基/高建齐天大厦高楼/中文系以火星语格斗/理想和追求发臭
大学的现状与自己的理想相距甚远,但他不甘同流,仍然有自己的追求:
我!拄着/蛆虫不咬/的时光/飞奔的走
对亲情的抒发是文学的母题,作者也能发挥得很好。比如《那年》,作者以那年为题,从母亲年轻的时候写起,用“青黑的辫子”、“粗布衣”、“白皙的脸”、“湖水般的大眼”等意象白描出母亲年轻时的样子,再以“半碗米羹”、“半碗红糖”、“半间瓦房”将那个黑白年代的艰苦写出来了。接下来的岁月,作者连用五个“那年”:
那年我上小学你抱着我去/那年我上初中你牵着我去/那年我上高中你跟着我去/那年我上大学你望着我去……那年你是根发白的竹篙:/我的母亲
情境随时光的流逝而转换,自己长大了,母亲却一点点老去,等到突然某个时候,发现原来年轻的母亲竟然如此衰老。这首诗构思巧妙,用情真挚,读来令人动容。
对爱情的叙写也是诗稿的一个重要内容。《冬夜里守候》造语精密,用情细腻奇峭:
亲爱的/我不愿深夜中那盏灯火/是你黑色眼睛//亲爱的/我不愿小塘底沉默的碎月/是你汹涌的柔情//亲爱的/零点击碎了春花之梦/冬月见证了你漫长守候/我不愿你在冬夜里憔悴/我不愿你在烟火里沉沦
当然,这里的“亲爱的”也可以不指恋人,或者是一个关系很特殊的人。但结合后面的诗句,理解为恋人更合适。这里设想自己的恋人在冬夜里默默地为自己守候,但是自己非常不忍,对恋人流露出心中的爱怜之情。这种写法即古代诗人经常用到的对位法。即站在对方的立场来设想,如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作者这首诗,在意象的设置方面,将对立矛盾的事物放在一起,造成一种语言的张力:深夜灯火与黑色眼睛、沉默塘底与碎月、汹涌与柔情,这三组意象的叠用,将恋人的真情和执著委婉地传达出来了。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能结合家乡当下所发生的变化,将现代化进程中农业文明的蜕化和失落写出来了。《再见宜春》就是这样一首比较有特色的诗。全诗每一句都以“再见”起始,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与“醉人的宜春”说再见,用的感伤情调。一部分是与恼人的宜春说再见。随着现代工业的兴起,美丽的农村也变得大不如前了,以前构成美丽农村画卷的一些东西如今都已成了过去,或者说已经不具有原来的诗意了。青山绿水、广袤的稻田、挥锄的老农、啄食的母鸡、戏水的水牛、赶鸡的老人、赤裸的特产、砍价的乡民、让座的姑娘等等都成了记忆,取而代之的是匆匆的行人、穿梭的车群、林立的商铺、拔地的高楼、死寂的车厢、站立的孕妇、膨胀的市区等。虽说收入提高了,但是家乡并不秀美。读来能引人深思。但是,诗歌在选择意象上有些随意,写到哪算哪,还不够典型和集中,没有代表性。这也影响到了作品的诗意。
吴旭的诗,的确超出了他的年龄。在他的诗里,充斥着诸如黑夜、血、刀剑、坟墓、鬼火、尸骸、殓布、雪花、梦、沙漠等意象。在他的文字所编织的世界里,随处可见寂寞、孤独、哀愁、怨怒等情绪,他喜好用哭泣、销魂、燃烧、颤抖等词语来表达内心的情感。吴旭也给自己取了相类似的别名:尸人、夜子。整本诗稿被称为“尸人的歌”。不知道作者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要这样来为自己命名。也不知道作者在短短的二十年中遭遇了什么事情,使得他在豆蔻年华中专拣那些阴气甚重的意象来装点自己的情感世界,让人读来不寒而栗。可能是受了海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