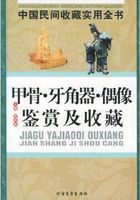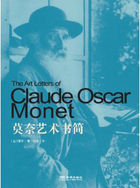本文提示
本文是一篇知识性兼探讨性的文章,其内容有:
1.书画封圣的概况;
2.王羲之、顾恺之生卒年的概述;
3.王羲之之“意”、顾恺之之“神”的新命题在书画史上的地位;
4.二人与时不入的个性;
5.二人之相异。
圣者,凡事皆通,智睿过人者是也。奉圣而过者谓“神”,有曰“神圣”;奉圣不过者称“贤”,有曰“圣贤”。诗有诗圣,医有医圣,书有书圣,画有画圣;文圣云孔丘,武圣乃关羽;各路神仙多自封为圣,是为至高,以示无上焉。
东晋时期有王羲之、顾恺之者,世称书画二圣,道之使然。
王羲之、顾恺之的封圣,虽无官方档案可循,世人皆为所崇。过去,没有学位制度,但社会上赋予艺术学位的意愿在王、顾之前就已萌发。人们在书画领域的地位的确立和晋封,多为后世出于对优秀书画人物成就的敬仰和认可。晋人王隐(生卒年不详,约四世纪上半叶在世,享年70余),推崔瑗(77-142)为“草贤”。现在能查到的最早书法封圣记载,是三国时期曹魏侍中韦诞称张芝为“草圣”。韦诞(179-253)是张芝的弟子,拥称张芝为“草圣”的原因,主要是张芝的草书实冠一时,此议既出,名取青史。
羊欣(370-442)亦有“张芝、皇象、钟繇、索靖,时并号‘书圣’”之论。羊欣所云乃葛洪之说,葛洪(281-341),是东晋著名的道教理论家和药物学家,长年深居山中。他在《抱朴子·辨问》中写道,皇象、胡昭、张芝、钟繇等皆称“书圣”。南齐艺术家王僧虔(426-485)在《又书论》中写道“崔杜之后,其推张芝,仲将谓之‘笔圣’……”陶弘景(456-536)在《与梁武帝论书》中亦云:“伯英既称草圣,元常实至隶绝。”直到庾肩吾(487-551)在评排书家次位时,仍认为“伯英以称圣居首”。
首称王羲之为“书圣”者,乃初唐中期的书画家李嗣真。李嗣真(?—696)在他著名的《书后品》中写道:“右军正体如阴阳四时,寒暑调畅,岩廊宏敝,簪裾肃穆,其声呜也……其芬郁也,可谓书之圣也。”有人以为王羲之封圣与李世民之推崇有关,此见不无理据,但王羲之之封圣,除人品之高尚外,艺术实践和理论阐述的闪亮是其主要原因。
王羲之虽自比钟繇、张芝,但也自认以“雁行”随张芝之后和“仆书次之”现今妇孺皆知“书圣”者,王羲之也!而书界方知草圣者张伯英焉!古今被封“书圣”“书贤”者甚众,唯张、王圣名扬古垂今。
顾恺之,无锡人,其在历代画界地位颇相当王羲之在书界的地位。和王羲之从师卫铄(272-349?)一样,顾恺之也从师卫协。卫协和张墨是同时代人,葛洪在《抱朴子》中说“卫协、张墨并为画圣”,但真正在画界起发展跳跃性作用的是顾恺之。“跳跃作用”指具有优秀精湛的时代画作和对画艺理论的开创性成果,并有推动绘画活动向前发展的辉煌业绩。
日前抱读《晋书》,习思之间,感知王、顾二人在艺术开创和理论生涯中有多处相似:
第一:关于二人的生卒年月,均难以确定,并各有三个相异之处。王羲之的享年是比较肯定的,即五十九岁(虚)。这在陶弘景所整理、作注的《真诰·注》中,以及《晋书》王羲之传(第80卷)中的记载,都是一致的。《真诰》说“至升平五年辛酉岁亡”;张怀瓘亦有“升平五年卒”之论。以此推算,应为303-361年。因为《真诰》中有“今乙丑年说:云五年,则亡后系”的记载。即这是在王羲之去世五年后的记录,无疑是强有力的;第二个观点是清·鲁一同在《兰亭全篇(外篇)》(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年)的《右军年谱》中说“永嘉元年,羲之生”(第728页),“乙丑(兴宁)三年,五十九岁,羲之卒”(第742页)。这就是307-365年;第三个观点是羊欣。羊欣有“羲之年三十三书兰亭序”之论。“兰亭序”文本明言写于“永和九年”(353),即此年王羲之三十三岁(虚岁),推算应为321-379年。
持有上述各种观点者,古今何止数十百家,但近人逐渐多以“303-361”之说为然。其中,中国艺术研究院王玉池先生的研究较为系统和客观。王玉池在《二王书艺论稿》(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中,较集中反映了他的研究成果。
有趣的是,同《晋书》的《王羲之传》一样,《晋书》在为顾恺之立传时,也同样只记录了享年,云“年六十二卒于官所”。何年卒于官所?没有记录。因为二人的政治地位、门第及声望之差异,顾恺之生卒年月的记录较之王羲之之更难寻觅。《中国美学思想史》(敏译著,齐鲁书社1987年)定在344-405年(第632页);樊波定在346-407年(《中国书画美学史纲》(吉林美术出版社,1998,第221页),而傅抱石在《中国绘画变迁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的“中国美术年表”中列为“东晋太元十七年(392)生”(第124页),“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顾恺之卒(七十六),公元467年”(第130页)。
虽然二人都有三个年限之论。但王羲之的生卒有个公认的倾向,而顾恺之的生卒似乎还在讨论之中。中国有记虚岁的延习,历史人物的生卒年月以及由此而涉及的历史事件年代,或多或少一年(也只限一年)是常有的事。但差二年就值得考虑了。
第二个相似之处是在艺术方面,王羲之在学习南方和北方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一反秦汉淳厚、凝重的书风,开创了妍丽流畅而又庄重的“羲之牌”行草,充分体现了王羲之的个性,留下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以及辉煌的《十七帖》《快雪时晴帖》《姨母帖》《橘奉帖》《丧乱帖》《孔待中帖》《圣教序》等作品,影响了晋后历代大书法家及中国的书法历史,虽然在宋齐时代对王羲之在书界的地位曾有过一段异议,以及后来出现颜真卿在艺术风格上与之并立的艺术局面,但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圣位,未发生过根本性动摇。
顾恺之的艺术作品和王羲之一样,现已没有原作传世,但摹本亦反映了顾恺之的高超技艺。《女史箴图》是他的代表作,《中国美术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在援引他作时,说顾笔法如“春蚕吐丝”“春云浮空、流水行地”(第109页)。这种笔法称之为“密体”,与唐代吴道子创造的“疏体”风格形成绘画的两个基本笔法,“知疏、密二体,方可议乎画”(第109页)。除《女史箴图》外,尚存有《洛神赋图》(摹本),《列女仁智图》(摹本)等作品摹本。
学术界对这部分谈议较多,本文不再赘述。
第三:二位的相似之处,还表现在双重艺术身份上:既是书、画家又是文学家。
东晋时期王羲之与谢安(320-385)结成文学集团,在他们周围,聚集着许多文士,其中包括:谢万、孙绰、孙统、袁峤之,以及郗昙、华茂、马虞说、庾友等,“兰亭序集团”成为他们的交游中心。
王羲之的《兰亭序》,其成就首先不是在书法领域,而是在文学领域。
东晋的文学,尤其是散文较为缺少,除过陶渊明(365-427)及其代表作外,《兰亭序》是一篇极为难得的佳作。它的特点是寄情于自然,这在当时是一枝新笔,“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即是代表性笔触。
《兰亭序》一文尚有明显的与哲理结合的特征,“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放浪形骸之外,……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等,这些都是老黄思想的流露,而与哲理相结合的文学作品在魏晋以前是比较少见的。王羲之的耿直和豁达的人生观,明显的受着玄学及嵇康、阮籍等人思想的浸润。
顾恺之的文学作品有《筝赋》。《筝赋》在当时是一篇相当有名的作品,而且顾恺之本人也认为是一部好作品,“恺之博学有才气,尝为《筝赋》,成,谓人曰‘吾赋之比嵇康琴不,赏者必以后出相。’”(《晋书卷92》顾恺之传)。虽然现在看不到其原作,但从历史上的记载上可见一斑。《晋书》九二卷中还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顾恺之在荆州为殷仲堪的参军时,有次他去会稽出差回来,众人问及会稽山川时,顾恺之以“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若云兴霞蔚”相对,引起在座的惊赞。他和桓玄、殷仲堪等人也常常对诗以娱,亦反映顾恺之的文学才能。
第四点相似,王、顾二人不只都在艺术创作上有着突出的贡献这一点上,在理论的开创性见解方面,也极为相似。鲁迅指出,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即谓“觉醒时代”。文艺“觉醒”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有繁荣的社会创作局面,二是有一批时代代表人物和代表时代的艺术作品,三是要有创造时代的创造理论的总结,四是对人的个性给予确认。王羲之、顾恺之正是这个时代的代表。
在理论方面,二人都有着卓越的表现,王羲之有六篇书法著作存世,即《题卫夫人“笔阵图”》、《书论》、《笔势论十二章》、《用笔赋》、《记白云先生先决》《自论书》等。作品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是以“意”论书,强调作书要“有意”。其《自论书》云,“吾尽心精作亦久,寻诸旧书,惟钟、张故为绝伦,其余为小佳,不足在意”。也就是说除钟、张外,其他作品未很好的表现“意”;随后又说“顷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魏晋六朝书论》,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103页)《全晋文》第二十二卷中,王羲之又说:“复与君,斯真草所得,极为小少,而笔至恶,殊不称意。”又说“君学书有意,今相与草书一卷”(同上,第二十三卷);飞白不能乃佳,意乃笃好(同上第二十六卷)等。
以“意”评书,在王羲之以前尚少有人提出,王羲之所云“意在笔先”者,笔者以为并不只指创作方法,而首先在于审美意识,(见拙文2002.9.13.“书法导报”《形、仪、神与审美意识的划分》及2002.6.12《书法导报》,《评集王书(圣教序)及其临习》等)。以“意”为审评标准,以“意”为书习目标,以“意”为创作方向,这同以往的“法象于物”截然不同。法象于物者,曰“为法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方得谓之书矣”“黄帝之史,沮诵,仓颉,眺彼鸟迹,始作书契”“字画之始,因于鸟迹”,(卫恒:《四体书势》,蔡邕《笔论》)“皇颉作文,因物构思,观彼鸟迹,遂成文字”(成公绥:《录书体》)。这些描述,都是以是否符合物象为审美和评比标准,而王羲之以“意”为标准,把人们的着眼点从物象引转到了意象领域,向理性思维推动了一大步,给了人们一双理性的眼睛。人们在认识论上,把理性认识(当然是指正确的理性)作为一种更深刻、更全面、更本质的认识来看待的。它是艺术实践深化的标志。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王羲之的六篇文章的情况比较复杂,比如孙过庭(生卒年不详,其《书谱》完成于687年)曾评《笔势论》为“意乖方拙,详其旨趣,殊非右军”。但《自论书》确系王羲之之所为。其他有的文章在唐初就有争论,而《书论》《记白云先生书诀》也在宋前尚未见到。
一个人的“意”是在长期的艺术实践和理论学习中得来的,是比较稳定在思想中的一种意识形态,它一经形成,又反过来指导从艺者的艺术实践和审美情趣。
顾恺之在绘画领域的理论贡献,同样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他的著作有《论画》、《魏晋胜流画赞》和《画云台山记》等三篇。在刘义庆(403-444)的《世语新说》、张彦远(813?—879?》的《历代名画记》以及《太平御览》等著作中,还在一些其他著作中均有片断记载。
和王羲之的“意”一样,顾恺之的画论思想全在一个“神”字。关于形神的关系,西汉的刘安(前179—前122)在《淮南子》东汉的王充(29-97)在《论衡》里以及魏晋时期都有人提及,但当时的概念比较零散和模糊,并且常限于对人物仪态评价的范围内,不若顾恺之明确规定为艺术高下的衡量准绳。“一像之明珠,不若悟对之通神也。”“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失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五)“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汉魏六朝收画论》,湖南美术出版社,第270页),以及“以形写神而空其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五。)可以看出,顾恺之将“神”作为评判画作的最高标准,作为指导绘画创作的原则,这也是画界的新命题,“以形写神”,“形”即画和画的形状,“神”即精神、意蕴、内涵,是画作的内容,是属于雄壮美、清秀美、还是阳刚美、阴柔美这些在审美上的概念,是品画上的意识。“以形写神”即用画来反映客观事物的精神内涵,不只是反映“如春蚕吐丝,紧劲连绵,风趋电疾”之类的物象。一幅好的艺术作品,应该是形式美和内容美的一致,但内容美是主要的。所以顾恺之提出的“以形写神”,明确了绘画的目的是为了表示“神”,是为了“写神”,而不是为了写生。
“迁想妙得”是顾恺之的又一理论贡献,在《魏晋胜流画赞》一文中,开宗明义,“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迁想妙得”也是属思维范畴的概念。对“迁想妙得”的正确理解,不只涉及正确阐绎顾恺之的本意,也涉及发掘历史遗产和遗产的精神继承。“迁想”,是一个对经验和认识的概括过程,是一个抽象过程,把过去自己的经验,所掌握的实际材料以及从他人那里学来的知识综合起来,对所要描绘的对象(顾恺之称为“生人”)作理论的思索整理、加以概括、进行抽象,去丑存美,去次存主,去伪存真,这个过程就是“迁想”。“迁想”不是直观的过程,而是抽象的过程。贡献正在于此。“迁想”之后创造出一个崭新的艺术形象,这个崭新的艺术形象,已经不是现实中的山水人物,而是艺术的山水人物,其形象更饱满、更生动、更具有代表性。这就是“妙得”。“妙”就“妙”在是艺术的,而不是现实的这一点上。所以在“迁想妙得”这个论断词组里,“迁想”是主要的,“妙得”是“迁想”的结果,“迁想”是“妙得”的起因,二者是因果关系,不是并列关系。
王羲之的“意”和顾恺之的“神”是在中国书画历史上把评价条件提到理念高度的新命题,和曹丕(187-226)提出的“文以气为主”把文学提到一个新高度一样,它也把书画艺术从物象审美提高到意象审美的新高度。他们总结书画技巧、阐述技巧与所表现内容的关系的同时,也指出了提高书画技巧的方向。对中国书画艺术的影响极为深远。千百年来他们的理论一直滋润着中国艺术家的成长,推动着中国艺术的发展。
我们在高度估量王羲之的“意”和顾恺之的“神”的同时,也必须指出,这个“意”和“神”的概念不免有点粗略,不是很精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完善,这是历史的必然,是为客观社会条件所限制的,不必要求古人,正如当牛顿开辟经典力学理论时,不必要求他涉及量子力学理论一样。重要的是,王、顾二贤开辟了一个领域,抛弃了过去“法象于物”的审美原则,树立了新观念。“意”、“神”的概念是具有普遍的、永恒的理论价值,完善这个理念,是后人的事。
第五,王、顾二人的相似,还表现在艺术家的独立人格方面,而人格的独立也正是社会觉醒的表现。“坦腹东床”是人们皆知的故事,表现了王羲之与众不同的个性。但他的独立个性表现不至于此。“羲之既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复授护国将军,又推迁不拜。”(《晋书》卷80.)这时,扬州刺史殷浩写信,劝王羲之接受召命,而王羲之回信,曰“吾素无廊庙志,直王承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晋书》卷80)显示了王羲之对高官地位的蔑视。
公元351年,前会稽内史王述母亲去世,述乃去职守丧。朝遂命王羲之为会稽内史。在此期间,王述以为王羲之会来拜访他,“每闻角声,谓‘羲之当候矣!’辄洒扫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顾,述深以为恨”(《晋书》卷80)。这证明王羲之并不是趋官附势之辈。公元354年,王述守丧期满。代殷浩为扬州刺史,时王羲之为会稽内史,王述便派下属经常寻隙于会稽,“羲之深耻之,遂称病去郡。”“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徧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晋书》王羲之传)此段时间王羲之经常和人交流,“羲之既优游无事,与吏部郎谢万书曰‘古之辞世者,或被佯狂,或污身秽迹,可谓艰矣!今仆坐而获免,遂其宿心,其为庆幸,岂非天赐!’”(《晋书》王羲之传),对死生表示很为淡然。从这些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王羲之的个性是与时人完全不同的,是独立于当时的社会意识“之外”的人。他的书法作品比之于秦汉,也体现了独立反叛的个性。秦汉以前的书法风貌是以敦厚重实为特征,而王羲之创造的行书,则以妍丽、明朗为特点,也反映了王羲之不因循守旧的个性。
顾恺之的艺术生涯也反映了他不同一般人的独立性格。但与王羲之相比,他带有浪漫的倾向。一次,顾恺之把许多画装进橱柜里,然后贴上封条,寄存在桓玄处。桓玄深知里面是些珍贵的画作,“乃发其厨,后,窃取画,而缄开如旧以还之。”顾恺之见到封条和过去“一样”,但画不见了,便郑重而又自言自语地说“妙画通灵,变化而去,亦犹人之登仙。了无怪色。”看来他的确认为是“通灵飞天”了,所以才“了无怪色”。
义熙年间(405-418)顾恺之为散骑常侍,常与谢瞻聊天、对诗。有一次二人在月下吟咏,“瞻将眠,令人代已,恺之不觉有异。遂申旦而止。”谈话的对象已经换了一个人,他还未察觉,可见其精神之奇异,可见其与众之不同。
顾恺之对人非常诚直,从不异想他人。恒玄曾拿一柳叶,对顾恺之说,这是蝉用以隐蔽自己的叶子。用它自蔽,别人看不见你,“恺之喜,引叶自蔽。玄就溺焉。恺之信其不见已也,甚以珍之。”(《晋书》卷92)
王羲之、顾恺之性格之不合时宜,不只是个体的特征,更重要的是体现着社会的特征,这就是魏晋时期社会觉醒在人们性格上的反映。
第六,王、顾二人身上反映的人性的觉醒,不只反映着艺术家的个性之与社会的不和谐,还反映在对下层人物的同情上。
大约在永和十年(354)左右,王羲之游蕺山,见一个老太婆持六角竹扇卖之,“羲之书其扇,各为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谓姥曰:‘但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钱矣!’姥如其言,人竞卖之。”(《晋书》卷80)说来也奇,顾恺之也有为人画扇面的记载:“一次,他替别人画扇面,扇面上画的是文学家嵇康和阮籍,没有点眼睛就把扇子还给了主人,主人问他,为什么不点眼睛?他说,点了眼睛,他们就要说话了。”(《上下五千年》中国致公出版社,第655页)。“寺画赠金”又是一例,兴宁年间(363-365)金陵瓦官寺修建,顾恺之认捐百万钱。日已近,仍无声。不日,他在寺内画了一幅维摩诘像,既成,光耀佛屋。要求第一天来看的人,每人施舍十万,第二天来看的每人五万,俄顷而得百万钱。把眼睛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时代认识,转至对人民的正视和笔助,可谓二位之行动的雷同,也反映着时代的觉醒。
在讨论了二人的诸多相似点(当然还有许多)之后,和所有事物一样,王羲之和顾恺之二人也有相异点。首先是性格,王羲之是个耿直而较为严肃、不苟言笑的人,晋书上说“羲之幼讷于言”,实际上一生都如此,虽然他敏于思,仍具有稳健的行事风格,而顾恺之在敏于思的同时,“好谐谑,人多爱狎之”(《晋书》顾恺之传),桓温(312-373)也说顾恺之“痴黠各半”。其次,王的诸多论文中,有一些为人所托,而顾的论文均为本人所笔。第三,王有道家思想,顾乃儒家传承,等等。二者都出生于世家大族,而王位更重。二人之相异,不是本文之重点,特简之。
在置笔本文时,偶然忆起我在求学时的一件事。1959年冬,在西北大学礼堂旁的新华书店里浏览,意外读到了郭沫若写的一篇关于王国维和鲁迅的文章,列叙了二人非常相似的求知、从业道路和相似的思想体系。呜呼!世有如此之相似者也。
2004年于西安兴隆园,2008年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