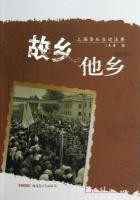一般认为张爱玲在1975年写完《小团圆》,根据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先生在《小团圆》内地首发式上的演讲,张爱玲在1954年或1955年,大约35岁左右已经计划写自己30岁以前的故事。在《小团圆》的尾声处,张爱玲写九莉做了一个梦,梦见在《寂寞的松林径》背景中,她和之雍以及好几个小孩在一起。“二十年前的影片,十年前的人。她醒来快乐了很久很久。”《寂寞的松林径》是1936年的电影,那么,回忆/写作的时间自然是二十年后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不难看出,张受玲的回忆始终执著于30岁以前的人生岁月。笔者将尝试分析《小团圆》中的生命时间和叙事时间。
一、童年和Toots(少女)时期
《小团圆》中的生命时间正如《对照记》中的自我分析,明显呈现童年、青年、中老年三个阶段,不同阶段之间各有标志性事件。九莉跨入成长期的标志性事件是父亲再婚和自己被关禁闭,跨出成长期的标志性事件是离开上海、自我逃离。《小团圆》详写的是崎岖成长期这一段,其次是童年和Toots(少女)时期,离开上海之后的岁月基本上是“下接淡出”的写法。
在父亲再婚之前,因为父母离婚、父亲抽大烟、打吗啡针、赌钱等事件,家庭生活谈不上美满,但父亲在寂寞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还是喜欢九莉的。让她坐在他身上,和她说没用的话,叫她替他剪手指甲,“她看见他细长的方头手指跟她一模一样,有点震动”。“他也是喜欢夹菜给她,每次挖出鸭脑子来总给她吃。他绕室兜圈子的时候走过,偶尔伸手揉乱她头发,叫她‘秃子。’她很不服,因为她头发非常多,还不像她有个表姐夏天生疮疖,剃过光头。多年后才悟出他是叫她Toots。”多年后悟出的刹那,温暖和感伤并起。随着继母的到来,父亲已经不再是往日的父亲,家不再是往日的家。父亲曾经不无宠爱的叫声,渐渐变成了冷漠、打骂,乃至禁闭。在被关禁闭期间,生了大病却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医治,几乎把命丢掉的九莉,毅然决然地从父亲的家里逃了出来。
好在还有童年,那如遗忘的火种,永远能在我们心中复萌的童年。在香港念大学的时候,有一天回宿舍,在门口摁铃,对海的探海灯照过来,九莉沐浴在蓝色的光雾里,“仿佛回到童年的家一样感到异样,一切都缩小了,矮了,旧了。她快乐到极点”。突如其来的强光照射,将九莉带回童年的家,那个永远也回不去的家。即使在现实中已经失去或毁坏,我们在其中度过童年的房子,都是我们昔日的庇护所,它静静地等待并欢迎我们的到来。在童年以后的人生中,我们离开它,失去它,再煞费苦心地寻觅它。
《小团圆》在同一页中对照着描述了两个相隔多年的场景。前一个场景:“韩妈弯着腰在浴缸里洗衣服,九莉在背后把她的蓝布围裙带子解开了,围裙溜下来拖到水里。”“‘唉哎嗳!’韩妈不赞成的声音。”“系上又给解开了,又再拖到水里。九莉嗤笑着,自己也觉得无聊。”后一个场景:“多年后她在华盛顿一条僻静的街上看见一个淡棕色童化头发的小女孩一个人攀着小铁门爬上爬下,两手扳着一根横栏,不过跨那么一步,一上一下,永远不厌烦似的。她突然憬然,觉得就是她自己。”电光石火之间,两个小女孩合二为一,仿佛前世和今生的分身,无所事事的童年,色调单一的生活,孤独无聊的主角,正经历着宁静平和的岁月。随着岁月流逝,“我们努力要认识的却是无事件的生活,一种不牵涉别人生活的生活。正是别人的生活才将事件带入我们的生活。从这依恋宁静和无事件的生活的角度看,所有的时间皆可能成为‘创伤’”。从某种意义上说,晚年离群索居的张爱玲不过是想回到童年那种不牵涉别人的生活状态。
张爱玲在早年的散文《自己的文章》中强调人生安稳的一面,“虽然这种安稳是不安全的”,“但仍然是永恒的”,“它是人的神性”。事实上,童年之于张爱玲的印象正是安稳和永恒,那是一段“没有生老病死”的“沉酣的岁月”,“像有种巫魇封住了”。对于九莉和之雍感情稳定的那段日子,张爱玲是这样形容的:“她觉得过了童年就没有这样平安过。时间变得悠长,无穷无尽,是个金色的沙漠,浩浩荡荡一无所有,只有嘹亮的音乐,过去未来重门洞开,永生大概只能是这样。”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光,世界美丽而宁静,平安而悠长,张爱玲对童年的体悟完全是存在主义的。
加斯东·巴什拉在《梦想的诗学》写道:“童年深藏在我们心中,仍在我们心中,永远在我们心中,它是一种心灵状态。”“我们的童年在重新与我们的生活融为一体前,经历了长久的等待。这种重返只在生活下半期当人们走下坡路时才能实现。”《小团圆》中篇幅不多的童年记忆,正如巴什拉对童年的精彩阐释。对于张爱玲而言,童年的记忆不是历史的记忆而是心理的记忆、存在的记忆,在沉酣的恋情中,那种什么都不发生的存在状态再次降临。童年和爱情,正是人体验诗意存在、感受神性的时间。金色的沙漠,嘹亮的音乐,过去未来重门洞开,在爱情最灿烂的当下,此刻和彼时遇合、重叠,永生的体验再现。
二、十八岁和三十岁
如果说童年是九莉生命中最美好最重要的时光,那么十八岁和三十岁则是她成长期中最关键最突出的生命时间。《小团圆》中,直接表示时间的词语并不多,十八岁和三十岁是例外。十八岁是成年的标志,也意味着成长期的开始,三十岁则是成长期/青年期的结束,是生命走向衰老的开始。当然,无论是十八岁还是三十岁,与其说是身体年龄不如说是心理年龄,其象征意义远大于现实意义。
正是对未来充满幻想,对即将到来的十八岁兴奋不已的时候,九莉却“连生两场大病,差点活不到十八岁”。因而在姑姑笑言“等你十八岁我替你做点衣裳”时,九莉想的却是:“不知为什么,十八岁异常渺茫,像隔着座大山,过不去,看不见。”从小说的叙述来看,九莉在十八岁之前至少生了三场大病:担心父亲再娶的事,急出了肺病;被父亲关禁闭期间生了场差点送命的大病;逃到母亲身边后因倍感压力而患了伤寒。九莉的每场病都伴随着精神上的压力和心理上的焦虑,甚至可以说正是精神和心理的因素导致了她身体的不适。每次在死亡的边缘挣扎,都是那样惊心动魄。真的到了十八岁,反而只是云淡风轻地一笔带过。大学期间功课拔尖,拿奖学金,战争却使她再次面对死亡的威胁。连分数也在战火中烧了,几年功名付之流水,大学也未能毕业。难怪张爱玲在二十余岁就说出“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这样沧桑的话,她的磨难从未成年时已经开始。
《小团圆》中,燕山对九莉说:“你大概是喜欢老的人。”张爱玲用第三人称写道:“他们至少生活过。她喜欢人生。”这里的叙述带有后设的意味,指向之后与更老的赖雅之间的婚姻。张爱玲喜欢老的人,却不喜欢自己变老,三十岁这个年龄给张爱玲以极大的震动。早期代表作《金锁记》劈头便是:“三十年前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十八春》中直言三十岁是生命时间的分水岭,“对于三十岁以后的人来说,十年八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而对于年轻人而言,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到写《小团圆》时,三十岁更是成为构思的核心时间。小说的第一页便从九莉“快三十岁的时候”,直接跳到“过三十岁生日那天”。以三十岁为界,站在三十岁之后,追忆三十岁之前的岁月,正是《小团圆》的叙述基调。偶有越界,也是因为前事触动,思绪转向多年后。
三十岁生日那天,“夜里在床上看见阳台上的月光,水泥阑干像倒塌了的石碑横卧在那里,浴在晚唐的蓝色的月光中。一千多年前的月色,但是在她三十年已经太多了,墓碑一样沉重的压在心上”。三十岁是一道坎,过了这道坎,从此听见时间流逝的声音,再也抓不住,留不住了,只能身不由己地跟着时间向衰老向死亡跑去。一连串的蒙太奇,下接淡出。于是,偶尔听见印度门警说“早安,女孩子”,张爱玲再次以第三人称出场,“她三十岁了,虽然没回头,听了觉得感激”。女孩子,那是父亲叫她“Toots”,她听成“秃子”感到不服气的年纪。虽然感激,但她丝毫没忘自己已经三十岁了。
值得注意的是,张爱玲或九莉对三十岁的恐惧始终和性别联系在一起。男人老了,照样有人喜欢。女人三十岁开始色衰,逐渐失去自己的市场价值,或者说男人眼中的价值。父亲和母亲便是最好的例子。奶奶因为其父的意志,嫁给儿子都比自己大的爷爷。母亲决意反抗命运,追求理想的爱情,坚持与父亲离了婚,母亲单身一人,才貌出众,虽然也想找个归宿,最后却四面楚歌。父亲带着两个孩子,抽着大烟,仍“成为亲戚间难得的择偶对象”。甚至曾经笨拙自卑的九莉,也取得了对母亲的完胜,因为“时间是站在她这边的”。当然,九莉知道自己胜之不武,更知道“自己将来也没有好下场”。对于男女关系的“清醒”认识,为多年后九莉和汝狄的婚姻埋下伏笔。“她也不相见恨晚。他老了,但是早几年未见得会喜欢她,更不会长久。”张爱玲是认命的人,即使不无委屈。从某种意义上说,张爱玲或九莉对三十岁的恐惧,正是男权文化造成的。
三、小说的叙事时间
“第一、二章太乱,有点像点名簿……我曾考虑建议把它们删去或削短”,这是宋淇在读完小说手稿后,致信给张爱玲时说的一段话,似乎颇能代表一部分读者的心声。前面说过,《小团圆》的基调是追忆九莉三十岁之前的生活。第一、二章讲述的香港生活,是九莉前三十年岁月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对她之后的人生有重要影响,删去自然不是一个好建议。当我们从叙事时间的角度对小说文本展开分析时,第一、二章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
在叙述学理论中,叙事时间是和故事时间(或现实时间)相对的概念,也被称为文本时间。现代小说的叙述者在讲述故事时,往往并不遵循事件发生的现实时间顺序,而是打乱故事时间,根据叙述者的意图、愿望、感觉或心理,以一种个人化的时间顺序,重新组合事件。叙述者自由转换事件发生的顺序,任意放大事件的细节,放慢或加快事件的节奏和速率,甚至引入非现实的虚幻时间,致使故事时间(或现实时间)和叙事时间(或文本时间)出现一定程度的分离。对于读者来说,既要理顺小说中的故事时间,又要追问隐藏在叙事时间背后的叙述者意图,以及个人化的叙事时间所带来的文本效果。
张爱玲没有按照现实时间讲述九莉从童年到三十岁的成长经历。小说从大考的早晨等待的心情写起,倒叙九莉快三十岁时的心情,依然是等待;写九莉三十岁生日,带出故事时间的终点。对九莉而言,三十岁是人生的断裂,“像倒塌了的石碑”。定好全文基调和故事时间的终点,小说正式进入九莉的香港生活。这段经历在九莉的成长过程中既是一个过渡,又是一个转折。九莉对生命和时间的体悟正是在香港最终完成的,而这种体悟是整篇小说追忆往事的起点和背景。
第一、二章虽然都写九莉的香港生活,但各有侧重。第一章劈面倒叙九莉三十岁生日,暗示了这章隐含的主题——衰老。母亲来港小团圆时,九莉已经十八岁了。通过对母亲的观察,九莉有了对衰老的最初体悟。母亲到香港后第一次出现在九莉面前,“午后两三点钟的阳光里,母亲看上去有点憔悴了,九莉吃了一惊”。成年的女儿与母亲别后重逢,轻描淡写的“有点憔悴”急转为“吃了一惊”的内心震动。去浅水湾饭店看母亲,“九莉非常诧异,从来没看见她母亲不大方。也没见她穿过不相宜的衣服,这次倒有好几件。似乎她人一憔悴了,就乱了章法”。叙述者进一步用“非常诧异”形容九莉的感受,再次相见,母亲还是“憔悴”,显然不是因为旅途劳顿,而是开始迈向年老色衰的人生下坡路了。九莉不禁回忆起早年母亲和姑姑换上漂亮衣服出去跳舞的情景,“其实就连那时候,在儿童的眼光中她们也已经不年青了”。如今,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坚持离婚的清高骄傲的母亲,竟然要去投奔男人了。九莉“只替她可惜耽搁得太久,忽然见老了,觉得惨然”。站在一堆人中,九莉送走了前去新加坡的母亲,第一章也就戛然而止。九莉既是为母亲感到惨然,也是为三十岁的自己感到惨然。每个个体都无力抗拒时间的力量,不论是时髦漂亮的母亲,还是丑小鸭的女儿。
如果说第一章侧重对衰老的感悟,第二章则隐含着对死亡的体验。这章把战争纳入故事的前景,“不喜欢现代史,现代史打上门来了”。还是张爱玲一贯漫不经心的笔触。“遇到轰炸,就在跑马地墓园对过。冬天草坪仍旧碧绿,一片斜坡上去,碧绿的山上嵌满了一粒粒白牙似的墓碑,一直伸展到晴空里。柴扉式的园门口挂着一副绿泥黄木对联:‘此日吾躯归故土,他朝君体亦相同’,是华侨口吻,滑稽中也有一种阴森之气,在这面对死亡的时候。”面对与战争相伴的死亡,一向旁观世态人情的九莉也不免发生震动。“我差点炸死了,一个炸弹落在对街”,心有余悸的口吻。战争时代,每个人的生存都受到威胁,“昨天枪林弹雨中大难不死,今天照样若无其事的炸死你”。死了,一切便结束了。给九莉奖学金的安竹斯也死了,九莉“这才知道死亡怎样了结一切……现在一阵凉风,是一扇沉重的石门缓缓关上了”。在战争的危机中,年轻的九莉深感活着最重要,“总要活着才这样那样”。然而,她再也无法摆脱沁入骨髓的世界末日感。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中,九莉人生中的亮色是没有生老病死的童年岁月,过去未来重门洞开的金色永生的初恋时光。它们共同的品质正是安稳和永恒。然而,时间和时代都在破坏和毁灭,童年永远地过去了,爱情也幻灭了,没有永生,没有安稳。在衰老和死亡面前,个人如此渺小,生命如此脆弱,时间如此虚无,可把握的只有身边的琐碎细节。“比比也说身边的事比世界大事要紧,因为画图远近大小的比例。”在早年的《更衣记》中,张爱玲提醒读者注意古代中国服饰的细节,“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周蕾在《现代性和叙事——女性的细节描述》一文中认为,细节描述不遵循传统的中心主义和目的性,“把细节戏剧化,如电影镜头般放大,其实就是一种破坏,所破坏的是人性论的中心性(centrality of humanity),这种人性论是中国现代性的修辞中经常被天真地采用的一种理想和道德原则”。回到《小团圆》的文本世界,我们看到张爱玲借九莉之口郑重申明自己不相信国家民族主义,那要信什么呢?“她没想通,好在她最大的本事是能够永远存为悬案。也许要到老才会触机顿悟。她相信只有那样的信念才靠得住,因为是自己体验到的,不是人云亦云的。先搁在那里,乱就乱点,整理出来的体系未必可靠。”九莉的这段自白,也是对《小团圆》写作原则的暗示。《小团圆》只有体验过的信念,只有片断的细节,宁可“乱”,也不要体系。
从小说的叙事时间来看,《小团圆》的结构的确颇为凌乱。九莉成长过程中不成体系的琐碎事件,偶然的所见所闻,随意的文艺片断,不时的恍惚梦境,整部小说由无数的细节构成。细节和细节之间的链接仿佛电影的蒙太奇手法,叙述者经常借助“以前”、“现在”、“后来”、“久后”、“很久以后”、“多年后”之类表示时间的词语,游走、跳跃于过去、现在、未来之间。试举一例。
九莉在纽约打胎的场景竟然穿插在对九莉和之雍热恋的描述之中。“他们在沙发上拥抱着,门框上站着一只木雕的鸟”,那鸟自然是幻觉,象征着九莉内心的惊恐。镜头淡出,笔锋一转,下接淡入,“十几年后她在纽约”,躺在浴缸里,“就像已经是个苍白失血的女尸,在水中载浮载沉”。上海和纽约,隔着十几年的时间,两组镜头时空交叠,不变的是九莉依然在惊恐中挣扎。怀孕已经四个月的九莉,正在等打胎的来。“原来是用药线。《歇浦潮》里也是‘老娘的药线’。身死异域,而死在民初上海收生婆的药线上,时空远近的交叠太滑稽突梯了。”张爱玲果然够狠,十几年的时空交叠中还要套上一个更遥远的现实和虚幻时空的交叠,在惊恐中载浮载沉的也不只是一个九莉,而是无数把命拼上去的女人。九莉肚子疼得翻江倒海,汝狄吃烤鸡吃得津津有味。镜头再转,达到恐怖的高潮:“夜间她在浴室灯下看见抽水马桶里的男胎,在她惊恐的眼睛里足有十吋长,毕直的欹立在白瓷壁上与水中,肌肉上抹上一层淡淡的血水,成为新刨的木头的淡橙色。凹处凝聚的鲜血勾划出它的轮廓来,线条分明,一双环眼大得不合比例,双睛突出抿着翅膀,是从前站在门头上的木雕的鸟。”十几年的时间跨越,镜头依然是顺接,场景之间共同站着那只象征内心恐怖与不安的幻觉中的木雕鸟。恐怖的高潮之后,是张爱玲惯用的反高潮手法:“比比问起经过,道:‘到底打下来什么没有?’告诉她还不信,总疑心不过是想象,白花了四百美元。”如果证实那不过是想象,恐怖程度还要无限地加倍。
张爱玲对叙事时间的处理使《小团圆》成为罗兰·巴特所说的具有可写性的现代文本,在不断的阅读中,不同读者会发现新的意义,产生新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