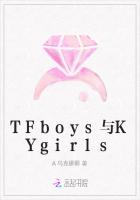对于传闻,严蕊并不以为意,当她成为一名歌妓的那天起,她就已经告诉自己以后的日子无论面对什么都要做到淡定释然。
而严蕊却不知道,传闻之后等待她的却是更大更凛冽的风雪,是那个冰冷的严刑,是阴森的牢狱。而这一切的发难者就是朱熹。
朱熹,号晦庵,南宋思想家,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他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对于他的主张,生性风流不羁的唐仲友是不以为意的,酒席宴会的言辞中就免不了会有些许的不尊与轻视,于是,他与朱熹间就有了点嫌隙与不快。那一年,朱熹受皇帝特命巡视浙江,他到了天台后就听说了唐仲友与严蕊间的种种传闻,于是,于公于私,朱熹决定惩办唐仲友。就这样,朱熹以“官府不得宿妓”定唐仲友的罪,找来严蕊要她承认二人有染。朱熹以为,一个弱质女子,想来吃不得刑拷逼问的,况且,欢场女子,也不会拿男女间的情爱当回事,只要刑拷一上,想来不论有无,都自然会认了的。到那时,他就有了切实证据指控唐仲友了。但是朱熹却没想到,任凭百般痛打,严蕊就是不承认自己和唐仲友有染。于是,朱熹将严蕊关在狱,想以此迫其承认,但严蕊的口供一如当初,朱熹从严蕊口中得不到切实证据,无奈中,只好以“蛊惑上官”为名将她发配到绍兴,让下级官员继续逼供。
绍兴的知州也是道学之士,在他眼里,自认为“从来有色者,必然无德”,所以,他最容不得的便是风月颜色,轻柔妩媚。于是,严蕊天生的娇颜与柔弱,竟然成了他拷问的理由,对严蕊又是一番刑拷打。在严刑与酷打下,严蕊依旧不肯招半个字。就这样,严蕊又被关入大牢。这时候,监狱里的看守见此情形都好言相劝:“上司加你刑罚,不过要你招认。女人家犯淫,极重不过是杖罪。况且你现在也已经被杖刑过了,如今说了,也就不用受这等牢狱之苦了。”而严蕊,虽被打得伤痕累累,精神委顿,却依然凭着纤纤傲骨,以金石之声掷地:“身为贱伎,纵是与太守为好,料然不到得死罪,招认了,有何大害?但天下事,真则是真,假则是假,岂可自惜微躯,信口妄言,以污士大夫!今日宁可置我死地,要我诬人,断然不成的”!这样的节气与傲骨,纵然是身为男儿也为其敬,也为其叹!
这一场风月案,终于还是因为唐仲友的不服而告到了孝宗皇帝那里。唐仲友指责朱熹“酷逼娼流,妄污职官。公道难泯,力不能使贱妇诬服”,在唐仲友的状子里,他只说朱熹的“酷逼”与“妄污”,却只字未提严蕊的冤枉与无辜,不仅如此,对于严蕊,他一直以“娼流”与“贱妇”相称。所谓的权贵与娼流,谁比谁更凉薄!这一场争论,于孝宗看来,也只不过是“秀才争闲气耳”,于是,就把唐仲友与朱熹两下平调结束了争端。
严蕊坚不改口,而朱熹又被调走,绍兴知州觉得关着严蕊已没了意义,就将她放了出来。而此时的严蕊,却已是“委顿几死,奄奄一息”。纵然如此,自始至终,她都坚持了那句:“循分供唱,吟诗侑酒是有的,并无一毫他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