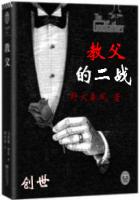这是一条重复的新闻,或称旧闻。所以,庄严的大报是决不肯登载的,而小报也难,因为小报是大报管的……但这事有意思,故我弄了个花招--杜撰一个玄乎的标题。
中国文联在威海开会。临行之前,我给我们村总支书记仙钰打个电话。他听了,说好啊,一定要去看,很近的,也就我们村到笏石的距离,顶多三十公里吧(在威海我问了开车的师傅,实际是六十公里,山东的路修得比我们好多了,给仙钰造成了错觉)。仙钰是个细心的人,我到威海的第二天下午,手机便响了。打电话的是林鸿恩--我们村驻山东荣成鲍鱼养殖总公司的出纳。他笑问还记得吗,我答当然,少年时在他家跟他喝醉过好几回。他弟鸿榜是我同学,但滴酒不沾。
会议开得很精彩,中国文联请到仲呈祥、傅庚辰等艺术大家给我们上课。老一辈艺术家那种浩然正气如久旱之甘霖,倒不是折服于他们那份盛名,而是心灵确如焦灼的荒漠……尽管如此,第三天我还是从会上逃出去--毕竟对故乡父老兄弟生计的牵挂,胜过对艺术的追求--对于文坛,我一直是个三心两意的“同路人”。
鸿恩带着荣成海兴水产公司的车直接到宾馆接我。车子穿越威海市区,往东南方向沿海滨的路疾驰。天下着蒙蒙细雨,路上少有行人,路边与故乡相似的风景,是一排旋转的风电机,从机杆上标明的大字,分属两家大型国企,从颜色判断,也是近年实施科学发展观、倡导可再生能源的产物。风电机下人烟稀疏,可见这里人口密度比莆田稀少。
四十分钟后,我来到荣成海兴水产有限公司。公司设在荣成俚岛镇,名曰岛,其实是半岛,地势与石城半岛相近。公司是民营企业--我从索取材料的过程得出这一结论:办公室人员几经反复,竟拿不出一份诸如“年终总结”、“年度发展计划”、“总经理先进事迹”之类的材料,仅给我复印几份国务院、国家教育部和威海市政府发给的“科技进步一等奖”、“水产新产品”和“劳动模范”证书。
海兴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孙建华是典型的山东汉子,不仅是体形高大,更兼性格爽快。从见面的那一刻起,他就对我的乡亲赞不绝口。他说:“你们莆田人很能干,很有企业家的胆识,一个个都是老板级的水平!”
孙建华回忆说:“2003年12月,天气很冷的时候,仙钰带着洪华、双潘等四五个人一路从大连那边看过来,转了好几个地方。那天刚好我不在,他和我们副总经理谈。不知为何谈不拢,都准备走了。好在第二天我赶回来,请他们吃饭;第三天接着谈,就谈成了。合作的内容非常简单:每年五月把福建莆田的鲍鱼运到山东荣成,就直接吊挂在海兴公司的海带绳子上(叫海带间养鲍鱼),六个月后,天气转凉,水温下降,再迁回南方莆田老家。租金价格:每亩(实际海带养殖面积,相当于海水面积的45%)一千元。”
隔了二十多天,已是农历腊月,大老板林国华来了,很快就把合同签了下来,第一次订第一年的合同;第二次订了五年期合同,2009年又订了五年的合同。孙建华对我说:“你们林老板真好,没有一点老板的架子。”我说:“他一个乡村裁缝出身,还来不及练就大老板的架子。”
仙钰是个内敛的人,他比我年长几岁,跟我堂哥同一年去当兵的。在我们各自成名之前,我不记得曾经跟他说过什么话。等到后来熟悉之后,我发现他原来知道的那么多,足见他对人对事对世道的深切观察和深思熟虑,偶尔他忽然冒出一句话,会让我感觉如一道闪电一般横过高远的苍天(我见过不少学养深厚的企业家,都没有这种感觉)。
采取断然措施,拉动石城鲍鱼北上山东避暑,避免南方水温过高导致大面积死亡,据说还不是仙钰的创举,而是附近的个别鲍鱼养殖户的成功经验。但是,在2003年冬天,石城村的鲍鱼养殖仅两年,就能够作出如此断然的抉择,足见仙钰作为当家人的清醒意识。石城村的鲍鱼养殖是2001年春开始的,当年夏季鲍鱼大量死亡,秋冬之季却一举成功,创造了200%至300%的利润;带动了2003年的投资狂潮,投资规模扩大到一千万元以上,并再获成功。
“胜利中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1976年春《福建日报》一篇报道石城村抓“阶级斗争”典型的通讯标题,那时仙钰还在部队当兵,肯定不知道有这么一篇文章,但这种清醒的忧患意识却深深地扎根在心中。相隔三十年后,当面临石城乡亲(含海外华侨、务工、经商和公务员)把所有的身家性命都押在这一粒鲍鱼上时,为这六千多人口当家的他,心头的压力和肩上的担子是太沉重了--那是几个亿的钞票啊!乡亲们把村基金会的钱借光之后,不少人家都是借的高利贷啊!
必须保障乡亲们的血汗钱万无一失--仙钰在心中默默地对自己说(今天我这样推断)。
我从家中仅带一件衬衫和一件T恤去山东。五月底,闽中天气已经很热了,但到了俚岛,又碰上下雨,尽管把厚实的金威牌长袖衬衫扣得紧紧的,仍冷得受不了,只好让鸿恩带我去住地拿外套。石城村三四百人全部租住该镇草岛寨村社区(这是韩国三星集团厂房用地的居民安置社区)。在这里,我见到多年不见的老同学(从小学到高中)林鸿榜,高中毕业,我们还一起当了一年的护林员。那年,我们一起参加高考文科考试,十几分的差距使我们踏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之路--他多年漂泊在异国的港口之间,如今年纪大了,便回来养一点鲍鱼--他哥鸿恩告诉我的。我问这“一点”是多少,鸿恩犹豫了好久才说是“投了三十万”。鸿榜像过去一样瘦,还黑了一点,仍然话很少,不问绝不多说一句。令人欣慰的是:他儿子(名字中一字与我儿子一样)大学毕业娶了媳妇定居厦门,还是个不错的事业单位。
穿上鸿恩的外套我来到俚岛镇烟墩山,从高处眺望俚岛湾:从遥远的故乡来避暑的鲍鱼就躲在沁凉的海水中,一排排的海带架整齐地排列在海面,为它们遮住盛夏的酷热骄阳……此时虽然雨雾茫茫,我还是不停地按动手中的数码相机……离开的时候,我转身对着“烟墩山宾馆”几个鲜红的大字连按几下,因为我故乡石城山的最高处,也有一个完全相同的名称--“烟墩坪”。
2010年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