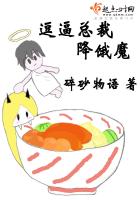面前那张脸,如果是普通人看到的话,恐怕会被吓到。
因为这样的怪病,妈妈经常用刀割伤自己,脸部也损伤的很严重,留着难看的疤痕,并且头发也掉光了...她是个可怜的女人,因为为了生下我她才变成这个样子的,每次我都不忍心看她自己伤害自己,但是在我阻拦不了的时候,我只能告诫她不要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
听我说到“禾谷与健同在一个班念高中”,妈妈沉默了,
“小希,请不要杀禾谷,行吗?”
她用苍老而干裂的嘴唇对我说道。
“吃饭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我回到小桌旁边,把食盒一层一层打开。
妈妈无话可说了,只是安静的坐下来拿起筷子沉默的吃饭。
五年前,妈妈嫁到琉璃家,令人悲哀的是,刚订下婚期夫君就发生车祸身亡,可妈妈还是尽到了一个做媳妇的本职,婆婆家这边同意让妈妈改嫁,不必要替丈夫守活寡,可妈妈毅然坚持要呆在琉璃家过日子,她被安排在丈夫的哥哥家里住着,但也就是那个时候,妈妈其实已经怀有身孕。
她并不是不贞洁的女人,是因为我必须要出生了,她只是个宿主,因为怀孕,这个可怜的女人突然变得发疯,她有几次弄伤了夫君的哥哥,也就是后来成为我大伯的那个人,甚至拿了把菜刀捅伤了大伯,在那以后,妈妈还企图自杀,但都没成功,一次又一次的都被阻止了,直到最后她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精神鉴定结果是,妈妈确实已经患有精神分裂,所以对大伯造成的伤害并不负有刑事责任,可是...于此同时,妈妈还被检查出另一项与精神病完全不同的病症,也就是后来被我称作“怪病”的东西——
在妈妈的血液里,含有“不属于这里”的分子结构,简单来说,不是人类的血细胞,但也不是其他什么动物的,那是...
“恶魔。”
这是一个实习医生悄悄对大伯说的话,他信奉宗教,抛开一切医患之间的关系,单纯出于一个信奉者对别人说的话,大伯不以为然的点点头,并不当一回事,可是之后,开始发生了某些可怕的事情...
妈妈住进医院以后一直被关在那种单间的“牢房”里,与其他病人不同,因为她有暴力倾向,唯恐伤及到无辜,所以她才得以这样宽敞的“待遇”。
那天晚上,一名护士准备进病房给妈妈换药,她割伤自己的地方一直都长不好,伤口总是在化脓感染,情况很糟。
护士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孩,很时髦的那类型,上班时还会带着耳机听音乐,她端着换药盘走进了妈妈的病房,可是病房竟然没有开灯——
“鹤丸女士,过来给您换药,今天感觉如何?”
说着,护士摸到了墙上的开关,按了下去...
强烈刺眼的灯光下,病床是空的,她扫视着四周,企图寻找妈妈的踪影。
突然——在窗边看到一个头发掉光了的干瘦身影,隔着一层白纱窗帘,身影干枯嶙峋,像极了一具靠在窗边的骷髅。
年轻护士被吓到了,还差点打翻了换药盘,她竭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叮铃...”从窗边飘来一阵铃音,护士才确定立在窗边的就是这间病房的患者,鹤丸未女士。
那是拴在妈妈脚腕上的铃铛,是她自己栓上去的,没人去追究理由,因为她是精神病患者,在别人眼里一切行为都是荒唐的。
“鹤丸女士,您站在那里吹风会受凉的,请到这边来,要开始换药了...”
护士呼唤着妈妈,可是立在窗边的人影没有任何反应...这让这位年轻护士不免害怕起来,她取下戴在耳朵上的耳机,周围顺势变得安静下来,甚至安静的令人发悚。
“鹤丸女士...”
护士又叫唤了一声,边说边慢慢朝窗边走过去——
除了病床,房间里还有一把靠椅,靠椅正好放在床脚,窗户在南面,床的位置在东面,如果不走到近处,靠墙一侧的床沿就成了被遮挡住的盲区,护士小心翼翼的走过去,一瞟眼,煞白的灯光下,一个女人趴在靠墙一侧的地板上一动不动,看样子正是她口中叫唤的“鹤丸女士”。
“啊——!”
护士惊恐的叫出声来,她猛然转头再看向窗户边时,隔着白纱窗帘,那个人影还立在那里,窗帘遮住了大半的身体,只露出一双光脚在下面...
“是谁?谁站在那里...”
护士颤抖着声音问道,她不敢过去看,那双脚分明就是鹤丸女士的脚,可如果那样想的话,趴在地板上的又是谁?
她决定先去确认趴着的那个——
她走到床边,放下手中端的东西,“鹤丸女士...”护士再次小声叫了一句,对方依旧毫无动静,像死了一样趴着,就连喘气的起伏感似乎都没有,护士伸手去翻动她,下一瞬间,凄厉的惨叫声震惊了整栋楼的人。
被惨叫声引来的人认出窗边站的那个是鹤丸未女士,可是趴在床边的那个无法确认,看到的人当场就呕吐了,还有直接晕死过去的,可是谁都无法说清看到了什么...
“我进去的时候,就已经看到鹤丸未女士站在窗边。”
询问间里那位护士小声回答着刑警的提问,她还在惊魂未定,瞳孔里闪烁着恐惧。
“一开始你为什么觉得在地板上的是鹤丸女士?”
刑警又问道。
“因为外貌的感觉...”
那个时候妈妈的头发已经掉光了,只有极其稀少的几根还粘在头顶,再加上她失去弹性的皮肤,死白的颜色,有时会泛起鳞片那种荧光,如果是初见的人看到后会有些害怕。
“那东西究竟是...?”
“你就当是一个噩梦吧。”
警察起身离开了询问间,护士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只是几个月以后跳楼自杀了,还不止她一个,那天凡是看到过“趴在地板上的那个”的人都自杀了。
那以后妈妈的病房更加“宽敞”了,整条走廊的病房都空着,只有她一个人住在那个房间里,走廊和楼梯之间还被人特别装了铁门,虽然不是密闭的,但铁栅栏的样子更像牢笼的感觉。
之后的没几天,我就在那个“宽敞的地方”出生了。
(这几天太忙,更新时间不太稳定,对不起各位友友,但是这种坏情况很快会恢复的,然后——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多吃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