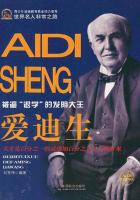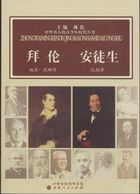“你不辞而别的时候是怎么想的?你和王汗一起在哈兰真沙陀向我杀来的时候是怎么想的?你,还有忽察儿、阿勒坛把我逼得在班朱尼湖边喝浑水、吃野马肉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我数万蒙古乞颜部只剩下四千六百人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我,我一直想着你呀……”
“胡说!你一直恨我不死!”
也遂插话道:“答里台叔叔您起来,铁木真应该向您道谢,您为什么反倒像负了债似的呢?”
“什么?!”铁木真瞪大了眼睛看着也遂,“我还,还应该向他道谢?!”
也遂从容不迫地说:“可汗,你还记得我们和王汗一起设冬营的时候,桑昆火烧牧场,抢掠百姓并未得手的事吧?那正是答里台叔叔给桑昆出的主意。”
铁木真吃惊地反问:“嗯?”
也遂接着说:“他那是给你一个知会,暗中提醒你多加小心。您不正是因为知道了桑昆的阴谋才转换了牧场吗?如果没有答里台叔叔救你,那一次你即使不被桑昆、札木合杀掉,哈兰真沙陀之战,你也不会逃出他们的毒手。”
铁木真看看答里台:“真的吗?”
答里台哭出声来。也遂妃继续说:“就说哈兰真沙陀之战吧,如果王汗死战到底,乞颜部就要全军覆没。你知道为什么王汗停止了进攻吗?又是因为答里台叔叔。是答里台叔叔劝阻王汗撤离了战场,你才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这难道不是孛儿只斤氏的骨肉之情使他这么做的吗?”
铁木真看着答里台,目光温和多了。
答里台哭着,摇头捶胸地说:“铁木真,铁木真,叔叔从来没有想当可汗的野心,是忽察儿和阿勒坛的妖言蛊惑了我。尤其是你关押了我,又不让我参加库里台大会议事的处罚,伤了我的心,丢了我的老脸,我是因为在晚辈和外姓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才走的啊。我不是为我离开你辩解,我其实不想求得你的原谅。只是,现在我老了,我只求你可怜可怜我这个孤老头子,给我一小块颐养天年的地方,我什么也不求了。铁木真,你肯吗?”
铁木真长叹了一口气,眼圈也红了,他抓住答里台,把他拉了起来:“叔叔,我恨你!可我再恨你也忘不掉你!你这个不争气的老头子啊!”
铁木真的眼泪也流了下来。
在一旁看着铁木真的也遂和合答安也都哭了。
二
太阳汗、古儿别速妃、屈出律太子临朝。
丹墀上置一小桌,小桌上的木笼里装着王汗的头颅。
札木合、忽察儿、阿勒坛、答亦儿兀孙、札合敢不辨认着王汗的头颅。札合敢不扑通一声跪下哭道:“哥哥!”
太阳汗问:“札合敢不,你认没认错呀?札木合,你们认出来了吗?”
札木合等道:“认出来了,的确是王汗。”
札合敢不跪爬几步:“伟大的太阳汗,我哥哥一定是走投无路才来乃蛮部寻求保护的,虽然乃蛮部与克烈部过去有过争端,但毕竟同是耶稣的信徒、和睦相处多年的邻邦,想不到我哥哥死得这样惨!”
太阳汗很生气:“撒卜刺黑,都是你治军不严,这样一个久负盛名的邻邦君主,怎么能随意杀掉呢?!”
古儿别速妃插嘴道:“反正脑袋已经掉了,你埋怨他也长不上了。请神甫来给他举行一次隆重的葬礼也就是了。”
太阳汗坐下了:“也只好如此了。札合敢不,你起来吧,我要让自己的文臣武将以臣子之礼,让儿子、儿媳以家人之礼祭奠你的哥哥,用国王的葬礼对待王汗,就像祭奠我一样!”
古儿别速妃咳了一声。太阳汗知道说走了嘴,赶紧道:“塔塔统阿,拿玉玺来。对了,要把王汗的头镶上银子。”
札合敢不说:“太阳汗,我哥哥一定是同他的儿子桑昆一起来的,求大汗派人去寻找并收留他吧!”
“应当,应当。这件事嘛,就由你来办吧!”
桑昆和他的十几个从人立马山头。桑昆说:“我们什么吃的也没有了,为了活下去,只好去抢了。”
他的马夫看了看下边的毡包说:“怎么,你是说让我们当盗马贼吗?”
桑昆说:“主会饶恕我们的,因为我们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有人附和道:“那就干吧!”
“女人留在山上,男人跟我去抢。吃的用的都要抢,人嘛,会说话的都要杀掉。”桑昆发布了抢劫、杀人的命令。
一个女人——马夫的妻子说:“抢东西已经是犯罪了,还要杀人?那样做,主还会宽恕我们吗?”
桑昆呵斥说:“你一个马夫的老婆懂什么?如果留下活口,乃蛮的士兵就会来追踪我们,我们一个也活不了!”他把刀一挥:“跟我来!”
十几匹马像旋风一样地冲下山去。
乃蛮居民从包里跑出来,被克烈人杀死。一个妇人跪在地下求饶,马夫举起的刀又收了回来。桑昆走过来:“你想留下她告密吗?”一刀杀了那个女人。
经过一场杀人抢掠,桑昆一伙已是筋疲力尽了。黑夜降临时,他们围着两堆篝火在烧烤羊肉。边吃边喝,一个个狼吞虎咽。
马夫捅了捅身边的妻子,两个人走开了。到了离开火堆远一点的地方,马夫的妻子问:“你有什么事?”
马夫说:“我不想给盗马贼喂马了,咱们走吧!”
“去哪里呢?”
“去投太阳汗。”
“他会收留我们吗?你忘了王汗的下场了?”
“我有办法能让大家活下来。”
“什么办法?”
“抓住桑昆,献给太阳汗!”
“不不不,主啊,宽恕我的丈夫吧!”
“你不愿意?”
“他是你的主人!”
“可他是个犹大一样邪恶的人!”
“那就让主去惩罚他好了,我们走我们自己的路吧。”
马夫把刀架在妻子的脖子上:“你这个糊涂的女人,不许坏了我的大事。你给我好好呆在这里,不许说话,不许动。我这就去除掉桑昆。”说罢提刀向桑昆的火堆走去。
马夫走到桑昆身后,刚要动手,桑昆回过身来:“你怎么不吃了?多吃点儿,明天我们还要赶路呢,给你。”
桑昆把一块肉塞给马夫,拉他坐下,然后对大家说:“我想过了,我们不当盗马贼了。太阳汗不收留我们,我们可以从这里往南走,那边的长城脚下有个汪古部,也是基督的信徒,啊——”
桑昆一下子咽住了话头——马夫的刀已经捅进了他的肋骨。
众人跳起拉刀,互相对峙。
远一点地方的马夫妻大声喊道:“乃蛮人来了——”
声音未落,百十名乃蛮骑兵已经把他们包围起来。一阵砍杀,十几个克烈人全都倒在了地上。
三
这年深秋的一天,乃蛮部太阳汗的汗廷变成了灵堂。
王汗镶了银子的头放在太阳汗的宝座上。
牧师在抑扬顿挫地念悼词:“他的一生伴着不计其数的光荣,而他的为人却谦和善良。他的地位使千万子民向他顶礼膜拜,而他却安详得像只羔羊。如今他离开了纷纭的人世升入天堂了,上帝啊,请接受这无罪的灵魂吧!”
太阳汗、古儿别速妃、屈出律、太子妃及札合敢不等群臣依次一边画着十字一边从宝座边绕过。
群臣走出汗廷。忽察儿对札合敢不说:“札合敢不,你哥哥死后有此荣耀也还算可以瞑目了,你就不要过分悲伤了。”
札木合对忽察儿小声说:“看到太阳汗的这套把戏,我直想笑。”
忽察儿怔怔地看着札木合。
在汗廷内,屈出律对坐在椅子上的太阳汗说:“父汗,把这老东西的头放在您的宝座上,这么隆重的祭奠,有这个必要吗?”
“你懂什么?我这是给活着的满朝文武看的,让他们知道我是个仁慈的国君,只有我才是我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最垂青的儿子。”
“也许有人会认为你是个糊涂的国君。”屈出律说罢走了出去。
太阳汗气极语塞:“你,你,你这个逆子,怎么可以这样对你的父亲讲话!你就不怕主的惩罚吗?”他气得跌坐在椅子上,对着王汗的头发脾气:“都是因为你这个死鬼!”
忽然他惊呆了,他揉揉眼睛,看见王汗的眼睛笑眯眯地在看着他,他顿时毛骨悚然,一边画着十字一边对阶下大喊:“快来人,把王汗的头从宝座上拿下来!”
侍卫们跑进来把王汗的头拿下。太阳汗指着庭角:“扔掉,扔掉!”王汗的头被扔到地上。
太阳汗见王汗还在朝他笑:“快,快踩,用脚踩,踩得粉碎!”侍卫们一顿乱踩。
太阳汗看着踩扁了的王汗的头,舒了一口气:“主啊,你接纳这个无依无靠的鬼魂吧!”
札合敢不回到自己的帐篷,颓然跪倒:“哥哥,你死后都得不到安宁啊——”他捶着地嚎啕大哭。然后抹了一把眼泪:“我要杀了太阳汗!我要为我的哥哥报仇!”
札木合捂住札合敢不的嘴:“札合敢不,咬人的狗是不叫的。”
札合敢不抓住札木合的手,答亦儿兀孙的手搭在他们的手上。接着是忽察儿和阿勒坛,几只大手握在了一起。他们的眼睛布满了血丝,阴森而可怕。
在太阳汗后宫,古儿别速妃给太阳汗摩挲着前胸后背:“一定是你又累又气,眼睛花了,死人的头怎么会笑呢?”
侍卫走来报告:“撒卜刺黑将军进见!”
古儿别速妃没好气地说:“不见!”
这时撒卜剌黑已怒冲冲地走进来了。太阳汗不满地问:“你怎么这么没有规矩?!我不是说过不见你吗?”
撒卜刺黑气呼呼地说:“人家王汗已经死了,你派人把他的脑袋割来辨认,这合乎什么礼仪?!”
“我用隆重的葬仪,用银子镶了他的头骨,难道这还不是最最崇高的礼仪吗?你没看见他的弟弟札合敢不都对我感激涕零了吗?”
撒卜刺黑顶撞道:“可是葬仪刚刚结束,你就把王汗的头骨踩碎了,你那种所谓的仁爱之心,早被这种惨绝人寰的暴行给冲刷得荡然无存了!”
太阳汗理直气壮地说:“那个脑袋是不祥之物,不踩碎它,毁灭就会降临到我们头上!”
撒卜刺黑毫不相让:“死人的脑袋有什么可怕?亏你还是鼎鼎大名的太阳汗!难怪先君对你不放心,临升天之前还担心国家前途未卜呢。”
“担心什么?”太阳汗不高兴了。
“担心你是一个祈祷而生的孩子,是一匹无经验、未经训练的小马。尤其是未经战阵,很难成为乱世有为之君。”撒卜刺黑悲愤地说。
“够了!”太阳汗不耐烦地打断他说,“我就不喜欢乱世,感谢主,给了我们安宁和平的生活,让乃蛮汗国一向太平无事。”
撒卜刺黑觉得他不可理喻:“什么太平无事?太平无事王汗还会掉脑袋?”
太阳汗轻蔑地说:“这有什么可奇怪的?东方有那么一些为数不多的蒙古人,用弓箭把老迈昏聩的王汗吓跑了,死在我们边将的手里,你说的不就是这件事吗?”
撒卜刺黑还要争辩,太阳汗抢着说:“铁木真算什么东西?莫非他也想做草原上的太阳?主说,天上只有一个太阳,那就是我!你看着,我现在就去把那个让你发抖的铁木真抓来。”
坐在一旁的古儿别速妃开始皱眉不语,继而撒嘴冷笑,这时她接过太阳汗的话头,以一个大国皇后的语气说:“我们要那些蒙古人干什么?他们浑身膻气,衣服油污,你如果真的把他们抓来,也要让他们离我远点,我可不愿意闻他们身上的那股膻味儿!”
“那就一个也不要他们,把他们都杀掉算了。”
“呃,如果有长得清秀的女孩儿啦、媳妇啦,倒不妨挑选几个,让她们好好洗个澡,换件干净衣服,可以派个挤牛奶、羊奶的差事让她们干干。对了,听说蒙古人唱歌跳舞还可以,留下几个给我唱唱歌、跳跳舞也行。”
“好,我马上派使者去汪古部邀集那些与我们同一信仰的人们,一起发兵,把野蛮的蒙古人都杀光,把他们的箭筒和弓矢统统夺过来!”
撒卜刺黑哭笑不得:“你们是在开玩笑吗?我的太阳汗!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大事,怎么可以当做儿戏一般,你这样草率从事,真是无以伦比的糊涂!”
太阳汗生气了:“你是怎么跟你的君主说话呢?”
“是先君临终时让我随时教训你!”
“你自己已经糊涂得无以附加了。你方才还说我未经战阵,现在又说我不宜用兵——真是语无伦次。撒卜刺黑你看着,上帝做证,我就要做一个有作为的乱世之君了!”
古儿别速妃站起来对太阳汗说道:“你们怎么对打呀杀呀的这么感兴趣?除了这个就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吗?太阳汗,走,陪我去看看裁缝给我做的新衣裳。”
二人走了,把撒卜刺黑抛在那里。撒卜刺黑愤愤然:“先可汗,你死的时候为什么不把这个女人也带走?留下她嫁给你这个昏聩的儿子,乃蛮就要亡国无日了!”
走下汗廷的古儿别速妃咕哝道:“这匹老山羊,叫得也太讨厌了,把他杀了算了。”
太阳汗叹口气说:“我何尝不想杀了他,可是先王临终时嘱咐过我,要听这个老东西的教诲。愿他的灵魂安息!”
“先王的灵魂安息了,我们可是不得安生了。”
太阳汗安慰他的妃子说:“你不要急嘛,我会想办法让这只老山羊永远闭上嘴的。”
四
1204年春,铁木真移营至帖麦该川狩猎、练兵。
一天,纳牙阿领着以汪古部首领之子不颜昔班为首的使团,赶着五百匹马和一千只羊,用车拉着六坛酒,押解着被捆绑的太阳汗的使者走向铁木真的大帐。
正在摔跤的拖雷、博儿忽和在一旁加油的窝阔台、脱虎见状停了下来。
纳牙阿领着汪古部使臣,押着太阳汗的使者进了大帐。
四个年轻人走过来。拖雷说:“啊,这大概是五百匹马,一千只羊吧!”
赶羊的人笑着说:“小将军好眼力!”
脱虎说:“他是瞎蒙的。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这车上拉的是六坛酒!”
博儿忽打了脱虎一拳:“你小子就是嘴贫!”
窝阔台说:“他若不是这张巧嘴,怎么会蒙骗住王汗呢!”大家笑了。
窝阔台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汪古部。”
“汪古部?”脱虎还没听说过有这么个部落,好奇地问,“汪古部在哪儿?”
别勒古台在他们身后接过话茬说:“在乃蛮部东南。”
赶羊人说:“对。我们汪古部世世代代为大金国镇守北部边疆。”
窝阔台说:“离这里好远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