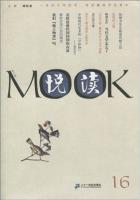乡思
/孙福熙
早晨的太阳斜照水上,又返射到河埠的椽手间,轻松的棉花似的依水的动荡而跳舞。
在我的记忆中,我此生没有这样清闲过,我坐在食常的一角上。这洋,我不必转头忽东忽西而能完全看见室内一切景象;尤其,劳烦我的耳目的形形色色的来路也只有两面,使我觉得比坐在中间者更是安闲。
我想在这清闲中开始我所欲做的工作之一,这种工作是我所预计或为旅行前所积欠下来的。然而我又想这第一日应该休息,所以连手中的这本日记也是屡次拿起而屡次放下的。
我的肩背所斜倚着的木壁零零地振动。不错,这外面就是波浪厂,他的奔腾的声乐真好听啊!四年以来,我所住的总是高楼,从未听到雨打屋瓦或雨水流地面的声音,在家中,低头看书时或深夜醒来时,欲知道下雨与否或雨止与否,不必抬起头来或开出门去,只要谛听瓦上就可知道的了。还有,每天大雨之下,院中积水数寸。不等雨止,鸭就从院角檐下出来游泳。在鸭声的轻快中,我感受驱逐烈日的风雨的凉爽。
抬起头来,我似乎想听听这声音是否从屋瓦来的,我看见光亮的天花板上的影子。窗外一半是波一半是天的景象投射到开着的玻窗上,窗洞与玻窗都投在返射镜似的天花板上,于是我们可以看见上下四个圆形与四个海天,水泡与波纹在船旁的水上向船后退去,而在天花板上的返射影中却反对方向的转成半圆形,使我想起幼年时所玩的走马灯。是的,现在已是阴历十二月,预计到家时还在旧的新年,正可玩走马灯,过我消失多年了的幼时的鲜美生活!
忽然的从两股罩传送上来薄爽的感觉,好像是穿了薄绸裤坐在石板上的样子,这观念似乎还是许多年以前所有的。
真的有许多年了。夏天的早晨,我家院中满栽鸡冠花老少年美人蕉;绯红的荷花乘着凉快浮在绿叶上放开来。我在这花前读书或写字之后就取了斗桶到河中汲水灌花。汲了几桶,小孩的腕力与腿力有些疲倦起来了。适巧,针一样细而蜻蜒一样在头上有两只大眼睛的鱼秧在水上几点绿萍的中间摇动尾巴,然而并不前进。为了疲倦,为了小鱼之可爱,我在这河埠的石级坐下。
早晨的太阳斜照水上,又返射到河埠的椽子间,轻松的棉花似的依水的动荡而跳舞。
轮船中天花板的面上也有这种光影,这是船边海水上的日光经过圆洞返射进来的,因此使我回忆幼年时河埠头的日影,而且使我觉得如当时坐在石级上的凉爽。
这种一切回忆确是甜蜜的。现在不必怅惘,我正在一日千里地向这甜蜜的实在进去。然而,所虑的,一切实景是否还完全存在,一切甜蜜是否还能在我的心中酿成,我忐忑不大敢走近去了。
故乡是一种图腾
/叶延滨
你无法战胜的漂泊感,逼着你寻找一个可以宁静的港湾,在这个港湾里有一只可以系紧你灵魂的缆桩一故乡。
几乎所有的诗人,广而言之,几乎所有写作的人,都写过故乡。这种写作的结果,使故乡成为永恒的主题,恰如爱与恨,生与死。在这个主题下,有乡情,有乡恋,有乡愁,那些无数次再现的场景——美丽的池塘,温馨的小屋,牵动情肠的小路,爬满青苔的石桥……反复叠印变成了一种图腾,渗入一代又一代人的血液。
如果认真分析和比较一下这类作品,大抵有这么个规律:故乡是离乡的人写的,故乡是上了年纪的人写的,岁数越大那种恋情越浓烈越苦涩。是的,年轻人是向往“山那边”和“外面的世界”的。在那些生活在父母之地的年轻人心里,故乡是一种束缚;在束缚之中,要像蚕蛾咬破茧壳飞出去则成为普遍的心理。故乡这个概念只有在告别老家那间老屋前站着的老母亲之后,在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独居异乡的滋味中,故乡才烙入心田。人与故乡终生处在角逐中,一个要走出去时却走不出去,想回来时又回不来的矛盾纠葛之中。我在陕北时知道这么一个故事:我军离开延安展开全面反攻时,两位当地参军的青年舍不得离家,当了逃兵。结果一个跑回来了,另一个捉了回去随军南下了。若干年后,被抓住的当了分区司令员衣锦还乡,而跑回来的依然是农民。告诉我这故事的就是这位跑回来的逃兵。真实性如何,天知道,然而却合乎情理。现在的年轻人开放得多,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总想以青春和活力为本钱,去闯一闯,去赌一赌。
闯入茫茫人海,无论取得何等成就,在这个风云变幻的大世界里,难免有无根的漂泊感。寻根、思乡、念旧也成为一种中年人慢慢患上的心病。十分奇怪的是,对于我们这些出生在城市的人,故乡不等于那个出生的城市,而是曾经经历苦难,流泪流汗的那块土地。也许这是一代人的特征,当过知识青年的几千万中国人,就这么认歪自己再生的那块土地。
思乡怀旧,会让我们回去看看。然而无论在想像中故乡多么美好,我们却无法抛弃现代文明给予的物质精神生活,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恬静了。乡里的亲友来了,瓜子核桃山货会让人感到亲切,也想唠唠家常,问一问今年的收成,然而亲友住了几日,便会感触到那一层透明的隔膜,把记忆中抹去了的有关故乡的苦涩味又激荡出来。
甜也罢,苦也罢,每个人总忘不了故乡,难道这不是我们情感所祭拜的图腾吗?大千世界,欲海天涯,那些人生旅途上许多人为之奋斗的东西,高官也罢,财富也罢,荣誉也罢,在某一天你会觉得它们竟是一钱不值的多余的装饰品。你无法战胜的漂泊感,逼着你寻找一个可以宁静的港湾,在这个港湾里有一只可以系紧你灵魂的缆桩——故乡。
我经常听见长长的唤儿声:“幺娃子!回来吃饭啰!”这不是我母亲的声音,也不是我插队地方的土音,是来自那图腾。
它提醒我,我已年逾四十,在这个世界上,该认真想想:欲何求也?
故乡在远方
/张抗抗
然而在城市闷热窒息的夏日里,我仍时时想起北方的原野,那融进了我们青春血汗的土地。
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流浪者。
几十年来,我漂泊无定、浪迹天涯。我走过田野、穿过城市,我到过许多许多地方。
我从哪里来?哪儿是我的故园我的家乡?
我不知道。
19岁那年我离开了杭州城。晴光潋滟、山色空潆的西子湖畔是我的出生地。离杭州一百里水路的江南小镇洛合是我的外婆家。
然而,我只是杭州的一个过客,我的祖籍在广东新会。我长到30岁时,才同我的父母一起回过广东老家。老家有翡翠般的小河、密密的甘蔗林和神秘幽静的榕树岛,夕阳西下时,我看见大翅长脖的白鹳灰鹳急急盘旋回巢,巨大的榕树林上空遮天蔽日,鸟声盈盈。那就是闻名于世的小鸟天常。新会县世为葵乡,小河碧绿的水波上,一串串细长的小船满载清香弥漫的葵叶,沉甸甸贴水而行,悠悠远去……但老家于我,却已无故园的感觉。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我也并不真正认识一个人。我甚至说不出一句完整地道的家乡方言。我和我早年离家的父亲,犹如被放逐的弃儿,在陌生的乡音里,茫然寻找辨别着这块土地残留给自己的要性。
梦中常常出现的是江南的荷池莲塘、春天嫩绿的桑树地里透紫酸甜的桑椹儿、秋天金黄璀璨的柚子、冬天过年时挂满厅堂的酱肉粽子鱼干,还有一锅喷香喷香的煮芋艿……暑假寒假,坐小火轮去洛合镇外婆家。镇东头有一座大石桥,夏天时许多光屁股的孩子从桥墩上往河里跳水,那河连着烟波浩渺的洛禽洋,我曾经在桥下淘米,竹编的淘箩湿淋淋从水里拎起,珍珠般的白米上扑扑蹦跳着一条小鱼儿……而外婆早已过世了。外婆走时就带走了故乡。其实外婆外公也不是地道的浙江人氏。听说外婆的祖上是江苏丹阳人,不知何年迁去湖州;又听说洛舍其名是早年此地曾有一支移民来自洛阳,洛阳人之合,谓之洛合。由此看来,外婆外公的祖籍也难以考证,我魂牵梦绕的江南小镇,又何为我的故乡?
所以对于我从小出生长大的杭州城,便有了一种隐隐的隔膜和猜疑。自然,我喜欢西湖的柔和淡泊,喜欢植物园的绿草地和春天时香得醉人的含笑花,喜欢冬天时满山的翠竹和苍郁的香樟树……但它们只是我摇篮上的饰带和点缀,我欣赏它们赞美它们但它们不属于我。每次我回杭州探望父母,在嘈杂喧闹的街巷里,自己身上那种从遥远的异地带来的“生人味”,总使我觉得同这里的温馨和湿润格格不入……我究竟来自何方?
更多的时候,我会凝神默想着那遥远的冰雪之地。想起笼罩在雾霭中的的幽蓝色的小兴安岭群山。踏着没膝深的雪地进山去,灌木林里尚未封冻的山泉一路丁东欢歌,偶有暖泉顺坡溢流,便把低洼地的塔头墩子水晶一般封存,可窥见冰层下碧玉般的青草。山里无风的日子,静谧的柞树林中轻轻慢慢地飘着小清雪,落在头巾上,不化,一会儿就亮晶晶地披了一肩,是雪女王送你的礼物。若闭上眼睛,能听见雪花亲吻蕾树叶的声音。那是我21岁的生命中,第一次发现原来落雪有声,如桑蚕啜叶,婴童吮乳,声声有情。
那时住帐篷,炉筒一夜夜燃着粗壮的大木棒,隆隆如森林火车如林场的牵引拖拉机轰响,时时还夹着山脚下传来的咔咔冰崩声……山林里的早晨宁静而妩媚,坡上的林梢一抹玫瑰红,淡紫色的炊烟缠绵缭绕,门前的白雪地上,又印上了夜里悄悄来过的不知名的小动物一条条丝带般的脚印儿,细细辨认,如梅花如柳梢亦如一个个问号,清晰又杂乱地蜿蜒于雪原,消失于密林深处……那些神秘的森林居民给予我无比的亲切感,曾使我觉得自己也是否应该从此留在这里。
小小的脚印沉浮于无边的雪野之上,恰如我们漂泊动荡的青春年华。我19岁便离开了我的出生地杭州城,走向遥远而寒冷的北大荒。
那时我曾日夜思念我的西湖,我的故园在温暖的南方。
但现在我知道,我已没有了故乡。我们总是在走,一边走一边播撒着全世界都能生长的种子。我们随遇而安、落地生根;既来则定、四海为家。我们像一群新时代的游牧民族,一群永无归宿的流浪移民。也许我走过了太多的地方,我已有了太多的第二故乡。
然而在城市闷热窒息的夏日里,我仍时时想起北方的原野,那融进了我们青春血汗的土地。那里的一切粗犷而质朴。20年的日月就把我这样一个纤弱的江南女子,磨砺得柔韧而坚实起来。以后的日子,我也许还会继续流浪,在这极大又极小的世界上,寻觅着、创造着自己精神的家园。
歌手
/佚名
自那以后,差不多过了一年半的时间,再也没有听到过盲人歌手弹唱了。
多年前,我从海口结束漂泊日子回到故乡,由于工作不太顺意,情绪十分低落,常常在夜深的时候独自坐在昏暗的书桌前,脑子里一片空白。每当孤独难耐的时候,在我居住的高楼对面一幢低矮的旧平房里,总会传过来一阵悠扬的吉它声,听得最多的曲子当属《爱的罗曼史》了。娴熟的弹奏技巧,注入曲子的款款真情,我猜想吉它手定会是一位翩翩英俊少年,或是一位对爱情充满了渴望与美丽幻想的纯情少女。
不久街上流行郑智化,对面楼里的吉它手也不例外。早上天不见亮,收录机开始播放歌曲《水手》,夹杂着跟着学唱的男中音,时间通常在半小时左右。晚上十点过后,吉它手开始了他例行的弹唱,只是绝少听到那动人心魄的《爱的罗曼史》了,取而代之的,正是这雄壮豪迈的《水手》,反反复复,直到夜深十二点过。
在神秘吉它手的歌声中,我仿佛看到了与海浪搏击永不倒下的水手,他们紧握住命运的缆绳,“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于是,我不再在书桌前无望地呆坐,又重新拿起显得生涩的笔,书写人生道路上经历过的风风雨雨。
往后的一段日子,对面的歌手把《水手》演练得更加纯熟了,弹唱时,声音苍凉悲壮,比郑智化唱得更有感染力,好像这歌就是专为他写的一样。我不知道,根据声音判断应该很年轻的歌手,为何有如此深刻的感触?
后来在路上偶遇搞新闻的朋友。问我,认不认识住在对门的向?我说不认识。于是我知道了吉它手的故事。
向今年20岁,从他来到这个世界,就从未体验过光明与美丽,他对这个世界唯一的认识,就是黑暗。没有朝霞,没有彩虹,没有花朵,好在他有音乐。音乐使他过得富足,心静如水。向对音乐有很强的悟性,吉它是他最好的朋友。他的音乐才能被别人发现,推举他参加当时正流行的卡拉OK大赛,而且还得了个二等奖。那时,我朋友为他写了专访,发表在报纸的一版上。
向出了名,心里就躁动不安了,再也静不下来,外面精彩的世界诱惑着他。终于,在无人关注他的某一天,他拨响了我朋友的电话,表达了强烈的自毁愿望。那天我遇到朋友时,他正匆匆地去劝慰年轻却失去了希望的向。
自那以后,差不多过了一年半的时间,再也没有听到过盲人歌手弹唱了。我的书桌也从封闭的屋内搬上了正对对面的阳台,每次在风雨中的阳台书屋里展卷读书,总希望突然就从对面传过来久违了的歌声,然而终是没有。
后来很少见到我朋友,见着的时候也忘了问向的消息。不知道年轻的盲人歌手是否重新振作起来,去挑战黑暗;也不知道,他是否仍在崇敬着风雨中那点痛算不了什么的水手,如我现在一样?
大顺通宝
/佚名
后来我在书摊上看到一本钱币大全,翻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这个距今1102年的钱币图案,更没看到想象中价值连城让我欣喜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