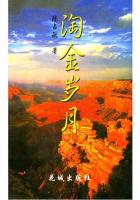喻昂的书店位于大学城的中心地段。
大学城在西城的西边。
离我的出租房很远。因为电动车即使充满电也不够往返于书店与出租屋之间的路程,所以我干脆卖掉电动车,换了辆好骑的山地车。我不得不像读书时那般骑着自行车穿梭于市中心与西郊。一周中有三四天骑车返回,有一到两天坐公交车,剩余的,我会先骑一段距离,把车停在某大医院门口,继而坐公交车,在我读书时,可节约一丁点路费。因为完全坐公交车太费钱,完全骑车我又太累。我喜欢选折中的办法。这种思维在我今后的生活中经常运用到。我总觉得穷人的孩子脑袋运算得多些,我对一切花销斤斤计较,除却书籍上的花销。另有个前提,在我心情正常的情况下,若是心情郁闷,哪怕洒钱能使我愉快,我自然也会毫不犹豫这样去做。
喻昂见状,笑言:"看来你是真打算钉在书店了。"
我一面整理刚到的新书,一面说:"那当然。虽然才干几天,但我发现这才是我最想做的事:与书为友。何况有你这么一个不善理财对生意无所谓的老板才是我不幸之中的万幸。"
"我已请之前辞职的那个学生帮你找了一位帮手,她负责晚上,你白天来就好,下午5点就回去。路途远,你自己小心点。"
"只好暂时先这样了。不行的话,我在这附近租住也行。"
书店布置得简洁温馨。大约有六七十个平方。主要出售考试资料和畅销书。
面对的顾客自然是大学城的大学生。
学生上课期间,我常常对着学校门口发呆。
说来惭愧,虽说我在这所学校待了两年多,却从未仔细看过它。即使我在写这篇小说时,也没有过多提及它。我就读的是一所三流大专院校。起初学校的旧址是在市中心的美食城附近,后来学院发展壮大,在我入校就读时就听闻学院要在西城重建。一年多后,我们顺利搬入新院校,远离市中心,害得我每天早早起床,骑近半个小时的车程上学。我永远记得当我骑三十几分钟车程来到新校区,给我的第一印象:大,太大了。
后来,接二连三,西城除了阳光大学没有搬到西郊,其他几所院校都搬至此,并命名为大学城。附近经济迅速复活。
每天看着这些比自己小几岁的学生进进出出校门,心里颇有滋味,细细嚼来,竟有一种丝丝甜味。我从未觉得自己度过的大学时光有多美好,我从希斯那儿获知每位同学的鸡零狗碎:某男生喝酒闹事住院了;班长期末考试又和团书记串通作弊;隔壁宿舍的某个高挑女生夜不归宿;某个白痴文艺男青年在女生宿舍楼下弹吉他唱情歌;某女生争风吃醋,种种,不一而论。多数时候,我都是一个人吃饭,走路,听随身听里的广播和音乐。无论过去校园20岁的我,还是在社会上现如今的我,都自觉忽视周遭人物事件,只活在自己的天地间。
生意清淡时,我便在随身携带本上写校园往事。只是偶尔甚是无聊时,才会翻阅书店里的书。说实话,我不太喜欢这些书,这些书纯粹是为了换取银子,对阅读的意义根本不大。因而大多数时候,我还是阅读在图书馆借来的名著。起初,我为自己这种清高羞愧不已,但当我翻阅几本流行书籍后,发现自己无法从中获取和找到我所要的心灵慰藉时,便认可了这种所谓别人口中的清高。何况,图书馆不久便免费对外开放,只需交纳100元押金,待到图书证退回,押金归还。文学类书籍和其他类书籍一样,享有一个月的借租时间,这大大方便了我的阅读。
书店的生活非常平淡。转眼就面临寒假。喻昂给我找的帮手叫蓝姬。大二。专业好像和金融有关。她有个男朋友,瘦瘦高高的,常送她来书店。
她的故事是自动送上门的。
有时候,我会觉得像我这样的写作者,太不是人了。故事里的男女主角各种情感,异常强烈,而到了我的笔下,变得非常平静。或许不如说,我本人非常平静。我写下她的故事时,平静得像是自己编织的故事。所以,我非常钦佩那些能把自己写哭的写作者。
我常常觉得自己不曾拥有人类的情感。难道我只是上帝手中的一只相机镜头?
我已不再是20岁的我。和蓝姬相处不多久,便明白她是怎样一个女子。轻易给人下定义是很困难的事。譬如希斯,起初我以为她和我是一样的女子,最起码,不贪恋钱财、不虚荣。可后来,事实证明,她对我压根儿怀有偏见,就像我现在这般固执地认定她一样。我无法找出深层次的原因,只好简单归结为一些形容词:爱慕虚荣、喜富厌贫。我不止一次看到蓝姬故意在喻昂面前打扮得花枝招展、说话嗲声嗲气的。这会让我昨晚的饭都吐出来、浑身竖起鸡皮疙瘩。所以我对蓝姬从不说多余的话,但她对我却莫名其妙地充满依赖和信任。
在快放寒假的最后几天里,她显得异常兴奋,兴奋中又带着些焦虑。我们肩并肩坐在书店的布艺沙发上,我随意翻看卜劳恩的《父与子全集》彩色纪念版。这本书荣获国外优秀畅销书奖。我收拾书籍时,看到它,翻了几页,便掏钱买下它。我喜欢在心情低落时翻翻漫画,朱德庸、几米都很不错。
蓝姬几次欲言又止。10分钟过去后,她像是作了最后的决定:向我和盘托出她的故事。
她先叫了声我:"小薰姐。"
嗯。我继续翻书。
我忽然想起,放下书,问她:"寒假过后还来的吧?"
"不太清楚。"
"要是你不能来,介绍你的同学过来也行。"
"嗯。"看得出,她在内心组织语言,"小薰姐,我告诉你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
"我中了10万块奖。"
"啊?"我万没想到是这个消息,想不到眼前的姑娘会有那么好运气,"不错哦。"
"我和大飞分手了。"
"为什么?"
"彩票是他送给我的礼物。"
"彩票中奖了,你却和他分手了?"
她点点头。我一副不解的样子。她道:"我问他,假如彩票中奖的话,他会怎么处理。他说先给自己买所大房子,我说不够买房,他说那就买辆车,我说车也不够,只有10万,他说那就挥霍掉,叫上一帮兄弟,咱也奢侈一回。你听听,这样的男人,我能跟他吗?"
我摇摇头。"是不能跟。那10万块钱?"
"是他送给我的。当然是我的,对不对?"
"对。"
"小薰姐,这几天,要是他来书店找我,你就说我回老家了,请他不要纠缠我了。"
"他不知道彩票中奖的事?"
"他要知道,估计非得活吞了我。"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这10万块?"
"你能陪我去领奖处把它领出来吗?到时我送你名牌包包。"她信誓旦旦,同时充满期望地看着我。见我不语,她加大尺码:"另再送只钱包?"
"陪你去可以,但东西不要。"
"真的?小薰姐,你太好了!"她激动得过来拥抱我。我被她的天真和对金钱毫不掩饰的追求给逗乐了。在男人与女人之间,我承认自己很多时候都很偏见。男人欺负女人就绝不可以,倘或女人占男人便宜,我便原谅女人。
待她激动过后,我问:"那你打算怎么处理这笔钱?"
"先存银行吧。我得跟往常一样上学读书,不然会被他怀疑的。留着关键时刻用。但小薰姐,每当想到我拥有这笔钱,就兴奋得难以自制,常常情不自禁手舞足蹈。感觉自己忽然之间变成一个富有之人,再不会担惊受怕了。我与那帮同学不再一样,我比他们都更有资本获得幸福。"
她说这些话时,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是在一本书上看到的。我想讲给她听,算是给她打预防针,预防她乐极生悲。但我又想起鲁迅的一个故事便作罢--一家人生了一个孩子,前来祝贺的人纷纷好言好语相祝,说这孩子日后一定大富大贵前程似锦。只有一个人说,这孩子,日后一定会死。
书上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个推销员向一位夫人推销一种产品,只要夫人答应推销员实施使用这种产品,那么夫人便可以得到数目不小的一笔钱,但前提是必须会有一个人死去。这个人可能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夫人开始还犹豫,为可能会死去的人深感不安,但后来,又想,反正这个会死去的人和我没有关系,而我可白白得到一笔钱,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她答应交易。结果,她丈夫意外身亡,她获得保险公司的保险金,数额恰好和推销员说给她的分毫不差。
我就是那个会认为"这孩子日后一定会死"的人,但我不会说出来。突如其来的好事常让我惶恐不安。因为得与失是一种平衡,当我得到一笔意外之财时,我考虑的却是我会在将来的某天失去什么。而我要失去的也许正是我最爱的。那么,我宁愿不要这笔意外之财。或许会有人说我太过悲观。在我看来,却不是悲观,而是预想到最坏的结果并准备好应对之策,那么,剩下的,便全是好的、不那么糟糕的。
不过,对于钓鱼者,鱼儿不上钩,是因为诱惑不够大或没有正中下怀、投其所好。若那位推销员给我的鱼饵是桑戈天或喻昂,我当然会毫不犹豫地上钩。就目前看来,上帝好像没有心情对我设下鱼饵。因为我与喻昂之间就像简单的员工与老板的关系。既然,上帝不准备钓我,那么,我便要准备钓喻昂了。
借口便是蓝姬领奖。
鱼饵,是我自己。
然而,故事并没有根据我设想的那样发展:拉上喻昂去领奖,领完奖,蓝姬离去,我找个借口去喻昂家里。
转折点竟是偶遇体彩领奖的负责人--梁超。一个在我的故事里消失了许久的人。
顺利领奖后,梁超约我吃晚饭。可气的是,蓝姬说要谢谢喻昂前来也要请他吃饭。我赶紧接话道:"不如四人一起吃吧?人多热闹嘛。"这就是从不喜欢热闹的我说出的话。
喻昂借故离开。蓝姬只好赖上我。
后来,我才知道蓝姬看上了梁超。梁超的确是个美男子。几年不见,他比从前更有男人味。我说他有男人味。一是他的眼神,二是他身材高大健硕(可判断他仍然坚持体育锻炼),三是他的秉性,显得成熟稳重、细心体贴。我压根无法把他与给我写信的梁超联系在一起。要不是他叫我,我根本认不出。
我还是喜欢他灵魂深处的东西。对他外表的美,和他本人一样,很抗拒。或许这种近乎完美的结合使我感到深深的不安。我越来越不相信看上去完美的人和事。完美背后或深处所潜伏的不确定因素,给我巨大压抑。
但蓝姬看到的只是一个貌若潘安的男子,还有个在西城来说相当不错的工作。最要紧的,当他从车库里开出他的黑色小轿车时,蓝姬更是眼前一亮。这种明亮和多年前希斯眼里的明亮如出一辙。看来,太阳底下,的确没有新鲜事。毫无疑问,她觉得自己好运来了。她这个曾经贫穷的女学生开始时来运转了。
但我知道故事远远不会那么简单、肤浅。
它不是小孩的思维和逻辑。它是老谋深算的老狐狸惯用的伎俩和把戏。故事里,到处飘荡着这些老掉牙的欲望与肉体、激情与金钱的嗜杀。人们或许对此乐此不彼,我却深恶痛绝。这并非清高孤傲。尽管这两个词语常被强加给我,我自己却并不承认。记得一篇关于《青春的倦怠》的文章,三岛由纪夫坦言:所谓真正的倦怠,是武侯贵族的专利。是拥有一切的人,在他们完全派不上用场的时候,才感受到的东西。清高和孤独,在我看来,清高和孤傲,亦然。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我没有任何行为可被称之为"清高和孤独"。就好像一个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姑娘,你夸耀她纯天然、质朴。又好比你赞美一个5岁孩童的天真。完全是多此一举。因为那原本就是特定人群身上拥有的特定品质。只有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才能公平客观地对待我,而非强行误解我,或一味地半讥讽半夸耀我。而我也是通过别人对待我的态度,来过滤我所交的朋友。
三人而坐的餐桌显得格外不合理。蓝姬看着梁超,梁超盯着我,我浏览菜单,却不知点什么菜。
我无力去描述这场饭局。奇妙的是,餐厅里播放的音乐是S·H·E的《长相思》。我记得这首歌。希斯常唱来着。还有那首《Super Star》。记忆尤深。
"你是,意义。是天,是地,是神的旨意。除了,爱你,没有真理。你是火,是我飞蛾的尽头。。。。。。"我记得这些歌词,因为希斯唱出它们时,满含深情。那时,她无可救药地喜欢着梁超。
吃完饭,梁超先是送蓝姬回学校,接着载着我飞驰在夜晚的公路上。
"很不错哦。你现在。"我坐在后座,似喃喃自语。
"可惜这一切,缺少了女主角,没有什么意义。"
我不曾想他单刀直入切入主题,便缄默不语。
过大桥时,他问:"去酒吧喝一杯怎样?"
作为故事的讲述者,往往比倾听者更没有耐心。他见我不做回答,再问:"怎么,不相信我?怕我借酒耍流氓?"说得我扑哧笑起来。"好啊。"我随即答应下来。
他开始如数家珍般地向我介绍西城的各个酒吧特色。"听上去,都不错。不过我更喜欢安静的环境。"
讲故事,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如果是一个悲伤的故事,最好是在黑夜里,讲述者和倾听者互相看不见彼此的表情。我称之为互相保护。模拟的是陌生人谈心场景。
相比较几年前,我津津乐道于别人的故事,现在的我,更倾向于保持一定距离。如果因为好奇故事而伤了其中任何一方,那么,我宁愿不知。这是我的原则。作为写作者,必须遵循的一个准则。
"那去我那儿吧。"
"好。"
如果说几年前,我相信他完全是出于本能,那现在我信任他,却是一种理性分析下的结论。夹杂着一点点第六感--感觉表明,他不会做伤害我的事。他只是需要有个伴儿,听他讲述,如此而已。
如果他只是想和我上床,事情或许会很简单。
我坐在车上,胡思乱想。
使我万万想不到的是,他与我联系的动机如此清纯--对当年我的帮助,一直心存感激。一到他家,他便开门见山说出他的动机。他就是这么说的:"一直铭记当年你对我的恩情。希望有机会报答你。"
我忙说不必,一面打量他的房间。
房间的装潢风格告诉我,他非常精于享受生活、拥有别具一格的审美情趣。他大概十分喜欢喝茶和咖啡。当他问我喝点什么时,已经开始研磨咖啡豆,煮咖啡了。"很不错的生活品质嘛。"
"你呢?"
"我只喝白开水。久水的水。"我强调补充。
"不介意陪我喝杯咖啡吧?"
"当然不。"我笑。
我完全忽视了我对咖啡心怀芥蒂--源于与韩野发生的不愉快都与咖啡有关。我这人就是这般不可理喻。
当然,我起初对梁超的好感也一直持续着,扩展到与他相似的人身上。"想什么呢,那么入神?"不知什么时候,梁超把热气腾腾的咖啡递到我面前的白漆桌上。
"呵呵。一些读书时的旧事。"
咖啡浓郁的香味扑入鼻中,沁入心扉。忍不住赞道:"好香啊。与我在咖啡馆遇到的咖啡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
"喜欢就好。"
他仔细看着我,看得我有些不好意思。
"你几乎没什么改变。"
我故作生气状:"不会啊,起码比以前知道装扮自己了。"
"我说的是本质的东西。"他呷了一口咖啡。
"你也是。但好像又改变太多。就好像一位心灵手巧的女子把她的旧娃娃拆掉,重新做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娃娃,尽管用的还是原来的材料。"
"你呢,是她手里一只挚爱的娃娃,很破旧了,她给你做了件新公主裙。"
我们相视而笑。
沉默,相得益彰的沉默。
他起身打开DVD,放了一张唱片,不一会儿,传来抒情的轻音乐。
"《蓝色的爱》。"他说,"它使我沉静。"
我细细品味。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他问,很深沉的样子。
"一直在相亲。琳琅满目的生活状态。"
"结婚了?"
"还没有。"
"能考虑我?"
"哈哈,不必以身相许。"
他也笑,笑容非常清澈。我常想他该是上帝最得意的作品之一。他身上有天然的魅力。这点,我以前倒没发觉。
"你请我喝咖啡,我们扯平了。以后,互不相欠。"
他着急起来:"那怎么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好像特别怕和我扯平似的。
"真的不必。心里话。"
我不是也欠着韩野的人情吗?但我心甘情愿欠着。梁超欠我的,我欠韩野的,你欠我,我欠你。把我们的名字通通去掉,这样算互相报答了。
"说说你的故事吧。"见他沉默,我说。
他摆摆手:"现在不想提。"
"好。"我说,接着和他一起沉默。
手机铃声不合时宜地响起。
我相信他会告诉我。只是时机未到。忽而有人给我电话,这使我恼火。但看到来电显示是喻昂时,我立马转恼为喜。
我表情的变化没能逃过梁超的眼。
我对他说:"抱歉,以后再见。"拿起包包便走至门口,等不及他对我说再见,便突兀地关好门,走下楼。这才接起电话:"喂?"
"你在哪儿?"
或许是走得急,加上内心欢喜,竟在最后几台阶梯踩空了,整个人跌坐在地上。"哎呀!"我尖叫起来。
手机那头听见,忙问怎么了。
我说没事,只是摔了一跤,崴了下脚。对方问能站起来吗,我说我试试吧。
他听到我故意叫声凄惨,忙说:"你待着别动,我来接你,告诉我你在哪儿。"
我内心窃喜。
拖着疼痛的脚走到马路上等他的时候,我十指相扣,默念:谢谢上帝。小女子佩服死你了。甘拜下风。以后一定多多照顾喻昂和我。
冬的夜,非常寒冷。我在冷风中瑟瑟发抖。
等了10分钟左右,我酝酿许久的喷嚏再也忍不住了,轰然而出,响亮而鸣翠。仿佛不过瘾似的,接二连三,喷嚏连连,它冠冕堂皇地告知我:小薰同学,你感冒了。
对哦,我痴痴傻笑:感情冒出来了。
喻昂的越野车及时停在我身旁,我钻进车里,一屁股坐到了副驾驶座上。这是我第一次坐他的车。
"冻着了吧?"他关切地问。
"没有。"即使冻着也冻得好啊。
"脚怎样,要去医院看看吗?"
"不用。"
他握紧方向盘,越野车飞驰在夜色中。
上帝啊,你的安排着实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啊。故事变得复杂了。因为上帝笑了,他把镜头一拉远,观众便可看到一扇窗前,站着一个人影,梁超看着我并目送我走远。
他身后的梅花,一朵朵绽开。
我在车上臆想连连。
喻昂不动声色地开着车。他的车技非常好,快而稳。
在问了我的住址后,他便不再说话。
车很快抵达出租屋前。我赖在车上,等他说点什么。
"到了。"他说。
"嗯。"
按照故事情节,他应该说:"不请我进去坐坐?"
但他说,下车。
可想而知,我的失望。
哦。我答应着,却不肯挪动。机会难得。
难道我只能等待三年后,与母亲安排好的人结婚吗?
我厚着脸皮说:"这么冷,进去喝杯热水暖和暖和。"
他笑了,好像对我一系列的心理活动了然于心:"车内有空调。"
该死的高科技,连车里都有空调。
"时间还早,去参观一下我的小屋。"我换种方式邀请。
"小朋友,都9点多,我还要赶回去写稿。下次再参观吧。"
可恶的老男人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我愤愤下车,把车门关得很响,淹没了他的话:"等等。"
他从车里下来,叫住我:"等等,小薰。"
我以为他改变主意,急忙回头,却见他递给我一个包装精致的礼品盒。送给我的礼物吗?暗想。谁知他却说:"这是我参加一个活动赠送的小礼物,是巧克力。我不爱吃甜食,你帮我消灭一下。"说着递到我手中。
"早点睡,明天还要坚守岗位。"
我打起精神对他说晚安。
第二天一早,蓝姬打来电话,明为问候我,实为打探梁超消息。还问我和喻昂昨夜如何。我笑问"什么如何"。她冷语:"别装了,你以为他昨晚为啥给你电话?""为啥?"我傻傻问。"是我给他电话的。说实话,我一直跟踪你和梁超。"她让我想起一个人:希斯。她们的口气如此相似--好像我上辈子欠她的100块大洋没还似的。原来昨夜不是上帝的安排,而是蓝姬的别有用心。
"怎么不说话?"她在电话里问我。"你想我说什么?"我说。"你想什么就说什么。"我什么都没想,但我说谢谢。"我们可以互相帮助。""怎么讲?""你帮我撮合我与梁超,我帮你撮合你和喻昂。"我本该说不必,但我说好。接着,我听到她的笑声,以零下180度的冰冷迅速向我袭来。我陡然冻住,动弹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