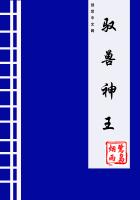两条线索,围绕着安诺波佩岛战局的发展而同步展开,平行而不游离。作者巧妙地利用书中出现的第一个高潮,把两条线索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侯恩爆发了公开的反抗,明知将军有洁癖却故意把烟头、火柴梗乱扔在将军的帐篷中央,向将军的权威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这是小说的第一个高潮。将军感觉到这是部下不服他约束的一个信号,断乎不能容忍,也采取了一个象征的手法,迫使侯恩承认不能不在他的权力面前低头。受了折辱的侯恩,虽然从来没有带过兵,还是被辗转调到了侦察排去当排长,并且立时受命要去执行一个至艰至险,成功之望极其渺茫的侦察任务。侦察排历尽艰险绕道后岛、企图潜入敌后的一段情节,把小说推到了第二个,也是最精彩的高潮。这是一段足使作者不朽的文字。从侦察排原来的头头克洛夫特上士身上,我们看到的几乎就是卡明斯将军的影子。侯恩固然是死于克洛夫特的借刀杀人之计,但是将军听到了他的死讯,觉得这个下场也“并不是始料未及的”,甚至还“感到微若游丝的那么一丁点儿快意呢”。
梅勒要写侦察兵艰苦的长途跋涉,这是他的既定方针。写后岛侦察的那段文字,也确乎说得上已完满地实现了他的夙愿,而小说中将军和他的副官这一条线索,则有点像是意外收获了。据梅勒自己说,他写出的《裸者与死者》第一稿并不是这样的布局。第一稿的重心完全放在侦察排身上。推测起来,梅勒大概是想模仿多斯·帕索斯的手法,以侦察排的这十几个人作为美国国内社会各色人等的典型代表,结合他们的出身经历写出他们在危急关头思想上是如何活动的,行动上是如何表现的。可是写到第二稿时,梅勒又把卡明斯将军和侯恩少尉这两个侦察排以外的人物发展了起来。这一发展,便意外地塑造出了两个有血有肉的军官形象。在第一稿中这原是两个不起眼的陪衬角色,到第二稿中他们的重要性却已经不下于原来的两个主角——侦察排里的克洛夫特和雷德了。梅勒自己也说:“如果不写第二稿,就把这部书出版,那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部有趣的战争小说,至多是有一些精彩的情节而已。”卡明斯和侯恩两个形象的树立,他们这一对矛盾的介入,不仅扩大了舞台的空间,更深化了作品的主题,使作品的内涵更丰富、更深刻了。若非如此,梅勒的这部小说也就不可能成为这样一件不同凡响的艺术珍品。
假如说从克洛夫特上士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存在于美国军队中的那股黑暗势力,那么从卡明斯少将的身上我们便隐隐看到了这股势力的根子所在。将军和侯恩少尉之间的斗争,将军的代理人克洛夫特和侦察排士兵之间的斗争,虽然发生于南太平洋的一个荒僻小岛上,但是我们如果视之为美国国内社会斗争的延伸,那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侦察排里那一群行动粗鲁、说话下流、沉痛愤激的士兵,他们本来在国内都属于社会的下层,甚至是那喧嚣动乱的美国社会的弃儿。透过他们在海外的作战生活和思想活动,联系关键时刻作者让他们“飞回到过去”的特写式“亮相”(这是作者仿效多斯·帕索斯《美国》三部曲而采用的一种奇特的倒叙手法),我们不只看到了美国军队内部官与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依稀看到了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从这一点来看,说梅勒的这部小说已经超出了战争文学的范畴,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于这部小说,历来有一些争议。有的评论家得出结论,认为小说的主调是悲观的、绝望的,理由是书中的人物个个都以失败或幻灭而告终。(这种观点可以说“源远流长”。直至一九七七年,纳尔廷在《当代文学概览》一书中还持这种观点。)侯恩少尉到处碰壁,不但受辱于将军,连性命也糊里糊涂断送在克洛夫特的手里。雷德在同克洛夫特的最后较量中“给打瘪了”。将军赢得了攻岛战的胜利,但是他心里明白胜利的取得却并不是由于他的指挥。克洛夫特眼看大功可成,穴河山征服在望,最后却还是不得不逃下山来。其他一些士兵最后也都成了人生战场上的失败者,个个都失去了自尊和信心。仗虽然打胜了,却并没有一个胜利者。不过,小说的作者可不是这样看的。早在一九四八年,他在接受《纽约客》杂志的一次采访时就坚决不承认这部小说是悲观主义的。他说:“有人说从这部小说里看不到一点希望。……其实这部小说是很想说明前途大有希望的。我的本意是想用这个故事来比喻人的历史发展进程。我想探索一下在一个病态的社会里,因与果、劳与酬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荒谬绝伦。书中固然写出了人的堕落、糊涂简直已经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但是也写出了人之甘受驱策并不是漫无止境的。人尽管是堕落了、变态了,然而胸中还是向往着一个比较光明的世界。”事实上,作者也决不会希望读者不带一点是非善恶的标准,完全用超脱的眼光来看待小说中每一个人物的成败,如上述论者那样。有些评论家得出的结论就和上述论者完全不同,例如赖德奥就认为这是一部积极的书、乐观的书(见《1900—1954年的美国激进小说》,第270页。)。他认为,将军满心想以前后夹攻一举击破日军防线,而日军早已崩溃在先,作者安排这样一个结局,显然是想表明这些权力论者终究不能违背群众的意志,任意操纵历史发展的进程。将军不能不忧心忡忡地看到,侯恩一个人他还对付得了,而他手下却有六千之众,这么些人他就无法对付了。克洛夫特对付得了一个侯恩,却对付不了不想翻越大山的那班部下。在赖德奥看来,一个不是那么腐败、不是那么病态的社会,其种子就埋在那些满嘴脏话、摇摆不定的士兵身上,尽管他们自己并不知道。
也有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缺少了一个真正具有战斗性的主人公”。当然,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同法西斯将军对抗的侯恩是显得很软弱,自知难免要跟骑在大家头上的“当家”上士爆发一场冲突的雷德是斗争得不够坚决。但是,我们似乎也应该看到作者塑造这些人物的初衷。作者在书中第三部的卷首引用了尼采一段不大好懂的话,倒是可以让我们窥知一些作者的心意。尼采的话是这样说的:“你们中间第一等的贤者,也不过是草木与幻影两者杂糅、混而不和的产物。可是我又何尝要你们成为单纯的幻影?又何尝要你们成为单纯的草木?”梅勒并且就以“草木与幻影”作为小说第三部的标题。草木与幻影,在这里是对立的两个方面,我们如果把这对矛盾理解为有形的肉体与无形的精神、俗世的东西与理想的东西,大概还是比较符合引用者的原意的。《当代名人传记》上提到,梅勒曾经表示过这样一种看法,就是《裸者与死者》是一部带有象征意义的书,主题在于表现野兽与先知(兽性与理想)在人类心灵中的搏斗。这就更可以为上面一段引语添上个注脚。所以作者创作时的主导思想,已经决定了他笔下的人物不会高大到近乎理想,也不会坚强到足以成为英雄。因此侯恩也就不免要感叹:“要是不算环境留在他身上的种种痕迹,不算他顺手捡来的那种种混乱谬误的看法,他基本上就跟将军一个样。”调到侦察排以后,他又觉得“认真检查起来,他自己俨然也就是一个克洛夫特”。雷德也会叹息:“人,敢情就是这样万分脆弱的东西!”我们看到他有时还会起“贪生怕死之心”,到后岛走了一趟回来,“心里还是没有一点谱儿”。想在作品中寻找作者根本无意提供的东西,那当然要失望了。
最后还有一个对书名中“裸者”二字如何理解的问题。“死者”,这和原文中的“the Dead”引起的联想是完全吻合的。打一仗死了好多人,这是一种理解;为了人类的未来有些人牺牲了,这又是一种理解;在卡明斯之流看来那些小人物“差不多已经全是坟中枯骨,只有等着做出土古尸的份儿”,这也是一种理解;还可以有其他的理解,其他的体会。“裸者”,跟原文中的“the Naked”基本上也能引起同样的联想,只是“naked”还有一层“defenceless”(无遮无掩)的意思,从一个“裸”字要想到这上头来,还得稍稍转一下弯才行。所以“裸者”固然可以理解为“人性已经暴露到赤裸裸的地步”,又何尝不可以理解为“感到精赤条条、无遮无掩、任人摆布、毫无保障”?书中的马丁内兹登陆前在运兵船的甲板上不是有一种“赤条条无遮无掩之感”吗?罗思在穴河山上爬得筋疲力尽,倒地不起,挨了加拉赫的一巴掌以后,不是又多了另一种“赤条条的感觉”吗?值得玩味的是,梅勒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也就是远在本书出版以前,还曾写过一个以精神病院为背景的剧本,剧本的名字也叫《裸者与死者》。这个书名他后来就移用于本书,剧本则改写为长篇小说,直到一九七八年才易名《化仙记》出版。可见,对《裸者与死者》这个书名作者有他特殊的偏爱,说不定还别有他独特的体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