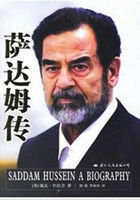求戒的学子,大多数经过多年沙弥生活的最初训练,一个真正的戒子,应该是自感到尘缘已经放下,他已不再有寻常人的那种“瞬息万变”的心猿意马,他已从基本上化掉了一般人的那种“心不由己”的积习,而不是在生活上对一切均掉以轻心。一旦求得大戒,则是需要时时处处以生命去维护每一条戒律的纯洁和它的完整性,否则,那便是一句空谈,那便是自欺欺人的戏谑。而那些踏进寺庙不过几天,根本上不懂出家意义的人为了追赶时髦和潮流而轻率“求戒”,那实在是视神圣的戒律如儿戏的行为,其本身即已犯了大戒。
所谓三坛大戒,即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一般说来,初坛沙弥戒时间最长,二坛比丘戒场面最为隆重,三坛菩萨戒教仪最为神圣。其中初坛沙弥戒最为烦琐,内容有挂搭、请引礼师、道喜看单、贴单、通启二师、请戒开导、查验衣钵、露罪忏悔,最后再登坛受戒。初坛时间最长,要占去整个戒期的三分之二。
新戒须在三师七证的证授下,才能成为真正的比丘。这三师七证,均须是有德行者,而得戒和尚更是佛界最受尊敬的大德。因得戒和尚是所有新戒得戒的根本师和归投处。
庄严的钟声敲响,戒子们穿上染衣,在引礼师的前导下走进雄伟的大雄宝殿。大雄宝殿里,那高踞于莲座之上的三尊大佛无比庄严,神圣的佛陀用智慧而慈爱的目光沐浴着这群不凡的年轻学子,在这一刻,这些南来北往,乡音各异的年轻学子一同沉浸在一种极其超然的境界之中。跪在那庄严的戒坛上,大兴不仅想起他这三十一年所走过的路,所遇见的包括爷爷在内的善知识:以三步一叩拜遍四大名山的西竺僧人、二祖寺里的疯和尚、戒如老和尚,当然,他最为感恩的还是师父常法。为了追寻出家之路,他可谓千辛万苦,最后终于得以见到恩师。如果不是恩师让他在挑水的山路上来来回回奔跑了六年,他又何能真正认识“搬柴运水皆为道”?与此同时,他还想到娘、朱逸然以及翠翠。他记住翠翠说过的话,想着,我此一生,若能成佛,第一个就来度她们。
一些早有所闻的佛教大德被分别安排为这批求戒学子的传戒和尚,羯摩师,教授师以及七位尊证师和引礼师。这一期的传戒师为当时江浙一带有名的高僧果慧大和尚。一切的因缘俱已成熟,戒期在有条不紊中顺利进行着。首先由引礼师为戒子们讲说最初的规矩和常规礼仪,接着,接受了三衣(袈裟)以及戒钵、坐具的戒子按班排序三人一组登入戒坛,这时,教授师开始分别为戒子们演说二百五十条戒律。当所有的戒条都一一讲说完毕之后,戒子们开始在三尊大佛的座像下举行庄严的宣誓:尔今得戒,将终身奉持,尽形寿而不渝。最后,传戒和尚面对刚刚得戒的戒子们郑重宣布:汝等今俱已得清净戒体,从此以往,汝等不再是预习沙弥,而是一个真正的得戒比丘,是一位修因中的菩萨,七位德高望重的尊证师可为汝等作证,汝等今后,一切言行,需以戒为师,依戒而行。
自此为止,所有的戒子便成为一个象征着“杀贼、应供、无生”的堂堂比丘僧了。
他记住了这一天,一九三一年四月初八,即佛祖释迦牟尼圣诞日。
戒期圆满,得戒的师兄弟们有的要去参拜其他三大名山,有的则应其他戒子之约,去江浙一带应付佛事,逆水行舟中就只剩下他一人了。船从南京启锚,在下游芜湖过夜并换乘另一艘木船继续下行。他决定上岸去广济寺投单,顺便也去逛逛芜湖的街市。
刚踏上江岸,就听到有人惊呼:“抓贼呀,抓贼,那是我的救命钱啊,你还给我!”呼喊的是一个中年妇人。芜湖是长江南岸有名的水陆码头,小偷之多,他是早有耳闻的。这时,便有一年轻人抓着一只包袱很快地从那边跑过来,而不远处,有几个人似在接应。小偷当跑过他身边时,他突然伸出一只脚来,那小偷扑了一个嘴啃泥,手里的包袱失手落下。小偷爬起来,要去抓那包袱,却被他用脚踩住。小偷看了看他,说:“和尚,把钱包还给我。”
大兴说:“凭什么给你?”
“那是我的钱包。”
大兴笑笑,说:“不吃酒,不脸红,不做贼,不心虚。你说说,这包里有多少钱?”
小偷当然说不出钱数来,小偷说:“你少管闲事,把钱包给我。”
他用脚踩住那只钱包,说:“有本事你把我的脚搬开,这钱包就是你的了。”
小偷扑上来,伸手去搬他的脚,又哪里搬得开。小偷急了,说:“和尚你找死啊!”说时,那几个接应的家伙一下子就将他围住了,有人抽出了刀子,说:“和尚,你不在庙里念经,却跑到这里管闲事来了,你活够了吗?”这时,那被抢的中年妇女也跑了过来,说:“师父,那包里的钱是我东挪西借来,给我男人抓药的,不能给他们啊。我这一大家,就全靠他啊。”
大兴只是将那钱包踩在脚下,说:“你们几个小毛贼听到没有,这可是人家救命的钱。”
“你少罗嗦,把钱包还给我,放你走路,否则,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小偷说着,就举着刀子向他扑来,他撂起一脚,将那毛贼的刀子打掉,接着,那几个毛贼将他前后左右团团围住,周围看热闹的民众喊着:“师父,你小心啊!”
大兴说:“刚才他一人搬不动我的脚,现在你们不是有四个人吗,你们一起发力,如果能把我这脚搬开,这钱包就是你们的了。”
四个毛贼一起扑上来,他们有的抱住大兴的腰,有的抱住他的左右两只腿,一心想把大兴搬开,但此时的大兴却像生了根的大树,像一块飞来顽石,无论这几个毛贼如何发力,大兴叉着腰站在那里,脸上带笑,就像没事儿一样。那几个毛贼力气用尽了,便有趁和尚不注意时拔出刀子。周围民众又叫着:“师父,小心刀子。”大兴见这几个毛贼孤注一掷了,便稍一发力,那四个毛贼就像四块碎片,向四处跌出一丈路远。四个毛贼知道今天遇到传说中的鲁智深了,不得不自认倒霉,有的抹着嘴角的血,有的揉着摔折了的腰,一个个骂骂咧咧而去。
那中年妇女趴在地上,连磕几个响头,说:“多谢师父,多谢师父。”大兴用脚一勾,将那钱包勾到手里,再郑重地交到中年妇女手里,说:“你丈夫得的什么病?”中年妇女说:“只是高烧不退,说着糊话,也看了郎中,也请了道士,一点用都没有,郎中还只是让抓药,家里哪有钱这样一包一包地抓药啊。”
大兴说:“你家住哪儿?”
中年妇女说:“离此不远,就在三长街。”
大兴也是怕那几个毛贼还会盯着这中年妇女手中的钱,便一直跟着她来到三长街的一个巷子里,见那男人烧得就像一团火,满嘴说着糊话,便对这男人的病知晓七分。他吩咐女人取出一碗米来,又要了一条干净毛巾将那碗米整个包了,就将那只碗在病人的头上晃了几晃,口中念了一通咒语。一遍咒语念过,那男人突然就睁开眼来。家人忙围了上去,问他看到了什么,男人说,那么多的鬼缠着我,要索我的命呢,幸亏一个菩萨赶走了那些鬼,我这才醒来。家人便明白几分,说:“菩萨就在你面前,还不赶紧谢他。”男人从床上爬起来,就要给大兴磕头,大兴说:“我给你开副草药,赶紧吃过,今晚就会好的。”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已有外国轮船在长江行驶,上游安庆与下游芜湖之间每日有小火轮往来通行。第二天一早,大兴便乘江华号小火轮逆水而上。然而轮船在大通附近遇到风浪,因大通码头吃水太浅,轮船无法靠岸,船上便通知乘客,所有在大通下船的乘客,只得去上游码头,第二日等风浪过后再转乘下游轮船返回大通。这样,大兴不得不在船上多呆了一日,当天傍晚,轮船靠在安庆盛唐湾码头。
安庆,这个他幼年流浪的所在,现在,他又再次回到这里。踏上码头,他第一件事就是想到要去看翠翠。直到现在,朱逸然是怎样当兵的仍是个谜,朱逸然当兵了,翠翠是否知情?朱逸然战死沙场,翠翠又是否清楚呢?再说,翠翠带着两个孩子,该是怎样的生活?这些,他都必须知道。天色尚早,他在迎江寺办好投单手续,便顺着江边,去了大南门一带。找到那座他熟悉的院子。
开门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看了看他,问:“师父是来化缘的吗?”
“请问这家主人是姓朱吗?”
那人摇了摇头,说:“我不知道,我是去年从一个姓刘的人手里买下这院子的。”
“呵,打扰了。”
他去了那条石板路小街,找到当年朱逸然的店址,但那里却开着一片瓷器店。他向那年轻的伙计打听原先的永和酱坊,伙计说不清楚。他不甘心,又去隔壁的一家绸缎庄,向一个上了年纪的朝奉打听朱逸然朱老板。那老朝奉摘下眼镜看了看他说:“师父是他俗家的弟兄吗?”他说是的,我出尘很多年了,不知兄弟的下落,先生如果知道,务必告诉我。
老朝奉把算盘放在一边,说:“七八年前,朱逸然说是去河南办一批货,没想到却再也没有回来。是死是活,至今没人清楚。”
他把要问的话问出来:“他的家属呢?”
老朝奉说:“男人没了,孤儿寡母的,店本来就不是朱逸然的,朱逸然失踪了,老板就把店收回去了。朱家的女人只得带着一双儿女投奔芜湖的公公,可不久还是回来了,在北正街烧老虎灶。惨哪,好好一个儿子,在马路上玩耍时被一辆汽车扎死了。”老朝奉长长地叹了口气,说“有几年没见到她了,不知道她现在还在不在那一带。哎,朱逸然的生意做得太红火了啊,结果就是这下场。”那老朝奉拨拉了一下算盘,又叹了口气说:“人抗不过命,命抗不过天。老天爷要毁人,人一点办法也没有。”
大兴去了北正街,远远的,他看到一个中年女人挑着一担大号水桶从江边走来,女人穿着草鞋,水一路滴洒着,女人的草鞋踩在那湿漉漉的石板路上,发出叭哒叭哒的响声。翠翠将那桶水倒在大缸里,接着就系上围裙,往老虎灶里添着大糠。她伸手撩一撩那一绺被江风吹乱的头发,麻利地端起水瓢,往前来冲水人的水瓶里灌着开水。他记得,翠翠比他还小一岁。
他实在不忍心走过去,既然自己无法帮翠翠,何必让翠翠破碎的生活再添新愁?就让她在这样的生活中麻木地生活下去吧。他记着翠翠的话:“你成佛后,就来度我。”他朝翠翠的方向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转身离开那条石板路街。